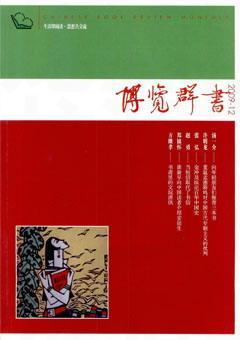当短信取代了书信
赵 勇
学术批评网的创办者杨玉圣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程春明被刺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要给学生上课,但他没有讲该讲的内容,而是给学生做了一次《热爱生命》的人生讲座。我在读他讲座的内容时,突然发现了如下文字。那是他在谈论当今的大学生如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时说出的一番话。他说:
现在科技和通讯发达了,人们几乎用短信和电话代替了传统的家书。对于那些日理万机的人来说,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大学读书的人来说,写信,而且是手写,可能是最好的与父母联络的方式。短信,固然言简意赅,但往往辞不达意,难以表达完整的叙事和笔端的丰富情感;电话,固然省事,但第二天通话内容就模糊不清、难以回味了。可是,手写的家书不同,亲人(无论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从收到信、拿到有孩子笔迹的那一刻起,就心存感动:见字如见其人;信,还可以反复地看,以解相思之苦。有人说家书有什么好写的啊?可是,我知道,在座的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大都是写情书的高手,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家书呢?其实,举凡成长的烦恼与收获、读书的困惑与快乐、生活的郁闷与感悟,乃至耳闻目睹、道听途说,哪怕是自然景致、天气变化,不都是家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吗?
千万不要小看了鸡毛蒜皮的家书,因为它恰恰是亲情的体现、人性的温暖,甚至是慰藉父母养育之恩的第一批“空头支票”。在不可能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回报亲人之前,让我们先从感情回报开始。因此,我希望听了我的讲座的朋友,如果你过去没有写或者很少写家书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写家书,并且是手写,而且是尽可能多地写。
读杨玉圣的这段文字,我很是感慨,因为尽管他的告诫没错,但现在的学生已很难亲自手写书信了。我在2003年的《光明日报》上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关于大学生书信情况的调查。文章作者在一所大学调查了1000名大学生,其中只有5人定期给家里写信。甚至有人还发现这样一封怪信:
爸爸、妈妈:
你们好!我最近身体好()一般()不好();学习累()一般()不累();有钱()缺钱()。
这并不是子女写给父母的信,而是一位母亲替正在上学的儿子写的家书。信的下面是母亲的一段注释:“孩子,好长时间没收到你的信了。妈替你写好这封信,你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括弧里划勾寄回来就可以了,这样我和你爸就放心了。”
看到这个调查后,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这种有着两干多年的书信传统正在走向终结。那么不用书信,我们现在如何与家人、亲朋好友联系呢?答案很简单,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MSN上的聊天。我把这些凡是诉诸于文字形式,通过电子或数字媒介传播的东西统统看作短信。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书信传统走向终结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短信文化。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短信取代书信,短信文化取代书信传统绝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短信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书信传统的消失,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方式的消失。
无论是古代的邮驿系统还是现代的邮政系统,书信从寄信人到收信人手中,它需要经过一个时间、空间的旅行,它的特点是慢。而这种慢又塑造了人们的情感体验方式和书信体验方式。比如,唐朝女诗人陈玉兰的《寄夫》中说:“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首诗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把离别之苦、关切之忧融入到一种名符其实的书信体验中。再比如,唐宋之问的《渡汉江》有这样的诗句:“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里无论是“一行书信干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还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都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方式。正是因为书信的迟滞、延缓、阻隔,才使古人的时空感知变得遥远而漫长,而等待、盼望、忐忑、焦虑、极度的悲伤与狂喜、悠悠不尽的思念等等,便成为这种时空观的产物。我把这种体验看作一种前现代体验。
我们现在还会有这种体验吗?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了。比如说一个在外地求学的大学生回家的时候,可以一个电话就打到家人那里,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几点几分的火车或者是飞机到达,而家里的情况也通过频繁的电话、短信联系,早已是一清二楚。所以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再有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受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这个时代我用一个词来表述就是全面提速。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铁路的6次大提速似乎已变成一个隐喻,它暗示着我们10年生活的速度变化。比如,快餐食品的增多,这是吃的提速;时装更新的加快,这是穿的提速;居住面积的变大,这是住的提速;夕发朝至的列车,这是行的提速。除此之外,还有电脑提速、宽带提速、下载工具的提速、产品上市的提速、结婚离婚的提速,像速配、闪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似乎已被生活的加速度所包围,我们也开始生活在一个对速度之快、之美的迷恋与沉醉之中。
这种全面提速、快的节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总是通过缩短时间去消灭空间。这就是美国学者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由于时空压缩,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时空观,而新的价值观也应运而生。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在中国一度非常流行,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用“短暂性”来解释今天这个时代和过去的时代不同:以前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低短暂性的时代里,如今我们却遭遇到高短暂性,所以“用完就扔”成为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当迁移和流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一个“地方”的用完就扔;当离婚率变得居高不下,这是对“感情”的用完就扔;当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被匆匆浏览后遭到删除,这是对“信息”的用完就扔。我想,在书信文化传统中,家书或情书总会得到妥善的保存,这实际上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缅怀和呵护;而在短信文化的氛围中,却很少有人去保存短信,因为它们太容易被生产和传播,所以一键删除、来去匆匆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命运,它们不幸遭遇到一个“短暂性”的时代。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思考短信,我们可以把短信看作是这个“短暂性”时代的美学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催生了一种崭新的体验——现代性体验,或者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这是一种轻快的、液态的、流动的现代性体验。由于现代电信机制造就了时空压缩,人们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得以改变,而时空压缩不但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贬值,而且也催生了人的情感世界的贬值。为了让情感得到滋养,人们的情感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但越是频繁,人们的情感就变得越是脆弱。古代的恋人一年半载没有书信往来,他们依然相互等待;现在的恋人不要说一年半载,就是三天五天没有电话短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持久的东西、永恒的东西。
我们今天确实已经生活在短信文化的包围当中,无论我们是爱它还是恨它,书信传统的终结与短信文化的来临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短信文化来临的时间还比较短,它最终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我现在还说不清楚,但书信传统的消失带走了什么却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比如,我在读哈贝马斯的著作时,曾经发现他对书信与文学之间显在与潜在的联系特别关注。书信与文学在中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我却从哈贝马斯那里似乎受到了一些启发。可是我们现在已失去了谈论这一问题的基础。再比如,以前我们曾经有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书信作品,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鲁迅的《两地书》、沈从文的《从文家书》、傅雷的《傅雷家书》,我们以后还会有家书、情书的形式吗?我们还会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吗?不可能有了。我们现在生活在快的节奏中,也生活在轻的体验中,但这种轻很可能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究竟是快好还是慢好,轻好还是重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会形成不同的答案。如果从文学、美学的角度来看,我给大家提供两个人的说法。我在读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时,看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没什么急事的时候,他更愿意开车走老公路,因为“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还有一个说法来自于米兰·昆德拉,他说:“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怏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我想,这两个人的说法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