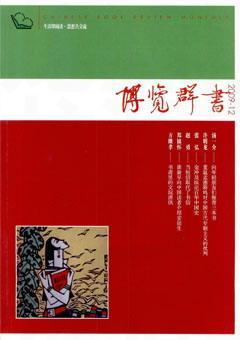静处的月明:林徽因诗存及其它
张建智
有关解读林徽因与新文化运动之文,至今寥寥。人们似乎只愿她是闺阁绣楼里不经风雨的才女,抑或仰慕的只是沈从文所说的“诗一样的人”。我认为,她于新文化运动,有着割不断、读不完的历史情结,只是未引起关注而已。
林徽因早期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新诗界中是占据一席之地的。她早期的诗作,大多刊于南徐志摩创办的《新月诗刊》,后常刊出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林徽因诗作,情感细腻,真挚婉约,善用比喻,多用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风霜雨雪作为象征物。《八月的忧愁》、《笑》、《记忆》、《那一晚》、《你是人问的四月天》等诗,都体现这一特点。《那一晚》,应该说是她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一首: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诗共两段,以“那一晚”开篇,连续出现3次,引出3个回忆的片断。以“到如今”作为承接,由回忆转入现实,又以太阳、阴影、红花儿、黄花儿等一系列意象,表现诗人所思所想,化无形的思绪为有形的象征物,形象生动。第二段,以“那一天”开篇,表示由现实转向未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的情感喷涌而出,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用箭、鸟鸣、花影来表达自己沉埋的思念、热切的盼望。全诗南回忆引入现实的思绪、转入未来的期许,情感虚实交融,层层推进,自然流畅。这首诗的遣词造句也十分精妙,每两旬尾字押韵,加上那一晚、到如今等起首词的重复出现,使得整首诗读来悠扬回转、极富音乐性。
我对林的作品十分喜好,书桌上总保留着她的一帧黑白相片。相片中的女子素面朝天,伏案凝思。身旁一盏瓷座的台灯,透出幽幽光亮。她静静地望着那光亮处,双手搁在一本摊开的厚厚的大书上,似在思索着什么,眼神楚楚动人。右下角题:1934年林徽因于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那年,林徽因30岁,已是一双儿女的母亲。这位活跃于二三十年代诗坛的传奇才女,留下了无数张美丽的倩影,但相比她少女时代清纯无邪、娇美如花的容颜,我更爱她为母后的清雅明丽。
林徽因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陆官巷。她生长在一个具有维新意识的旧式大家庭中:祖父林孝恂是光绪进士,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他资助青年赴日留学,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父亲林长民两度赴口留学。习政治法律,通中学西学;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为黄花冈革命先烈。16岁,她随父亲游历欧洲,旅居伦敦,后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这些经历,让徽因的学识、心性、文字,时透着北平朱檐琉瓦的旧时月色和康桥浓荫碧水里的幽幽桨声。
美丽的女子身边总不乏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何况林又才华横溢。与徐志摩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初识,惹得这位大诗人对她情牵半生,抛弃发妻张幼仪,结局她仍嫁为他人妇,徐终生视其为缪斯女神和红颜知己。最终志摩因赶去参加她的演讲坠机身亡,令林徽因痛彻心扉。徐志摩去世后,她不断有诗文对其缅怀纪念。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她是青梅竹马,一同赴笈美利坚,终为伴侣,一生对她宠溺有加。
在被无数传记作者、小说家和编剧反复咀嚼和津津乐道的感情纠葛中,林徽因对徐、梁两人的态度始终是争论的焦点;真相也犹如雾里看花。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无从评论。但我始终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和交融,是把握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主线,对林徽因也不例外。
徐志摩对她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少女林徽因的心绝不可能如一池死水,必然荡起层层涟漪甚至波澜。梁思成对她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相近的家世背景、素养和学识,意味着安定的生活、有尊严的社会地位。她可能犹豫,可能徘徊,甚而痛苦分裂,但长久以来的家训和教育,最终战胜了如流星般一闪而过的感情冲动。
人们常惋惜徐志摩那段包办婚姻,不禁臆想若徐林二人在康桥相遇时男未娶会如何如何。即便如此,我认为林徽因依旧会选择梁思成。尽管当时的林徽因未经世事,但旧式大家庭三妻四妾的生活,已在她早熟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生母与父亲貌合神离的婚姻令她明白婚姻不能仅依靠感情的契合,共同的志向和人生道路,才是她追求的幸福之旅。而这恰是梁思成能够给她的。面对徐志摩西方诗人式的热烈追求,她清楚地看到“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确实,她无法像志摩那样,浪漫到底。她的性格中交织着性灵与沉重、浪漫与现实,正如她终生热爱的建筑学一样,是一种美与科学的结合。
相比对林徽因爱情和婚恋之种种热议,她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论说,便显得门前冷落。
林徽因除了写诗,创作的小说虽仅留下六篇,但可以说篇篇是佳作。处女作《窘》,透出她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细腻、精巧、多层次的功力;《钟绿》、《吉公》、《文珍》以及最有名的《九十九度中》等作品中,林徽因非常关注京华烟云中各色人物的理想与挣扎。她的小说,读着流畅、清新。其娴熟的手法,多源自于英美求学时代阅读西方文学的功底。如果林徽因能坚持小说创作,我想,其成就恐在张爱玲之上。只可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避乱西南的林徽因身心交困,失去了安稳的创作环境。她生前未有单印本的诗集和文集出版,最早的《林徽因诗文集》,直到1985年问世。
最令人惋惜的是林徽因唯一的剧本《梅真同他们》,本是四幕剧,只完成了三幕。剧中心比天高、身为婢女的梅真,敢爱敢恨、聪慧婀娜。当时业界评价很高,美学大家朱光潜赞其为“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梅真等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林徽因戏言:“梅真参加抗战去了”!这像是一句双关语,透露出她对人物命运和自身命运的无奈,也成为当时不少读者,如今许多研究林徽因的学者,永远的遗憾。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作如是观:因为诗歌、文学也许只是她众多兴趣中的一种,林徽因人生的最后30年,都奉献给了中国建筑事业。她以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发现了古建筑中灵动的神韵,也铸就了她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片辉煌。
如今忆及她的文学生涯,除了积极从事新诗和小说的创作外,林徽因还是新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文化推手。她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重镇之一的“新月社”的重要成员,诸如泰戈尔来中国,几次重要的文化盛事,都能见到林徽因的款款身影。她的家世背景、学识经历、品行和魅力,使新文化运动的众多主要人物,与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如胡适曾称其为“中华民国第一才女”;金岳霖把她称为“中国的曼殊菲儿”。我想,一部五四后的新文化史,不论是竖着写还是横着写,围绕林徽因周围,似有着无形的磁场,俨然成了新文化运动战士们相聚畅谈的桃花源。在她面前,没有政治立场、没有党派门户——她只单纯地欣赏新文学作品中的美和真。
林徽因非常喜爱沈从文的小说。因撰写《王世襄传》,我曾访谈过他。王世老94岁时,在迪阳公寓的家中,还不无神往地与我聊及抗战时期,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同住李庄时期的生活。他说,林徽因曾问他是否爱读小说,当得知王世襄未曾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时,她大为诧异,极力向王世襄推荐沈的几种小说。也许,在沈从文小说中,那深深根植于民间的乡土情怀,强烈地吸引了她。因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使她产生了神秘感。她高度赞赏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性,给予当时这位间荡北平的“乡下人”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帮助。萧乾斑斑白发时,还忆及自己的文章被林徽因赏识、受邀初至梁家的往事,惊喜和得意,溢于言表。当时寓居北平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也是林徽因家的常客。
如今,我们只能从那一代文人零零爪爪的掌故中了解林徽因的趣事,想象她的机趣、妙语和率真无矫饰的性情。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匆匆走了:伦敦寓所里林徽因曾拥被夜读的炉火冷了;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曾被冰心讽刺为“太太的客厅”里的茶香淡了;真光剧院里美丽的齐德拉公主缓缓谢幕;四川李庄病榻前,低低的读书声听不见了……香山“双清”的霜叶却仍年复一年地红于二月花。重读她的诗作,是想拨开围绕在她身边爱情婚姻的种种故事,单纯以诗人名义,去怀念她,也是为了留住那个年代最真的一缕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