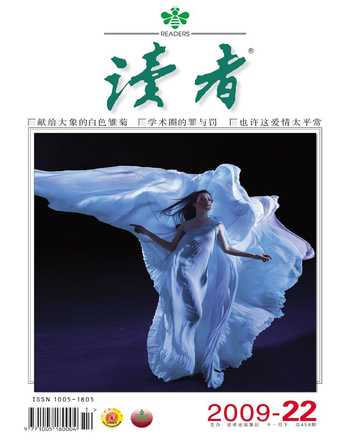夜里疼痛的片段
包利民
一
童年。
一个漆黑的夜里,大雨未歇。偶尔的闪电撕开黑暗,映出疾走的身影。母亲背着我,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我伏在母亲的背上,如身处颠簸的船上。我昏昏沉沉地发着高烧,母亲踏在泥水中的脚步声,如在遥远的梦中。
还是黄昏的时候,雨就开始下了。我走在雨中,心里全是疼痛。那是记忆中母亲第一次打我,因为我偷拿了别人家一块漂亮的小镜子。当时我紧紧地捏着那面镜子,母亲在抢去的时候,镜子突然碎裂,她的手也被划破,鲜血淋漓。
我夜里发起了高烧。当母亲背着我走了4公里的土路,到了镇上的卫生所时,已经快到午夜了。打了针后,我感觉好了些,母亲又背起我走进黑夜,走进雨里。回去后才发现,母亲的手被雨水淋得发了炎。那一刻,我心里有了莫名的痛。
童年如一个无瑕的梦,而我的梦里却有了一块疤,常常疼醒所有的回忆,然后,心被遥远的爱与温暖所湮没。
二
记得一位老师,姓于,极凶悍。当时我正读初中,他是我的班主任。他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不管学习好或不好,都是同样的严厉。大家都不喜欢他,有时还故意气他。他有很严重的肺病,一生起气来就会剧烈地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每当他开始咳嗽时,就意味着他很生气,有人就要倒霉了。
我那时学习偏科,数学极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最高分,而别的科目就很一般了,为此于老师没少对我进行暴风骤雨式的管教。我一直对他没有好感,常感叹自己命不好,初中最美的3年时光,会遇到如此不堪的老师。
我曾偷偷地报复过他一次。那个冬天,有一次我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临走时,我用圆规把于老师的自行车轮胎扎破。这样一来他就无法去县里,也就没人在我耳边大呼小叫了。
可是当我从考场中走出来时,看见冰天雪地里,于老师正艰难地走来。10公里的路,不通车,零下20摄氏度的天气,他竟然真的走来了。他大步走到我面前,胸口起伏着,呼出大口大口的白雾,然后咳得弯下腰去。我的心惴惴的。果然,他咳喘稍平,就立刻对我吼道:“考得怎么样?要是拿不了第一,看我怎么收拾你!”他的眼睛红红的,竟吓了我一跳。
后来我才得知,那个早晨,于老师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刚刚安排好父亲的后事,就急匆匆地向县里赶来,只为来看我的竞赛。许多年间,我都没有太多的感激或者感动,直到有一天,听闻于老师因肺癌离世,我才如梦初醒。而醒后,疼痛如水漫过,那个冬天的上午,他的身影,他的咆哮,他红红的眼睛,成为我心底最温柔的伤,一次次逼出我的泪水来。
三
那一年,在一个离家千里的陌生城市,我因胃病住进了医院。
一个大病房中,住着十几个患者。那时我胃一疼起来,仿佛全身所有能感知的痛都集中到胃上。我蜷缩在床上,双手紧按胃部,脸上全是冷汗。
邻床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先天性心脏病,嘴唇深紫,瘦瘦的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着好奇。有一次,我疼得翻来覆去的时候,她忽然来到我床前,拿着一块手帕给我擦额上的汗。她的手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她说:“叔叔,你很疼吧?我给你念书上的故事,就不疼了。”然后,她拿起一本书,给我朗读起来。
这个孩子,曾经两次被送进急救室,身上插满了管子。更多的时候,她只是躺在床上看书,或者轻哼一些歌曲,凝神看着输液管中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只有母亲在护理她,母亲在的时候,她的笑容比平时都多,夸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只是从没见她喊过疼,即使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只是咬着嘴唇。
那个有着暖暖阳光的下午,女孩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拉着妈妈的手说:“妈,现在一点儿都不疼了!”然后,她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紫色的嘴唇如花绽放。那一句话,那一朵笑容,使周围的每一颗心都剧烈地疼起来。现在想来,那个永远也跨不过13岁的女孩,却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与怀念。
(辛碌忠摘自《思维与智慧》2009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