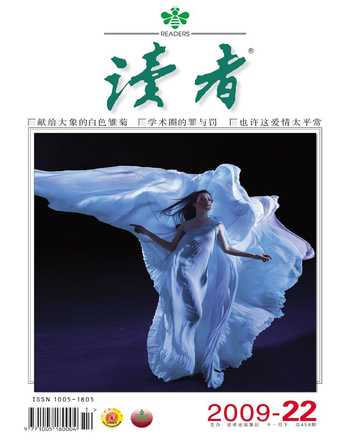学术圈的罪与罚
薛青青
谁是诺贝尔的囚徒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学者始终具有无上的声望和权威。他们远离普通人的视野而生存,因为和其他职业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是神秘、纯净和一片祥和的。
事实上,学者不过是靠科研吃饭的普通人。然而不同的学者面临的境遇可谓天壤之别:一辈子出不了成果的人,只能在寂寞的暗夜里爬行;一旦出了成果,便仿佛登入仙籍,享有无尽的学术副产品——美誉、权力甚至金钱。为了戴上那个诺贝尔的皇冠,他们难免会犯错误,难免要明争暗斗,难免会变得虚伪,难免会迷失。
敢于揭开学界血淋淋的恶疮的人并不多,而能用一个深刻的故事去探究学者内心的,只有《诺贝尔的囚徒》。这一切都得感谢它的作者卡尔·杰拉西。在写小说之前,杰拉西本人就是一位标准的学者。他因实现了人工避孕药的合成而名震全球,至今还享有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人工避孕药之父”。这项成果让他一夜之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斯坦福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甚至还把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国际科学大奖——沃尔夫化学奖收入囊中。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在六十岁时突然宣布退休,把科学研究毅然抛在脑后,转向文学创作,而作品的题材无一例外,全都是科学界的稗官野史。
小说的主角是天资聪慧、自信满满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康托。在某个凌晨,他灵光乍现,构思了一个关于肿瘤如何形成的绝妙的实验设想。根据经验,他很快得出了判断:如果这个实验能够成功,他绝对有实力去角逐诺贝尔奖!很快,康托就安排座下得意门生杰里·斯塔福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由于担心其他学者也会在某个凌晨想出类似的课题,他给了斯塔福三个月的期限,这样他就能获得对外公布这个理论的优先权。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而恰恰是这个绝妙的实验,给他日后的学者生涯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在导师的耳提面命之下,斯塔福没日没夜地待在实验室里,最终获得了成果。康托大喜过望,和斯塔福联名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成果,一时间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哈佛大学的权威教授克劳斯决定提名康托为当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可接下来,意外却接踵而至:克劳斯带着研究小组希望对康托的实验结果进行验证,然而,接连两次重复实验都遇上了麻烦——由于斯塔福的实验笔记过于简略,克劳斯的研究小组开始怀疑这个实验结果的真实性。紧随其后的是有人偷偷给康托递上一张神秘字条,暗示他斯塔福没能在导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从而私下修改了实验结果。此时的康托正走在通向诺贝尔奖的星光大道上,这些巧合让无法回头的他不再信任斯塔福——他曾经认为所有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位。于是他毅然决然地与斯塔福分道扬镳。
康托面临着一个难以选择的困境:如果他向外界透露了斯塔福失败的实验结果,恐怕他这辈子再也别指望得诺贝尔奖了;可要想隐瞒,又谈何容易?面对诺贝尔奖的诱惑和学术道德的挑战,他该何去何从?在光环的面前,康托最终做出了选择——隐瞒真相。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
谁料克劳斯早已在一旁洞悉其中的隐情,于是,这位学术大牛也不惜撕破老脸,对康托提出了种种要挟,使康托从此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这本《诺贝尔的囚徒》看上去似乎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它描绘了同行间为学术优先权而相互竞争,为发表论文而费尽心机,女性在学术界所受到的歧视,乃至为争取学术桂冠——诺贝尔奖而不择手段……这些在现实大学里正一一上演。
其实,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只是一个正常人,在巨大荣誉和大好前途的吸引力面前,道德操守的堤防有时也会溃裂。比如原本大度豁达的康托,一向主张公开自己的学术思想,鄙视那些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藏着掖着、生怕被人抢先发表的人,可是一旦事关诺贝尔奖,他却马上像变了个人,一再叮嘱学生斯塔福“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克劳斯虽说是世界闻名的权威,却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他曾经是康托心目中的“恩师”“偶像”,最终却不惜一切代价,向康托进行敲诈。他抓住把柄,要求康托今后要不断地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直到有朝一日他获奖为止。
学术江湖的潜规则
在各种诱惑面前——小到论文署名的顺序,大到诺贝尔奖这样的学界至高荣誉,学者们也会有常人的反应。康托为了获取学术荣誉,与同行钩心斗角,甚至在违规、作假的边缘行走。诸如此类的困境是今天千千万万的学者都曾经遇到的。
潜规则之一:著名教授只管申请经费,几乎从不亲自动手做实验。
在当今大学,实验室就像一座金字塔,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大多数学生都在从事一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他们“只是被当做有手的工具而已”。而实验室的领导——那些地位显赫的“超级明星”,主要任务则是募集研究经费,以及在重大学术会议上公布他们的成果。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学生,你只能希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到时候你就同样可以享受“科学明星”的待遇了。事实上,大家都承认这条潜规则,所以康托偶然亲自动动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无限敬仰:“像他这种地位的人谁还在做实验?”
潜规则之二:教授在学生完成的论文上署名,甚至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作者。
书中有一段关于这条潜规则的对话极为精彩。当正在攻读文学批评博士学位的莉亚对论文署名提出异议时,教授阿德利立刻对外表态:“这个课题是我提出来的,我用我的研究经费提供了设备和学生的奖学金,经费申请的报告是我写的,我们一起讨论工作进度,我建议采用某种技术,提醒她注意重要的参考资料……”所以,她的结论是:“一般认为,教授作为作者之一是很正当的事情。事实上,这个领域里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主要作者。”她的话自有一番道理,不过,这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在这些教授眼里,他们才是学术课题的真正完成者,学生只是“有手的工具”,能让学生在论文上署名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所以,当斯塔福和他的导师康托联名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时,他十分满足于自己并没有像大多数学生那样被忽视——被列在所有称呼中最常见的“等等”一行里。
潜规则之三:女性在学术界很难得到晋升。
小说在主要描绘男性学者的科研工作之外,还穿插了校园中的女性故事。斯塔福的女友塞莉是化学系的高才生,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才上大二的她心甘情愿地与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教授勒夫金恋爱,最终从师生恋中获益,得到了勒夫金的许多学术指导。后来,勒夫金还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对她的前途更有帮助的导师琼·阿德利。阿德利是一位女教授,年仅三十四岁就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荣誉,令人惊诧的是,她为了将来能成为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毅然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因为她认为,科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可能把她将来怀孕的情况也考虑在内,而评审委员会里大多是男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德利原本姓亚德利,她在读研时,非常关注自己发表论文时名字会出现在第几位,因为学界有一个惯例,一起从事研究的作者署名时应该按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排列。为了将来在论文署名时永远占先,亚德利(Yardley)把自己的姓氏更改成了阿德利(Ardley)。虽然这让她的父亲肺都快气炸了,她却很高兴,因为从此她的姓氏首位字母是A,每次发表论文都能排在第一位。
作为一位有着几十年学术阅历的科学家,杰拉西自然对这些潜规则深有体会。学术圈,不过是一条生物链。无论多么出色的学者,也首先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然后才是各自专业领域中的专家。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好人与坏人,只有一群有着聪明的大脑但偶尔也会犯错、也会迷失的人。正如眼下学术腐败被一一揭露,那些学者犯过的错误尽管隐藏多年,终有一天也会大白于天下。如同康托在后记中所言:“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没有永久无法侦破的谋杀。因为凡是重大课题,或迟或早,其实验都会被重复,其理论必定会被其他人检验或论证。”
(醉欣怡摘自《大学生·中国校园》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