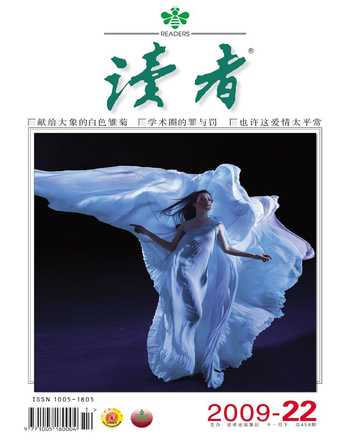喜爱花儿的警官
亨利·斯莱萨
春天来了,堂·佛莱莫队长的感官再度活跃起来,感受到那种熟悉而又令人愉快的震颤。佛莱莫喜欢春天,那时大地披上绿装,树木欣欣向荣,最妙的是到处鲜花盛开。他喜爱乡村警察这份工作,在黑利维尔警察总部附近栽种牵牛花是他的主意,那些花儿也能得到他的保护。
到了6月,佛莱莫队长明显地表现得与往年不同。佛莱莫像是变了一个人,常常皱着眉头,不去照料他的花园,却总是待在屋里。警队里的朋友们为他担心,不过也明白其中的奥秘。他们知道佛莱莫的烦恼:他仍在思念麦克维伊太太。
他们相识正是因为两人都喜爱花儿。自从麦克维伊太太和丈夫搬进阿登路上的那座两层小楼之后,那女人在她继承过来的蓬乱的花园里挥动着绿色的魔杖,令它改变了模样。一簇簇玫瑰竞相开放,大片粉红色绣球在门廊边争奇斗艳,硕大的三色堇、牡丹全都露出脸来,紫罗兰和圆叶风铃草在石块间蔓延。这儿的矮牵牛花显得比队长养的更茂盛,铺展开来,一直爬上台阶。
一天,佛莱莫队长停下车,红着脸朝那个花园的栅栏走去,麦克维伊太太正在里面侍弄常春藤。他是单身汉,已是四十多岁的人,却不善于同女人相处。麦克维伊太太比他小几岁,稍微有点消瘦,并不十分美丽,不过脸上总带着阳光般的和蔼笑容。
佛莱莫艰难地对她表白:“我只是想对你说,你家的花园是全黑利维尔最美的。”说完他皱起眉头,好像刚刚才将她逮捕归案似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回车旁。
头一次遇见麦克维伊先生时,佛莱莫便不喜欢他。麦克维伊脸上轮廓分明,嘴巴里像是永远含着一个柠檬。佛莱莫同他谈起那些花儿,他那张酸溜溜的嘴巴歪了歪,表示轻蔑。
麦克维伊太太解释道:“乔不喜欢这个花园,不过他知道它对我意义重大,特别是他常常出门在外。”
在黑利维尔,没有人说过他俩的闲话,也没有人在他们背后嗤嗤地窃笑。一周周过去,麦克维伊太太和警察队长在室外见面,全镇的人都看得到他们。在秋天到来之前,他爱上她了,她也一样,但是两个人都不曾谈起此事。
她倒是偶尔谈到她丈夫。她渐渐对佛莱莫产生信任,又受到爱情的鼓舞,便对他讲了乔的事情。
她说:“我真担心。我认为他生病了,不过他的病是医生看不出来的。他总是气哼哼的。从小他就有远大抱负,如今得到的却很少。”
“不算少啦。”佛莱莫贸然说道。
“他一出门便不愿回家来。虽然他从来不这么说,但我看得出来,到家后他恨不得马上再走。”
“你觉得他……”话还没有说出口,佛莱莫脸先红了。
麦克维伊太太说:“我倒是不怪他。我从来不问他,他也不喜欢别人刨根问底。不过有些时候,我……我有点儿怕乔。”
佛莱莫站在门廊上瞅着粉红色的绣球花丛,虽然夏天就要过去,它们仍在盛开。他想,如果能够握住麦克维伊太太那只沾着泥土的手,他会多么开心啊。
9月19日,有人用一把手枪打死了麦克维伊太太。夜间枪声很响,把麦克维伊家两侧的邻居都惊醒了。
枪声响起之前,邻居们有一阵听到有人以微弱的声音喊救命,于是便给黑利维尔警察局打电话。佛莱莫始终无法原谅那天晚上值班的警官,因为枪击事件发生后,他没有往佛莱莫家打电话。到了第二天早上,佛莱莫才获悉麦克维伊太太死了。
除了一名认真负责的警察应表现出的关切之外,在场的人从佛莱莫队长脸上看不出有丝毫异常。他以必须具有的超然态度工作,询问麦克维伊先生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不作评论。
乔·麦克维伊说:“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钟。格蕾斯醒来了,她说她听到楼下有动静。她总是听到各种响动,所以我叫她回来睡觉。她不听,披上睡衣自己下楼去查看究竟。这一回让她说对了,来了一个窃贼。他一定是吓坏了,一看到她便开枪把她打死了……听到声响我便出来,看到他跑了。”
“他长什么样?”
乔·麦克维伊说:“就是两条腿在跑。我就看到那么多。”
待调查结束,佛莱莫没有发现可以改变验尸官结论的证据,即身份不明的某人或某些人杀死了麦克维伊太太。佛莱莫不同意这个结论,却缺少那一点点证据去推翻它。他知道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是谁,他在梦中多次看到那张可恨的、嘴巴扭曲的脸。
太太死后不到一个月,乔·麦克维伊就处理掉这幢两层楼的房子,把它廉价卖给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有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之后他便离开了黑利维尔,有人说他去了芝加哥。从此,佛莱莫队长不再欣喜地盼着春天早点到来、百花再度盛开。
有一天,佛莱莫队长驾车去乡村转悠,在昔日麦克维伊的家门口停了下来。
站在门廊上的那个女人挥手招呼他,大捧大捧的蓝色绣球簇拥着她。若是人的心能够凌空翻转,此刻佛莱莫的心便是如此。他差一点儿大声喊出格蕾斯的名字,虽然这时他已看出那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体态丰满。
瞧瞧停在车道上的警车,这姑娘说:“你好!天气真好啊。”
佛莱莫呆板地应声道:“是啊。米切尔夫妇在家吗?”
她犹疑地笑着说:“他们不在家。我是他们的女儿安吉拉。我想你不是来这儿办公事的吧?”
佛莱莫说:“不是。”
“我当然也知道这所房子的事,知道去年这里发生的事,那件凶杀案以及一切。”说到这里,她压低嗓门道:“你们没有捉住那个窃贼,是不是?”
“是,我们没有捉住他。”
“她准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说麦克维伊太太。她可真爱花儿呀,是不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园呢。”
佛莱莫队长道:“是啊,她非常喜欢花儿。”
他悲哀地伸出手来触碰一下绣球花枝上的一朵蓝色花儿,然后转身朝他的车走去。他觉得自己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不过看东西却看得很清晰。
他突然站住,问:“蓝色的?”
那个年轻姑娘不解地望着他。
“蓝色的。”他重复道,走回来盯着盛开的绣球花丛仔细瞧,“去年它是粉红色的,我记得的,现在却变成了蓝色的。”
“你在说什么呢?”
佛莱莫说:“绣球。你懂不懂绣球?”
“我完全不懂花儿,只要它们漂亮就好。”
佛莱莫说:“粉红色的绣球很好看,可是一旦土壤里含有铝合金或铁元素时,它们就会变成蓝色的,就像现在这样。”
那姑娘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粉红的还是蓝的,又有多大区别?那就是说,土壤里有铁?”
“对。”佛莱莫队长说,“土壤里一定有铁。好啦,米切尔小姐,请你给我拿一把铲子来。”
她迷惑不解,不过还是拿来了铲子。佛莱莫在那丛绣球的根部挖出了一把手枪。枪管已生锈,扳机也无法扣动。这时,他脸上并没有现出洋洋自得的表情。
在人们弄清那把手枪的来历后,佛莱莫也没有欢呼雀跃。格蕾斯·麦克维伊正是被人用这把手枪打死的,而这枪是乔·麦克维伊的。甚至在杀人犯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之后,佛莱莫也未感到欢欣鼓舞。虽然没有大获全胜的感觉,但他还是承认,热爱花儿可以使人从中得到许多乐趣。
(九月风铃摘自《视野》200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