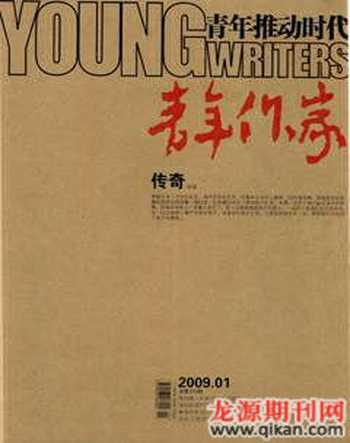理想的破灭——傅雷余话
……他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彷惶,你可不必彷惶。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万一有低潮来,想想你的爸爸举着他一双瘦长的手臂远远的在支撑;更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的在鼓励你前进!……
这是傅雷先生于公元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写给他远在波兰的长子傅聪家书的摘抄。很难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待这样的文字,而在当时不论是傅雷先生还是其他人,都在用这样的语言来描绘心中的希望。恰恰也正是这个时间,毛泽东对于旧式知识分子的厌恶到了某种极限。那种冷漠中的沉默让毛泽东很是担心,熟知历史的他自然知道周厉王弥谤的后果,也明白齐威王纳谏的效果,因此他果断采用了后者,令他没有想到的批评如此之多,言辞如此之严厉,作为领袖他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纳谏的问题了。或许对于领袖来说,偶然的刺耳之音,可以视为良方,群起的异音就是不详之兆。在中国文人和政治家的身份一直在混淆,五十年代初期的学者,还在延续民国那年月的思维。改变一种习惯总需要付出点代价,虽然今天来看,这代价有些大了。
郭沫若曾经有一段回答右派的话很有玩味: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不言本身就有罪,言了罪上加罪,右派即如此。就此一言,便能够表明郭老本是政治客而非文人。
一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二日,蛰居沪上的傅雷先生和夫人在公寓自缢而亡。中国现代的翻译大家选择了如此痛苦的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谓生不如死!
傅雷先生的死确实和他一贯为人的原则有关。这个书生气太浓的读书人,既然没有养成苟且偷生的本领,却选择了在大陆生活,这样的结局从他选择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只是我们无法回避他夫人朱梅馨女士的气节,面对死亡居然如此的坦然,山盟海誓的生死相约,有多少时我们郑重说过,但有几个能够真正相守。同赴黄泉,恐怕是人生最大的爱情浪漫曲了。
很久以后,在翻阅傅雷先生的文集时,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作为中国翻译巴尔扎克的权威,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的中国会员,傅雷先生为什么没有把巴尔扎克的小说全部介绍给中国读者呢?一度我把原因归结是时间,先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当然我还是有另一个推测在心底的,只是不敢或者说不愿去那样想,直到我开始准备写先生,收集相关资料时,才肯定了我心里的那个推断。
一九六五年十月间,在他写给曾在反右斗争中竭力想保护却又力不从心无法保护他的老朋友,时任文化部长石西民的一封长信中,谈到了关于上面的问题。其实傅雷先生已经把可以译成中文的“巴尔扎克”都译了,剩余的只是一些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他担心读者不能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批判而“中毒”,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
看到这里无法平静自己的思绪,甚至有一种东西在堵住人的呼吸。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竟然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不知道这些意识概念是中国读者的悲哀,还是巴尔扎克的灾难。
很多人误解傅雷,把他等同一个翻译家,甚至等同一个翻译巴尔扎克的中国人。其实翻译不过是傅雷的一个方面,这个固执的旧式文人,居然是中国早期艺术理论的开拓者,他对传统绘画理论的研究,深得国画大师黄宾虹人可,引为一生唯一知己,而在西洋绘画方面,他和刘海粟一起开创了中国西洋艺术最早的学校,从学校的建立到艺术的方向,都浸透了他的心血,甚至可以这样说,当初没有傅雷的直接支持和参与,刘海粟的辉煌或要推迟若干年或根本就是个未知数。一本《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显示了他对世界美术的卓越研究成果,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理论中的少有的重量级的论著。
当然,这些对于傅雷都是过往云烟的旧事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全心做的事只有一件,给儿子写信。傅聪从留学的波兰叛逃后,转道去了英国。这样的举动对当时的傅雷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神奇,不知是出于何种意图,出逃后父子间居然得到了长期通信的权利,并在若干年后,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至少到今天,国内或还没有任何一部《家书》能够与《傅雷家书》相比。无论是从文字上表现出的卓越成就,还是文字背后的浓厚感情。
很多年后,我们读到这些书信时,不得不心存敬畏,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面对一个叛逃在外的儿子,他没有义愤填膺,更没有断绝关系,以示自己的清白,而是通过种种途径,终于得到周恩来的首肯,与那个“逆子”通信聊天,讲艺术谈人生,探讨音乐讲解绘画,在如此敏感的政治氛围中,他这样的举动恐怕是国内的唯一。或是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吧,没有他的允许,这样长时间的异国同函是不可能的,不可否认这些书信既是若干年后的一本好书,更为傅聪的成长注入了动力,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钢琴家为西方人知道的中国人,也许真的只有傅聪这一人。
二
《傅雷家书》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傅聪的恋爱和婚姻,当傅雷得知儿子在与一个法国女孩恋爱时,表现出异常的兴奋。我只能够用这个词汇,因为这样的热忱出现在古董样的傅雷身上,除了因为兴奋,想来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而这兴奋确实是有理由的,当儿子替老子完成了某个心愿时,老子表现出满足之兴奋,实在是非常合乎情理。儿子傅聪娶了美丽的法国妻子,恰似他傅雷完成了当年的誓言。
确实很少人会想到,这场异国婚姻替傅雷圆了少年的梦想。因为傅雷夫妻间几十年相敬如宾的家庭生活,无法让不了解他年轻时代的读者联想到这个古板的学者,当初却是个地地道道浪漫多情的人儿。
年轻的傅雷在法国留学时,曾经与法国女孩玛德琳真心相爱,罗浮宫殿的雕塑旁,塞纳河边的草地上,都留下他们亲密的足迹,为了心中的艺术,为了神圣的爱情,年轻的傅雷甚至有为卿与家庭决裂的决心。
年轻的傅雷草率地给母亲写了一封要求与朱梅馨解除婚约,他要和法国女孩共结连理的信函,委托刘海粟帮他寄给上海的母亲。对于母亲傅雷是由心底而生惧怕的,来到法国留学完全靠母亲变卖了家产,自己如此的行为他知道母亲将表现出的态度。不过此时的他又完全沉醉于爱情的长河中,面对玛德琳的热情和奔放,傅雷的情感和情欲失去了理智和冷静。在他委托刘海粟寄信后,他的思想开始更激烈斗争,面对既有的文化道德理念,特别是他内在的道德衡量概念,迫使他行为与之前大变,这样的变化对玛德琳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内在深层的旧式理念束缚的傅雷,中西文化在爱情伦理上的鸿沟,是傅雷没有完成他对法国女孩许下的诺言。幸运的是,刘海粟没有如他所托寄出那封信,他在母亲和妻子面前都一如当年。假如当初海老发出了那信,傅雷的历史或者要重新改写。
随着塞纳河的流水逝去,傅雷和玛德琳间的爱情犹如昙花,终究只能一现。只是如此的挚爱是无法忘记的,甚至是铭刻在心的。当他真正进入法国文学的世界,对西方文化有更深层次了解后,他心中必定是生存一丝愧疚的。
因此,得知儿子的异国恋情时,傅雷的昔日思念一发难收,并完全倾注到儿子的恋爱和稍后的婚姻中。他热忱支持着儿子,还作为一个曾经留学法国的学生的经验,以及一个艺术家和文学家的修养,来充当儿子爱情的幕后军师。虽然这样的举动对年轻的傅聪是多余的,风流倜傥的中国翩翩美少年,又是才华横溢的新晋钢琴演奏家,爱情犹比鲜花,只要他付出真诚,其他的无需多虑。儿子婚后,傅雷又意外地主动与这位未曾谋面的儿媳通信,用他个人的知识,以及他的人格魅力,来融通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把一个中国长者的爱传达给西方的少女。可惜的是这位洋媳妇没有机会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公公,等到冰封解冻后,傅雷先生早已经魂归西天了。
三
傅雷先生屈死在那个年代,或不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悲剧,文化革命毕竟也是一场“革命”,所谓革命自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尽管真正付出这种代价的都是一些傲骨铮铮之辈。然而,像他们这样夫妻共赴黄泉的,并不多见。恩爱一生若算是人间美谈的话,如此真正“不愿同日而生,但愿同日而亡”选择,不知道该算何等的佳话。
在那场“革命”之后的很多文字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为屈死的人儿痛哭流涕的遗孀,她们满目怒容,满纸辛酸,却又安然在享受那个已经作古人的遗存。虽然她们未必不是与死去的人恩爱异常,未必不是真正的痛心疾首,但与朱梅馨女士来比,如此之后哭泣与哀怨,并化为纸上的文字,或多少有点做作的成分的。如同那些能够写到纸上的美景,都不是最美丽的,只有写不出,讲不清,画不尽的美丽,才是真正的美丽,就像李太白酒后仍然描抹不出黄山的风韵,苏东坡只能写出二流的诗歌来描摹庐山。
傅雷先生离开尘世的当晚,他就如同是离开一个正生活着的城市前往另一个地方,所做的不但要整理下行装,还要对一些事情做个交待。在他的遗书中,除了解释了一下“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背面有蒋介石的印像;一张褪色旧画报中的宋美龄的照片;都是别人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并封装在箱内,绝非他个人私藏。然后写下一段真情的表白:“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恐怕是傅雷这个书生,在其一生中最坦白最大胆的一次控诉了。一张旧画片就要引来杀身之祸,这样的社会活着真的比死去更艰难,那么还是早些离开吧。
之后,他竟然开列了十三条委托其内兄朱人秀办理的后事,内容琐碎到交纳房租,归还寄存之物,赔偿被抄寄存的损失,安置保姆周菊娣的生活,支付自己的火葬费用等等,但其中却没有一条涉及到他的书籍和著作。身心俱死,除了要交代一下人所应为的,其他都是无意义的了,这样的悲愤不知道是否人间最惨痛的一种。
傅雷夫妇的离世,在那时候不会引起丝毫的震动,他的朋友们除了唏嘘一声外,或是眼泪都不敢流一滴的,即便是他的儿子傅敏,接到朱人秀的电报,只简单地毫无感觉地回复了“父母后事请舅代理”八个字。不是傅敏无情,而是他不敢流露悲痛,不敢哭泣,不敢奔丧,只能把眼泪往心里驱赶。只有周菊娣这个做娘姨出身的穷苦人,敢抱着老夫妻的尸首嚎啕痛苦一场,指着那些人怒骂:“傅先生傅太太是好人,都是给你们害死的!你们真作孽啊!。”
很久以后,中国交响乐团访问伦敦,傅聪听到父母双双自缢而亡的消息时,这个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钢琴家,竟然没能够哭出一个声音,就昏死过去,幽幽苏醒后,唯有眼泪而无声响。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但此时从祖国来的音乐家,也不敢对他表示一丝慰问,甚至是一句“节哀顺变”的客套劝慰。因此当悲痛中的傅聪提出要回国祭奠父亲,得到的只能是沉默。
毕竟傅雷是“自决”与人民的,他依然是一根导火线,随时会让接触到他的人粉身碎骨。傅聪先生没有得到更多父亲的消息,但他能够体恤到这些来自祖国音乐人的处境,其实他也能够想象到父亲死后的状态,在那种时间里,父亲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隆重的追悼会,更不会有父亲希望的那种政治或艺术上的肯定。然而傅聪没有想到,也许所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预料,傅雷先生不但不可能有追思这样的集会,不会有当局对他人格或艺术的肯定,而且傅雷先生连死后的遗骸都不能够保留。
无法想象这样的残酷,也无法理解如此的野蛮,抹煞一个人的尸骨就真的能够磨灭了他的一切。愚昧到如此,也就那时代那些人了,或还不是的,如此的行为和动作,也算是有年头的历史了,也保不了若干年后,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还会再次重演。但所有这些依旧只能用愚蠢来形容。
傅聪先生如果在解冻之后回到祖国,无法在上海城找到他父亲的骨灰,不知道傅聪先生会是如何一番痛不欲生的悲愤。或傅雷先生九泉有知,不忍他心爱的儿子伤了中国情结,所以让一个年轻的女孩用其一生幸福,换回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不因为那点个人的恩怨来伤及对民族的感情。
一个先生文字的阅读者,一个曾经学音乐的学生,当她得到了先生屈死的消息,黯然伤心,她只是想去凭吊一下心中的偶像,却闻听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对于“自决于人民的傅雷”是没有资格保留骨灰的。一种良知,更是一种因不平而迸发的反抗,女孩毅然抉择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先生的骨灰。
同样是无法想象女孩拥有了何等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又是花了多少的心血与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取了保留下傅雷先生的遗骸,更无法想象女孩是如何度过往后的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忍受了多少凄苦和悲凉的生活艰辛,知道的只有一点,她不曾后悔过。
多年后处境潦倒的女子,见到了满怀感激和欲以图报的傅聪先生时,她只是淡淡一嫣,此刻对她来说,他们父子的相会,或就是她最大的成就。在傅聪先生的巨大诚意下,她接受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以释怀傅家的某种牵挂。相信傅聪先生是抱以万分诚恳之心的,特别知道女孩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而遭受到非人的待遇,以至穷苦潦倒时,他一定想尽一个人子的应为,诚意去帮助下这个有恩于他们傅家的女孩。但女孩还是没有接受,她在演出接近尾声时,悄然离开了音乐厅,并永远离开了傅家人的视线。
这女孩身上显示出的正是傅雷先生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