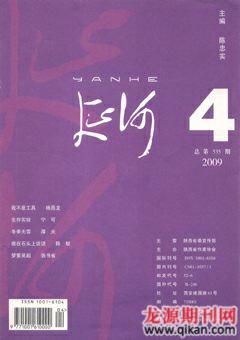冬季无雪(外一篇)
厚 夫
厚夫 本名梁向阳,1965年生,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散文理论奖”、“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等。
雪是冬天的娇女儿,冬天是雪的家园。试想一下,没有了雪的冬天,那还是冬天吗?然而,现在的冬天是个让雪儿有家难归的冬天。在这个没有雪的季节里,我的心田里滋长着一种怀念。
雨是在季风的作用下来到北半球的。正像报春的燕子一样,从大洋深处掠起,在飞翔中选择善待它的人间环境。这个适宜它们居住的环境,自然是草木茂盛之地,自然也是青山绿水之所。有了上苍赐予的雨,就会有郁郁葱茏的万物,就会有河流与湖泊,就会有农民金灿灿的丰收。而土地一旦失去雨水的关爱,那旱魃就破门而入,河水干涸,土地龟裂,万物嗷嗷待哺。君不见电影《黄土地》中那童山秃岭之间,烈日炙烤的大地,氤氲着飞扬的尘土。在这个绝望的背景中,祈雨的人们抬着象征着龙王爷的轿子,在山间狂颠狂奔,时而顶礼膜拜,时而辱骂鞭笞,企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榨取龙王爷一两滴可怜的“鳄鱼泪”。然而,这种劳动常常是无效的,百姓只好在苦难的年馑中挣扎……这种绝望背景里的绝望之戏,恰恰就是雨水的不作为造成的。无水之地的百姓也许会突发奇想,有一天把苍天捅开个大窟窿,那大雨如瀑,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当然,成天在雨水蹂躏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们,也许会想到在天上安装一个降雨开关,何时何地要求降雨打个报告那该多简单啊!
遐想是美丽的梦,雪虽然说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灵”,但她调动起人们的更多是一种情绪,一种诗意。秋风起了,树叶变黄了、落了,大雁们也踏上南归的路了,这时的人们想到冬天也就到了家门口。男人们忙着贮存过冬的粮食,女人们整理一家人过冬的棉衣,孩子们呢,也开始修理冰车、冰鞋,翘首期盼着冬天游戏大幕的拉开……
雪儿一般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初回娘家的。当然,事先老天爷也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酝酿感情,调整状态,蓄时待发。孩子们的心理也有个期望值,知道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雪的,至于下多大的雪,心里没谱。累了一天的孩子们在热炕上做起那神奇的梦去了,第二天推门一看,好大的雪呀,漫山遍野银妆素裹,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孩子们既不会像岑参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丽遐想,也不会像韩愈做出“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的大胆设想,孩子们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便满心欢喜地盘算着怎样打雪仗、堆雪人、套鸽子去了……
雪应该是大自然最杰出的化妆师,最优秀的想像使者。你瞧,那六瓣形的雨的精灵们,多么晶莹剔透,多么玲珑漂亮;你再瞧,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不像是一位姿态婀娜的神女么?雪花飘落到地上,并不立即融化,寻找她的最后归宿,而是用一双巧手善于掩埋众多的污垢,精心打扮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留给人们一个冰清玉洁的、平等而和谐的世界。显然,雪儿的创造性才能,对于渴望平等、渴望和谐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件喜事。现实的生活里,人们兴许有着种种的不如意,为什么就不能让雪儿为我们创造那片刻的欢愉与自由呢?
虽然说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这种意象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依偎,但是雪的好处似乎远比雨多,因为她是雨死而复生后的精灵。在雪的世界,富人们可以到滑雪场尽情地体验激情与浪漫,穷人们虽说没有这种福份,但也可以围着火炉尽情地想像着来年的生活。就是一位在田野里经营多年、双手布满老茧的乡村大爷,他也会在大雪的飘飞中呢喃着“瑞雪兆丰年”的古老谚语。即使穷到饥肠辘辘还可以像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姑娘一样做着自己粉红色的梦。有梦总比没有梦好,梦能激发人的情绪,煽动人的欲望,使人们重新投入创造……退一步说,冰天雪地与出行不便是暂时的,可一旦有了阳
光的亲吻,雪儿就会心甘情愿地敞开肌肤,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土地,带给土地的是积蓄营养的勃勃生机。由此看来,冬季无雪就像夏季里无雨一样,不只缺少一种独特的风景,更缺少滋育生命万物成长的源泉。
这些年来,一到冬季我就左顾右盼、左等右等,等待雪的出现。可是,雪儿就是迟迟不肯光顾人间。我不知道是谁戕害了她,让她远遁它乡、销声匿迹。雪啊,你让我的怀念与日俱增。
无雪的冬季,我只能翘首以盼。
心灵的边际
走了趟海南的三亚,才发现所谓的“天涯”、“海角”不过是几块大岩石。这些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岩石,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关键是好事的文人在上面镌刻了大大“天涯”与“海角”,它们才拥有了文化价值,变得生动起来,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于是,今天的游客们一拨又一拨,喧哗之语快要压过海浪声了,整个把一个应该让人静思的地方,快要搞成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了。许多游人才不管它到底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内涵,只是大老远跑来拍张留影照片,好回去夸耀而已。又想,倘若当时的文人在三亚的其它什么地方找上几块大石头,大书“天涯”和“海角”,那么今天的人们还不是乐不迭地跑其它地方去凑热闹?这样想想,也真是好笑。
话说回来,“天涯”与“海角”落户三亚,是有其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是与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或者“迁谪文化”有关。在古代,不要说海南,就是岭南也是贬官之地。唐代大文豪韩愈晚年因上《论佛骨表》而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被贬到今天广东东部的潮州,就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最后明示侄孙“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其当时的心情可见一般。而宋代大文豪苏轼先是被皇帝贬谪到岭南,后来皇帝还嫌贬到岭南不解气,直把他下放到本土之外的海南儋州。苏轼在文章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当时在海南岛北部儋州人们的生活状况便是这样,那么在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又能好的什么地方去呢!这样,三亚成为“天涯”与“海角”才有其合情合理的成分。三亚是海南岛的最南端,贬官们到了这里,向南那是浩浩淼淼、天水一色的大海;向北那也是关山阻隔、望穿秋水而不得归返的中原故乡啊!遥想当年,贬官们眼前是翻滚的怒涛,耳畔是如鼓的海潮,他们对酒当歌,一樽还酹海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于是,那些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海洋里徜徉恣肆的文人们,便利用这些在海南岛最南端被怒涛巨浪雕琢好的天然岩石,大大地镌刻上“天涯”与“海角”,来倾吐心中的块垒,表现一种茫然而无所依的心绪。这“天涯”与“海角”便成为他们最后的心灵边际,最后的心灵防线。试想,这道心灵的边际一旦被突破,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后果呢?所以说,“天涯海角”成为表达中国古代文人心灵边际的一种符号文化,而被传承下来。直到今日,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穿过遥远的时空而浸入心脾的一种文化魅力。
当然,今天的人们对古代贬官们评头论足,真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好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海南成为国内的旅游胜地,三亚也俨然成为一颗璀璨夺目的旅游“明星”城市了。现在谁说去“天涯海角”,人们觉得是一件快事。
这不,导游又动员游客们赶紧拿出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给妻子、给情人打个电话:“喂,亲爱的,我走到天涯海角也想着你!……”
责任编辑 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