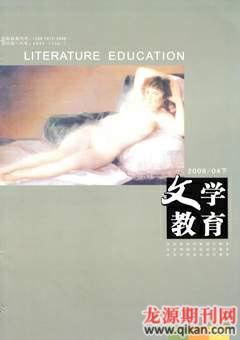秦观词的审美价值
被人们称为“婉约之宗”的秦观的词,虽然题材不外乎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自己的愁苦,但长期以来一直深得人们的喜爱,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词人抒发了真挚深沉的情感,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优美的艺术境界。
秦词局限于相思、相恋、愁苦几个方面,但却不是一般的相思愁苦词。由于词人纤弱的性格,更由于他飘若浮云、屡遭不幸的命运,使得词人往往借助艺术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的迟归之感,以及“暗随流水到天涯”(《望海潮》)的无可奈何的惆怅之情,也就是“将身世之感并打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秦词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的深切感受,创造出或清丽、或苍茫、或凄迷的优美意境。而这种优美的意境创造正是为了“情”,所谓景为情生,情由景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也。我们说,秦观词的境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先看《满庭芳》上阕: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蔼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在这首描写男女别离场面的词里,词人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当时的环境并表现出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山抹微云”两句就描绘出苍茫廖寂的境界。用“抹”字形容那轻轻地漂浮于山上的薄薄的色彩,用“粘”字表现出那一望无际,与远天相接的已衰枯的草。云是“微云”,草是“衰草”,微云被“抹”,衰草被“粘”,画面是何等苍茫!境界既扑朔迷离,又清丽明晰。山间淡云漂浮,天地相接为一,都属举目所见,眼前景物。接着“画角声断谯门”则属耳之所闻—城楼上若断若续的号角声。这样画面有动有静,有色有声,有物有人,妙趣横生!后面的“斜阳外”三句也是久传的名句,男女主人公征棹暂停,想得旧日所欢,满腹离愁,恰像迷茫的烟雾一般。而这时极目前程,又只有斜阳、寒鸦、流水、孤村。词人用“寒”、“流”、“孤”等色彩暗淡的动词,用白描手法,形象鲜明地绘出一幅斜阳荒远图。斜阳惨照,寒鸦凄啼,流水自去,怎不叫人触目惊心,况复离别之时。表面全为写景,骨子里则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哀叹。
从这些画面可以看出,词人笔下的景物,都成了人的情感的象征,思想性格的外化,一个极普通的、极平常的事物,便成为无限的东西。词人调动眼前的景物来表现自我,发现自我,用物来再现自己的精神。也就是把物象变成意象,把意象变成艺术形象。再来看看《望海潮》上阕:
梅英疏淡,冰凘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这首怀旧之作,开始写今,再写昔。起首三句总的描摹初春景物,与欧阳修《踏莎行》“侯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同一机杼。只不过秦词境界更为宽广。梅花渐渐稀疏,冰冻的水流已经溶解,春天不知不觉地来了……词人正面写来,淡淡用笔,抓住典型事物来表现物候的变化,清新、婉丽。下面的“柳下桃蹊”两句,则是词人回忆昔日极乐时的春景。浓春季节,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到处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独具匠心的词人不是一般地描写春日之美,而是写春色漫不经意,随便“乱入”人家。一个“乱”字就活画春色的无所不在,无处不存的情形。词人不写春色如何,而读者从“柳下桃蹊”的暗示,很自然地联想到柳絮飘飞,摇曳生姿,婆娑起舞;想到桃花满枝,香磬四溢;人们还似乎看到杨柳下,桃蹊上如云的游人……这一切不都是春的协奏曲、主旋律吗?这不是绝妙的艺术境界吗?人们常为称颂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画面幽雅宁静,以“红杏出墙”见出“春色满园”,当然是绰约生姿,但秦词提供的艺术画面更能体现春天的本色,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色彩更为妍丽。
我们说秦词意境悠远,婉丽含蓄,凄迷苍茫,他所提供的画面,或静或动,在朦胧中见清晰,与凝静中见新意。这种优美的意境既不同于王维的空寂静远,也不同于李白的豪放不羁,具有独特的风格。秦词的艺术境界,虽没有“澄江静如练”那样的静谧悠远,也没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那样的博大豪迈,但这是时代风气不同所造成的。而秦词同样能丰富人们的情感,引发人们的联想,也同样具有美学价值,只不过风味不同罢了。
张清湘,安徽蚌埠坦克学院中文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