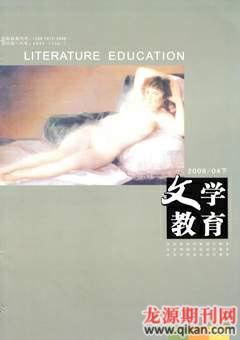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的苍凉感
五四新文学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纪末”色彩,这是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的问题。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写道:“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境,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1](p5-6) 鲁迅在此剖析的五四青年“时不我与”的焦虑颓废心态,应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世纪末情绪”。最先敏感触到世纪末情绪并极力推介的当属郁达夫,但真正把世纪末情绪发挥到极致的当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葩——张爱玲。
张爱玲在《传奇·序》中曾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中有这惘惘的威胁。”[2](p203) 张爱玲的思想背景中为什么会有这“惘惘的威胁”?为什么她能把这种世纪末情绪发挥到极致?
一、“家庭失落者”
父母是子女童年心灵的港湾,是情感唯一的依托,而张爱玲的童年却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与父亲一起生
活的张爱玲在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带着鄙视和愤怒,永远地逃离了父亲如古墓一般的家。投奔母亲,琐屑的难堪却轰毁了她对母亲罗曼蒂克的爱。至此,张爱玲成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家庭失落者”,人伦的亲情连同“父慈母爱”的“家”的观念一起坍塌。
如此不幸的家庭使她敏感早熟,让她过早地积累了对人事的否定性情绪。这是张爱玲建构小说世界之前,来自于她经验世界的基本心态。因而,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她以“家庭失落者”的心态,以“人世挑剔者”的眼光,无情地剖析着家庭的丑恶。《金锁记》中曹七巧凭着一个疯子的审判和机智,果断地葬送了儿女的幸福;《花凋》里的郑先生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女儿生命垂危,竟抱怨没钱养姨太,母亲担心暴露私房钱,宁愿女儿死去;《琉璃瓦》中姚先生拿女儿作筹码提升自己的职位;《倾城之恋》中白老太太对因遭受哥嫂的排挤和嘲讽,而向她哭诉的女儿无动于衷,冷若冰霜。
张爱玲在失落于家庭,逃离父亲又摧毁了对母亲的罗曼蒂克的爱的过程中,完成了她对人性的最初理解。她从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经验中,积淀了最初的人生悲剧意识。如果没有家庭的失落以及家族的沉落,她对这一切的认识也许该另当别论。然而,这一切却恰恰成就了她!
二、时代沉沦感
张爱玲曾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名列第一,后又入了香港大学,每门功课拿第一。发愤用功的结果激励了张爱玲的自立和自信,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了她的“自我中心”。但香港的战火却烧毁了她平静的书桌,烧毁了她引以为豪的学业成绩,她开始怀疑过去的努力与成就的价值和意义。紧接着香港十八天的围城,对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形成,对她精神上悲观气质的定型,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因此感到个人的渺小,已经建立起来的“自我中心”的自信受到激烈的冲击。同时,对自我的生命体验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生命是渺小的,有限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生的安危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在死亡的阴影中,个人的自立与自信显得那么轻飘和微不足道。
她曾在文章中多次表达由于这一战争形成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态度。“出名要趁早呀!”“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2](p203)这种急迫感流露出的是人生的荒凉意味。《倾城之恋》中,倾城的毁灭让范柳原刹那间决定娶白流苏为合法的妻,是文明的毁灭让他看到生命的渺小。而白流苏面对这样一个荒凉的外部世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烬余录》中她写到,战后的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且报上挨挨挤挤的均是结婚广告。战火、死亡去掉了一切浮文,人终于又回归于“大欲存焉”的食色本性。
在时代的危难中,张爱玲才真正看到了人生,生的无奈,活的荒谬,苦中寻乐,危中苟安,且“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3](p45) 如是张爱玲便在梅堂里看见男女同学的荒唐,战乱撮合了许多原本无意的男女,“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3](p45)
三、尴尬的女性写作
中国妇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抹煞了作为“人”的地位,沦为工具和附属物。她们不仅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还在精神和人格上受奴役。作为“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之一,张爱玲在其笔下展现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理世界。对这些女性悲剧人物的心理痼疾,张爱玲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出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和自我解构的新气象。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小说的开场写葛薇龙初入梁太太魔窟,紧张惶恐地试穿壁橱里的衣服,她明白这是梁太太的用心与伎俩,却终于无法抵御这物欲的诱惑,堕落成交际花。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悲剧的自审和解构具有重要意义。
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张爱玲小说世界里一贯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本位,始终没有产生相关的决绝的人生结论,不但如此,她们甚至未曾对此做过努力,只得任其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就像葛薇龙明知她的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4](p185) 而且从张爱玲自身来看,她也始终没有在当时个人主义冲激、女性自强自立意识抬头的思潮里,标榜过任何旗帜鲜明的主张。从一篇直见性情而思路凌乱的散文《谈女人》看来,当她抽离而且广泛讨论这个问题时,甚至产生了几分迷惑——这篇散文由男女不平等的环境归结到女性本身的缺憾与矛盾,以及缺乏对不平等主动反抗的意识,又由此而提出女性种种的美德。她注意到这种种社会现象,但是在寻求改善方法时却显得很混乱不堪。
四、爱情缺失的人生体验
张爱玲23岁结识了胡兰成,一向孤傲的她以为遇到了赏识的知音,飞蛾扑火般投向爱情,可惜遇人不淑,一再地遭受伤害。痛苦绝望的她毅然与胡决裂,却也萎谢了。然而,梦魇并未因此结束。之后,她遇到了身有残疾,经济条件差,生活不安定的剧作家赖雅,从此历尽艰辛而又疲惫无助,被人称为“落难才女”。
对爱情的渴望而不得的痛苦使她更敏感地体会到现实世界两性关系的虚伪冷漠,因此在她构筑的文本世界中,两性关系异化为原始本能的发泄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呈现的是一片感情的荒漠。她笔下的女性是一群迫于生计而寻找没有爱情的婚姻的 “女结婚员”,“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女人最怕的不是‘失业而是‘失嫁”。[5](p95)《倾城之恋》中范白二人虽有较完满的结局,却也是由香港战乱沦丧成全的,与爱情无关。《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琪乔在梁太太授计下与葛薇龙结婚,利用她作为高级妓女赚钱为自己开销,计划等她年老色衰后将其抛弃。总之,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千疮百孔,没有一样完美,婚姻也是彼此妥协,偶然偶合的产物。
爱情的失落,加上幼年时期亲情的剥夺,这些缺失性体验让她悟透了人性、人情和人生,也成为她一种持久的、稳定的人生态度。当她进行创作时,荒凉的人生感触就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从而使她的作品染上苍凉的基调。张爱玲是“人间无爱”的怀疑论者,文本透着彻底的苍凉虚无。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6](p18)这段话阐述了张爱玲对于苍凉的独到见解,然而正是由于张爱玲身处的家庭、时代环境,女性意识的不彻底以及情感的缺失性体验才成就了她这一番“苍凉”,也正是这番“苍凉”,让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世纪末”情绪发挥到极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
[2]张爱玲.流言·传奇序[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3]张爱玲.流言·烬余录[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4]张爱玲.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张爱玲.流言·谈女人[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6]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张文静,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06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