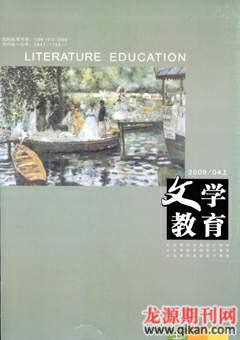信息17则
舒 坦等
●《纽约时报书评》再推中国专题
3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推出中国专题,介绍三位中国作家的三部新作:欣然的《见证中国:沉默一代的声音》、余华的小说《兄弟》以及李翊云的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本期《时报书评》的封面画作,亦全然中国色彩。在《兄弟》的书评中,杰斯·罗(JessRow)称此书“实乃20世纪末的一部社会小说”,但也指出,它超出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乃社会喜剧、市井粗俗和尖锐讽刺的混合体,尤其“充满了狂风暴雨般的语言和肉体暴力——诅咒,贬斥,乌眼青,痛殴——而且余华描写此种暴力时是如此写实,不厌其烦,虽经翻译过滤,仍然令人感到无法消受。小说结尾处的马拉松性爱场景沉闷而乏味,几乎令人无法卒读。”“这是否意味着《兄弟》是不可翻译的呢?”困惑的评论家写道,“也许最好是说,此书英文版的陌生感仅仅证明,中国与西方之间在普遍的意义和理解之间,仍然存在着何等宽广的鸿沟”。去年5月4日的《时报书评》,亦曾以专题形式介绍四部中国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以及姜戎的《狼图腾》。此事反馈回中国,一度引发许多人的好奇与惊喜。(舒坦摘编)
●李安欲将布克奖获奖小说搬上银幕
大导演李安有意改编布克奖获奖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将其拍成好莱坞电影。美国《综艺》杂志报道,李安正在与福克斯2000公司认真协商这一项目。《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为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所著,2002年获布克奖后成为全球畅销书,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40种语言。故事讲述从小在动物园长大的少年Pi·帕特尔与一头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在大洋上落难扁舟,漂流227天的离奇经历,因此被视为“不可拍成电影”的小说。难怪马特尔听闻好莱坞有如此雄心,亦“吃惊不已”。最初,小船上尚有一人、一虎、一斑马、一土狼和一猩猩。弱肉强食的内战很快爆发,土狼咬死猩猩,吃掉斑马,自己也死于理查德·帕克的血盆大口,只余小朋友与大老虎四目相对。少年为保小命,计划以六种方式弄死帕克,皆不灵,遂以智慧和老虎玩政治,不做武松做宋江,终于收服猛兽,安然横渡大洋。李安考虑用真人活兽出演,结合电脑特技。《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舒坦摘编)
●浙江一农民推出长篇小说
由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150万字长篇小说《芙蓉外史》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创作这部长篇作品的作者名叫陈晓江,是浙江省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的村民。芙蓉村是浙江省永嘉县陈氏聚居的古村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坐落在国家级风景区楠溪江畔。芙蓉村陈氏在楠溪为耕读世家,历来文风炽盛,文人雅士代相接踵。陈晓江的家族就一直生息繁衍在这个古村落里。陈晓江自幼年受家庭及当地瓯越文化的熏陶,酷爱文学。因父亲被打成“右派”,儿时的陈晓江一边读书一边干农活。高考落榜后,他走上自学成才之路,并选择了文学创作的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创作出长篇小说《芙蓉外史》。该作品系统、深入、细致地描述了民国初年到“文革”结束以后芙蓉村的历史。作品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集楠溪风俗民情、方言土语之大成。全书共分6部:《追源记》、《寻金记》、《归宗记》、《荒年记》、《争斗记》、《还乡记》。(舒坦摘编)
●各地开诗会纪念海子去世20周年
3月26日是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纪念日,一系列纪念活动也在这一天举行。海子生前好友西川和海子的读者将前往诗人故乡扫墓,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今年的主题也是“海子”;在上海,一群海子的读者聚集在909咖啡馆朗诵海子诗歌。海子去世20周年,诗人在家乡安徽安庆的墓地不久前也已经修缮一新。3月26日,海子好友诗人西川和北京的海子读者自发前往安庆海子墓地扫墓。活动组织者之一大仙说,除了扫墓,他们还将瞻仰海子故居缅怀诗人。这是一次低调的行动。为了纪念这位早逝的诗人,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每年都选在海子忌日举行。今年,2009第十届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的主题是“半完成的海”,主办方取海子最后一首遗作《春天·十个海子复活》之名将请来王家新、姜涛、胡续东、臧棣等10位诗人。由作家出版社选编的《海子诗全集》也将在这一天首发。在上海,诗人郁郁和一群诗歌爱好者将聚集909咖啡馆,以“909诗·歌会:海子廿年祭”为题纪念诗人,两位民谣歌手还将海子的诗作谱曲并现场演唱。(舒坦摘编)
●王小波《黄金时代》首现话剧舞台
4月10日至19日,作家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的《黄金时代》将被首次搬上话剧舞台,亮相解放军歌剧院。史可、赵奎娥、林京来、孙刚、董路等实力派演员加公众红人将携手演绎那段知青岁月。《黄金时代》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后,不少导演都曾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影视改编的探索,而“话剧版”却迟迟没有现身。对此,该剧编剧兼导演夏波表示:“王小波的小说风格独特、随意性强,其中有很多意识流、插叙式的手法,而戏剧则讲究情节的冲突、集中,这二者间其实存在矛盾。”为了能把小说更好地还原于戏剧舞台,夏波也颇费了番心思,“在编剧时,我对小说的多条线索进行集中,拎出主线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希望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能与我们的当代生活发生更多联系。但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充满作家语言特质的对白等都一一保留。”(舒坦摘编)
●张承志自称将不会再写小说
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张承志日前出席了其新书《敬重与惜别》的首发式,他称自己在以学生心态写作此书,还表示,比起小说自己更喜欢散文,称自己恐怕不会再写小说了。上个世纪张承志以写作《黑骏马》等小说而闻名文坛,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写作重点放在了杂文和散文上。对此,张承志解释说,小说必须有虚构口吻,而现在的自己已经没有这样的虚构心境,“中国现在是散文时代、杂文时代,读者更愿意看到的是真心话。”他说自己已不具备这样的虚构才能,恐怕不会再写小说了。《敬重与惜别》是张承志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作品,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在首发式上,张承志一直强调,与其说是一个作家谈论日本文化,倒不如说自己在写作中更像一个学生站起来在课堂上发言。“做个作家的感觉并不伟大,自我吹牛没什么太大意思。”(舒坦摘编)
●刘震云认为80后写作应从学好汉字开始
作家刘震云日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我觉得一个时代产生自己的文字书写者是非常正常的。凡是新产生出来的群体,新产生出来的文字,一开始都是要遭到责难的,但是新的总会慢慢变成主流的、中坚的、成熟的。目前80后作家的作品我还是读过好多,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对于新的元素、新的人类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对于整体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相对了解得比较少,广度够了,深度严重不足。另外对于艺术形式,比如像小说本身的研究也非常不够,我能看出他们的结构能力、情节能力、细节能力、语言能力都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胸襟和气度,动不动就骂人的人我觉得很难写出好作品。最后一点,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写错别字,一页纸如果有3个错别字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觉得80后写作是不是该从学好汉字开始!(舒坦摘编)
●陆天明称作家不触及当代是失职
作家陆天明在签售他的最新作品《命运》时接受采访称:“当代作家要关注当代,如果只写个人情调的东西,那干脆在家写日记、写情书好了。”当今文坛虽然很热闹,但缺少富有责任感的作家。陆天明认同这个说法。他说:“为什么人们会记得路遥,因为路遥用生命写作,每个字都充满作家的使命感。”在创作《命运》时,陆天明也付出很多。为了这部书,他大病一场,六七天高烧40度不退,人都虚脱了。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一部反映当代改革题材的作品,他首次将虚构的人物和国家领导人、真实的城市放在同一个历史平台上,这是从来没有的。陆天明从开写这部小说的第一天起,就坚持这部书一定要有史诗品格。他说:“首先是史,得允许作者直面现实。这么多年来,中国作家面对当代题材绕着走,怎么可能出大作品和大作家呢?我就是要去突破禁区,想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写改革。”说到作家责任,陆天明说得最多的是作家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责任。他认为,当代作家如果不能代表自己的祖国、民族与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失职。“在这个30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当代作家,有责任、有使命去表现这个时代,更要把这30年人民群众做的事留在文字中。”(舒坦摘编)
●梅子涵表示早期阅读不应有功利心
近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在武汉举行题为“爱上图画书”的讲座,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早期阅读需要文学读物,且不是功利性阅读。他说:阅读可不是为了孩子的所谓“成长”。“你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他长大、老去直到死掉?”他认为阅读是一种本能需要,和喝水、吃饭没区别。而“成长”一旦成为功利目的,会抹杀孩子童年阅读的快乐。梅子涵希望不要让识字记数充斥在儿童的阅读中。对国内新兴的图画书,梅子涵推崇备至。如湖北出版的《起点阅读》等大型图画书,他就赞赏有加,“这些文学类读物很有趣,也很有诗意,读起来非常开心。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给他读。”至于火过一阵的《三字经》,他不太赞同:“小孩在那里摇头晃脑,大人看了很开心,其实孩子什么都不懂,这样的阅读不该推广。”(舒坦摘编)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
据《联合晚报》报道,文坛再吹张爱玲旋风,继二00七年《色,戒》造成轰动后,号称是张爱玲最后遗作的小说《小团圆》出版。报道称,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在她过世十四年之后面世,在新书发布会上,请到“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从香港来台。出版社强调,这是张爱玲最后、也最神秘的作品。《小团圆》全书共三百二十八页,书中女主人公九莉的身世与张爱玲相仿,同是二十出头就惊艳文坛的新秀女作家;父母新旧观念的对立,与张爱玲父母如出一辙;男女主角的恋情更宛若张爱玲与胡兰成,可说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出版,正如同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带有浓厚神秘色彩。张爱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此书,直到去世前多次易稿,仅少数友人看过手稿,据传张爱玲曾希望销毁原稿。历经许多波折,《小团圆》得以出版。(舒坦摘编)
●苏童推出新长篇《河岸》
著名作家苏童近日透露,他刚刚完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河岸》,将在《收获》第二期上首发,并于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是苏童自3年前完成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的首部长篇。苏童坦言,他永远不满意现在的作品。“我认为想象力和题材是不会枯竭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满足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苏童一直对法国作家福楼拜重写《情感教育》的做法推崇备至,他说“我写《米》只花了三个月,以后老了可能也重写一遍。”(舒坦摘编)
●赵玫长篇新著《漫随流水》出版
作家赵玫的最新长篇小说《漫随流水》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洋洋洒洒近50万字的小说,被出版界誉为“一部女人的史诗”。作者立足最近40年沧桑中国的背景之上,尽职尽责地让女主人公将黑色的优雅和人性的反思演绎得炫目至极。每一番人生舞台的转换,都充满着欲求的选择,良知的拷问,乃至灵肉的挣扎。书中的人物并不完美,但却展现出绚烂的生命流程,漫随流水,犹如一江春水,流淌出当代女人心灵的感召,以及时代变迁中民族的深省。小说中唯一的女主人公,一个穿黑裙的女人。所有其他角色都是她生命中的过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生活境遇中,她所呈现的,都是和现实的高度合拍与完美匹配,同时也都深怀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哪怕她已经青春不再,美丽凋零。哪怕她的心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掩埋。这是个天鹅一般的女人。她的高傲和冷漠,学养与智慧,注定她只能是一只黑天鹅,并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她所代表的颜色,应当是人性中最晦暗的部分。所以女人可能是时代的宠儿,亦可以做时代的叛逆。于是一次次,她总是能适时地更迭场景,确立坐标,编织出新的人物关系,构建起新的爱恨情仇。没有人对她迷茫的旧往纠缠不休,但她却最终没能摆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舒坦摘编)
●张炜新作《芳心似火》出炉
作家出版社日前推出张炜的新作《芳心似火》,和之前《古船》《外省书》《浪漫与丑行》《刺猬歌》等作品书名之诗意、典雅、田园比起来,张炜的新作《芳心似火》的书名显得有些撩人。但是等你迫不急待翻阅时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的深刻、幽默与思辨,一点儿不亚于他以往的作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因为他的切入点起于爱情,便显得轻松愉悦,原来进入齐国的历史是如此漫不经心又让人过目不忘。副标题是“兼论齐国的恣与累”,因为书中大量涉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世情民俗。张炜谈齐,不是清言,而是为了议论当世,是为了观照今天。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张炜都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加以对照,发出他个性的声音。这位在文坛上活跃了30年的著名作家,著作近千万言,《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等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然而《芳心似火》的出炉,令评论家们刮目相看:在作者全部的文字中,还从来没有以如此迷人的、平易近人却又美丽绚烂如织锦的关于人类生存思想的表述。这表述是如此地清晰圆融,如此地朴素,如此地切近,如此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舒坦摘编)
●帕慕克处女作中文版面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处女作终于在写就30年后来到了中国。日前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透露,帕慕克的首部作品《杰夫代特先生》已由该公司出版,近日将在京城上架。《杰夫代特先生》的写作完成于1979年,最初的名字为《黑暗与光明》,帕慕克凭借这部作品一举获得了当年的国民报小说奖。1982年,该作品正式出版时更名为《杰夫代特先生》,并获得了《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受到土耳其文学界的瞩目。本书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家族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三部分描述了杰夫代特先生祖孙三代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据悉,本书是帕慕克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家族背景写成的,它不仅是二十世纪土耳其社会的缩影,同时也是窥视帕慕克个人生活的一个窗口。即便是在多年后,帕慕克依然对自己这部处女作情有独钟,在2006年的诺奖颁奖典礼上,他曾说:“我的父亲用极富感情和充满夸张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和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像此刻一样,站在这里,满怀巨大的欣喜,赢得这一奖项。”(舒坦摘编)
●杜拉斯《情人》姊妹篇引进出版
有着《情人》姊妹篇的《平静的生活》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平静的生活》是杜拉斯的第二本小说,绝望的爱、时时笼罩的死亡,正是杜拉斯笔下永恒的主题,因此也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作《情人》的姊妹篇。故事发生在偏僻的乡村中,弗朗索瓦丝在孤寂中渴望生活,渴求爱情。舅舅与弟妹私通,她向弟弟告发,舅舅被弟弟打死;弟弟的情人爱上了她的情人,弟弟绝望自杀;她逃离到海滨城市,却又在阳光灿烂的沙滩上目睹一个男人溺水身亡。感性而清醒的语言,笼罩在死亡阴影中的情节,生活就在表面的平静和内心的挣扎里缓慢又迅疾地逝去。玛格丽特·杜拉斯本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印度支那,在那里度过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1943年,以杜拉斯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从此步入文坛。以电影《广岛之恋》和《印度之歌》赢得国际声誉,以小说《情人》获得当年龚古尔文学奖。(舒坦摘编)
●耶利内克新话剧《一位商人的契约》上演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奥地利银行界近年来发生的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丑闻,奥地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女士奋笔疾书,写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新剧本《一位商人的契约》。耶利内克女士集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于一身,其作品文体很难定义,常游走在散文、诗体和戏剧脚本之间,时而讥讽,时而咒骂,时而批判,还包含了剧场和电影般的场景章节。最近奥地利文化界人士聚集在维也纳学院话剧场举办了《一位商人的契约》作品的朗诵会。朗诵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作品广受好评。德国科隆市话剧院也将于近日首次上演《一位商人的契约》。(舒坦摘编)
●村上春树新长篇涉及二战
日本新潮社近日宣布,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新作将于今年初夏上市,书名定为《1Q84》。然而出版社方面并未透露更多信息,反倒是村上春树本人在国外对这一新作说了不少。村上春树在西班牙证实,他欲以此书向奥威尔致敬。不同的是,“奥威尔写《1984》是预言未来,而我的小说正相反,我回溯过去,但仍然在讲未来。”村上说。此书非常有可能涉及“二战”时日本的野蛮侵略与可悲战败,或许比以往更多地涉及政治,但不会成为《1984》那样的政治小说。正在西班牙访问的村上春树向西班牙《国家报》透露,他启程出国前,刚刚将其新长篇《1Q84》的书稿交与出版商,“这是我最长、也是最雄心勃勃的作品,花去了我两年时间。”《1Q84》书名古怪,令人联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事实上,在日语中,“Q”与“九”同音。(舒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