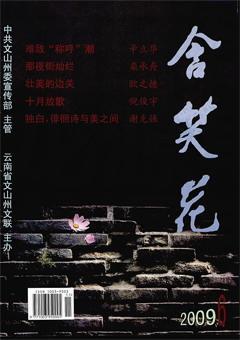江南乡菜(三章)
陶方宣
蒌蒿的工笔之美
在江南,春天的蒌蒿有一种工笔之美。美的感觉是汪曾祺带给我的,早年读他的小说《大淖记事》,文字似乎用雨水洗涤过,人物仿佛用工笔描绘过,沾着水乡的晨露与草叶:“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一”
仿佛萎蒿就生长在汪先生笔下,纸上——初春,只要落几场雨,烟雨中,江南河滩上池塘边,一地萎蒿青青——蒌蒿长于临水之地,在其它草木刚刚绽出新芽时,它起了一片绿,远远地看就像一片烟,浮着,水带不走,风吹不散。这时候,牧童便去河滩上采摘,雨稀疏地落,小小脑袋上扣着竹笠,犹如硕大的蘑菇,老水牛沿河岸咀嚼,一只雪白的鹭鸶独自立在水中央,像哲人般思考。
汪曾祺说:“萎蒿是生于水边的野革,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萎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一”蒌蒿有一股清香,采摘过后放过一晚,便老如细棍,所以采摘萎蒿要赶早采,赶早提到露水街出售,一见到青青蒌蒿,便知道又一个春天姗姗而至。蒌蒿采回,重新摘过用开水焯一下,放入臭干子,淋上麻油,那种特殊的香味分外诱人,江南人闯到就要流口水。此时一般人家皆储有半透明的冬腊肉,腊肉干丝炒蒌蒿,佐饭下酒皆是美味。在那很短的季节里,又常落雨,烟雨中,江南万千傍水的古镇,一家家隐没在桃花柳阴小饭馆里,你都能找到这道蒌蒿炒腊肉——坐在临水楼窗前,点一碟蒌蒿端一碗黄酒,江南细雨千丝万缕,江南杨柳柔情缠绵,一两朵油纸伞,三两声黄梅调——酒还没饮人就微醉,此时惟一的念想,便是荡一叶扁舟在桃花夹岸的河流上归隐。
蒌蒿的蒌字很多人不识,读成楼——汪曾祺特地标注:“萎蒿的蒌字,我小时不知怎么写,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才知道的。这个字音吕,我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萎蒿薹子——许多从娄的字都读吕,如屡、缕、褛。”蒌蒿二字我从没有读错,这是故园野蔬,我将它当成同乡,在我生活过的地方,它亦形影不离一路生长:芜湖、南京、上海——有时在菜场见面,并不购买,只是拿起它闻闻那股清香,一如见到老乡打个招呼。
蒌蒿茎紫红纤细,碧绿的叶细长狭小,生长在草滩的萎蒿有一种工笔之美,一直想着将它画下来,然后再配上苏东坡那首著名的蒌蒿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苏氏笔下,烟雨江南尽显工笔画的柔美与清丽:萎蒿、芦芽、竹枝、桃花,还有春江以及不时泼刺跃出水面的河豚——这样想着,我的心就如同一只乌篷船,晃晃悠悠悠悠晃晃,仿佛荡进某个蒌蒿滩头,扑鼻的清香就是我无边的乡愁……
苏州的清淡滋味
汪曾祺说:“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都放那么多糖,包子里的肉馅也放很多糖,没法吃——”无锡菜的甜蜜没有尝过,苏州菜的清淡倒是甚合我心。
我去过苏州多次。从上海去苏州比去浦东还方便,记忆里它就像一片荷叶,漂浮在南方流水之上,这是个惟美的地方,桃花太艳,女人太俏,茶馆太多,书场太密,歌曲太软——还有,还有就是美食太淡——清淡的淡。苏州的美食多得数不过来,仅仅是小吃点心就名目繁多,采茉莉花时和插栀子花时吃的点心是不一样的,剪梅花时或打桂花时尝的点心又是不同,季节性表现在苏州小吃上特别明显,比如艾草青青时,就能吃到艾草绿汁染成的清明糕团,桂花芬芳时,肯定能吃到桂花糖藕,那又香又糯的桂花糖藕就用棉布围在木桶里沿街叫卖,多是一些头插桂花的女人,一边走一边敲着竹梆,这样的美食看着就能大饱眼福——它又是农耕的怀旧的环保的绿色的,符合人文情怀与现代理念。车前子写过苏州奇奇怪怪的小吃,什么梅花脯、海棠糕、蟹壳黄,还有扁豆糕——小贩们提着竹篮在书场戏院等人流集中的地段站着,也不叫卖,就在那里静静地守候,他的心是笃定的,相信老苏州会闻香而至——是的,那种独特的香气老苏州一闻见就馋得要流口水,他们知道扁豆糕上市了,像蜜蜂闻到花香,嗡嗡飞来。扁豆糕制作过程好比一种美的仪式:将扁豆籽蒸熟,滚压成粉再加糖炒过,以此作坯再制成糕。糕分两层,下层掺了草汁为淡绿色,上层是掺了薄荷的米粉为乳白色,吃时抹一点玫瑰酱,为粉红色,拿在手里,淡绿乳白粉红,好看极了,吃到嘴里一片清凉。初夏时节坐到开花的槐树下吃,小蝴蝶一样的槐花啪达落下一朵,啪达又落下一朵,再看一个苏州女孩子从对面石桥上姗姗走过,那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一瞬,恍若初恋。
汪曾祺记得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一提起塘鳢鱼,立马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鳍如蝶翅。苏州人做塘鳢鱼有清炒、椒盐多法。”我在苏州找不到汪曾祺爱食的塘鳢鱼,却找到一种蒸馄饨,馄饨蒸着吃怕只有苏州才有,先将牛肉素菜馄饨蒸熟,配一碗蛋皮汤和麻油香醋来吃,兼有烧卖、馄饨、汤包三种风味,吃起来有风味也有趣味。还有一种灰汤粽,精巧如红菱,颜色为灰色半透明,不蘸白糖,浇一种特制的糖油,这种粽子现包现煮现卖,许多人排队,长长的队伍从小巷拐到大街上,拐到肯德基门口,肯德基食品哪里比得过它?包粽子的老婆婆大概习惯了这种场景,任凭人催,一点也不着急,老半天包一只,老半天包一只,动作里有着一种苏州人才有的悠闲与笃定。
苏州是出美食家的地方,已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就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美食家》,把苏州的美食写绝了。其实苏州作家也是一道道点心、小菜:陆文夫、范小青、苏童、车前子——他们不是麻辣火锅或生猛海鲜,而是滋味清淡的江南乡菜,一律装在青瓷细花的碗盏里……
红萝卜的花样年华
红萝卜给予我的记忆全是美好的花样年华——胖胖的身子像裹着臃肿的红棉袄,长长的根须像女孩子的发辫,翠绿的萝卜缨像一条绿裙子,整个就是正月里一身喜气的乡村姑娘,稚拙的,农民画式的,犹如梵高或高更,甚至陕北窑洞里那些剪纸、泥塑的大爷大娘。
我们老家叫它杨花萝卜。杨花像雪花一样飘飞时,红萝卜离开菜园,装在竹篮里来到街市,犹如村姑出嫁。我常常会拿一个在手里看,舍不得切开。红萝卜切丝凉拌浇麻油,滋味最美;当然也适宜煲汤——汪曾祺说:“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徊嫩,不糠;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这个台湾女作家就是琼瑶,我猜想当年的琼瑶大婶一定吃得眉开眼笑,说不定还漏出她的口头禅:好好喝哎。或者是:好靓好靓的汤哎——可惜除汪老外没人听到,汪老太听到也不会吃醋,她不会想到这个团脸短发的家庭妇女写起《情深深雨蒙蒙》来,会把全中国的女孩子弄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杨花萝卜炖干贝我克隆过。哪年春天,杨花飘飞如雪的时候,我到上海郊外访她,把所有的废话都说完后,我说:给你露一手吧。我在市场上找到杨花萝卜,它红得像糖葫芦,像爱脸红的小姑娘。菜贩叫洋萝卜,中间少了一个花字。将萝卜切片在锅里干炒,炒到微微发焦。干贝找不到,河蚌倒正上市,就用它代替,放在砂锅里娄叶炖,没一会儿就有腥气扑鼻,黄酒和姜块压不住阵脚,三只苍蝇闻腥而至翩翩起舞。这是料定的事,我就切半碗咸肉投入,果然腥气全无,丝丝幽香弥漫起来。一下午我就守着砂锅,在咕嘟咕嘟自言自语的唠叨里,埋头看完了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又随手翻翻琼瑶的旧作,最后打开盖子看一看,浓香软烂,清腴嫩滑,是一种很少有人尝过的独特滋味,一如汪曾祺随笔或沈从文散文。我一连喝掉三杯花雕,觉得自己就是汪曾祺了。醉眼朦胧中,就权当她是琼瑶吧,可她老大不情愿,跟我开玩笑说,她宁愿做亦舒。
汪曾祺对杨花萝卜入痴入迷,“这个名称很富于季节感,我家不远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檐下,有一个岁数大的女人摆一个小摊子,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萝卜总是鲜红的。给她—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几句话又让我想起乡间的红萝卜,杨花飘飞的某个早晨,我带着一队孩子踩着露水去拔萝卜,胖胖的红萝卜睡在菜园里做梦,红萝卜一样的孩子们拔起一只只红萝卜,面带惊喜,高声尖叫——
本栏责编张邦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