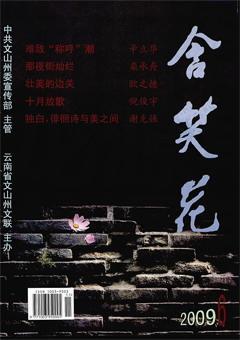壮美的边关
欧之德
到马关去
从清晨登上昆明飞往文山的飞机开始,心就一直在激动。虽然,马关那地方我只去过两次,而且至今已相隔20多年,但提起那片土地、那个地名,总会情不自禁地牵扯出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那些充满青春活力和战地激情的往事。我相信,当年在滇东南那片土地战斗过的军人,都不会忘记这些刻骨铭心的地名: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滚滚硝烟熏染过的地方。
到马关先要经过文山。飞机在一场夏雨过后的天空朝着文山飞行,天宇显得格外宁静安详。清晨的霞光抛出几抹金色而柔和的弧线,堆堆云絮,绵延光晕,在无垠的碧空抹染出一片流动的天景。不过,心中所想的还是马关,与同机邻座的同事谈的话题也是马关。
半小时,仅仅半个小时,一番破雾穿云后,飞机掠过具有文山特色的座座青峰,平平稳稳降落在被称为“普者黑”的文山机场,文山州文联主席周祖平和马关县文联主席欧阳厚尧已在机场迎接,下飞机后来不及进城吃早点,即刻转乘汽车,向着还有73公里的马关县城飞驰。
撩拨人心的马关,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对,就是这条路,通往边城马关,通往马关前线。只不过20多年前根本没有平坦闪光的柏油路,那是一条坑洼不平的碎石路。路上全是覆盖着草绿色伪装网的解放牌军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烟尘滚滚,腥风猎猎。路两旁的树叶、庄稼被飞扬的尘土染成了土黄色。
马关,祖国南方的重要大门之一。
“关”者,关隘、要塞也。在云南,在中国,凡是称“关”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防卫重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住一“关”,八方平安。史书记载,马关这一“关”,设于雍正六年,距今280余年,先是在一个叫白马寨的地方修筑城墙,叫马白关。而当初的县名叫“安平”。据说后来发现贵州也有个安平县,不管谁先谁后,云南的“安平”主动谦让,将自己的马白关“精兵减政”去掉一个“白”字,留下“马关”二字为县名,那是民国2年(1913年)的事。于是,“马关县”风风光光延续至今,既是县,又是“关”,闻名知古,鉴古知今。
马关是一道真正的国门雄关,一片著名的英雄土地。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留下的是战场遗址,是边关史料。长期以来,马关人心系疆土,血洒青山,巨大奉献和牺牲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安宁和平富足的边陲。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在那场举世瞩目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稳边固防”的战争中,马关县就有126个集体单位、1012名个人荣立赫赫战功;5个单位、5063名个人受到嘉奖;7个集体和7名个人分别被授予英雄、模范称号;13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293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数字还远不止这些,一个“支前”的军事术语,从革命战争年代就一直是中国人民广泛投入正义战争的自觉行动。行动的内容在马关县具体为:抢运伤员、警卫堵卡、封锁边境、运送弹药、抢修公路、物资保障、安葬烈士……口号是“全民总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感谢当时的统计员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组支前数字,仅一个公社的支前点,70天内就供应参战部队粮油612万公斤、肉食6.75万公斤、蔬菜17.5万公斤、禽蛋1350公斤、红糖1675公斤、各种罐头100余件、日用商品100余种……艰难岁月中的过来人知晓,那时贫瘠黯淡的边疆,物资何等匮乏、民众的物资供应何等短缺。不畏牺牲以“支前”,勒紧裤带以犒军,山区人自己吃不饱,城里人吃粮凭定量,吃肉要肉票,可怜家中娃儿们馋得流口水,却慷而慨之“省口待军”贡献前方,马关人的行为感动前线,感动后方,一个响当当的“支前模范县”称号当之无愧。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一串串光闪闪的数字和故事留给这个边境县一个永久的殊荣,一枚太阳般大的军功章。
现在,循着当年的车轮,我又旧地重返了。
往事沧桑,流水渐远,但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没有淡忘的马关人“支前”的细节。
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就是在这条公路上,数十辆军车溅起满地的泥水向马关行驶。喇叭声急,马达声咽,宁静的山水被火急的军情搅碎,窄小的路面拥挤着钢铁般的长龙。突然,一支马帮出现在前头,大约二十多匹骡马朝公路走来。马驮上驮的是一捆捆木柴。前面一头高大壮实的领头骡,额头上装饰着红色丝带和两个橙黄色的小绒球,正中间镶嵌着一面银光闪闪的小圆镜,像古代战将胸前的护心宝镜。由于马队急于停住脚步,一片骚动,有的竟往回跑。互相碰撞中,脖子上的铃铛声“叮咚咚”、“叮咚咚”,在雨雾中发出一串串惊惶的响声。
车队嘎然停住了,准备让马帮先通过。没想到,马队也停住了,并突然又是放鞭炮,又是敲锣鼓,似乎是在欢迎解放军的车队。“父老乡亲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此时,只见一个体魄强健的马帮头模样的人跑到最前面的一辆军车前,对着带车的人说了一阵话,接着,对讲机里有命令传下来,汽车继续前行,经过马队时必须按喇叭。所有人的理解当然是答谢人家的欢迎。然而,完全错了,车队到了目的地才知道,那是地方的一个支前骡马连在训练自己的骡马队伍。山区的骡子和马没见过公路,更没见过汽车,这个连队接受了“支前”任务后,得让身负重任的骡子们、马们先见见世面,适应公路、适应汽车、适应枪声炮声。因此,才把马队赶到公路边,放鞭炮,敲锣鼓,听汽笛声……
当年,我就在这支车队中,并就此事写了一篇散文《一切为了前线》,在《解放军文艺》发表。阵阵马蹄叩响边关,叩响前线,这只是马关支前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尽管时过境迁,但那音符却长久定格心中。那地方似乎叫坡脚。只是,现在只有康庄的柏油大道,何处去寻找那既害怕汽车又要远征的马帮?
战争这个词,从来都有着某种庄重感。它是一种国家利益的体现。在人类战争的纪录上,战争总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思索。马关人披载着浓浓的国家意识,显示了他们的无私和勇敢。当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打仗,人们最终从战争的重创和启示里走出来,将战争留进史册,然后洗去硝烟,继续发扬着家国意识精神,在建设新家园的大道上前进着。
寻找马关
难以寻找的不仅是那些马帮,还有那个当年的马关县城。
现在,呈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马关新城的夜晚,灯火辉煌,霓虹闪烁。宽阔的安平广场白炽如昼,广场上的人群或闲庭信步,或舞蹈自娱,歌舞升平,一派祥和、一派福景。
我还是迫不及待要寻找记忆中的那个马关,那个古朴而曲径通幽的马关。在我的记忆中,马关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拽着当地文联的欧阳厚尧、周祖平、张邦兴等人,迎着幢幢高楼投下的万家灯火,去寻找马关的旧街老房。
依稀记得,不,肯定地说,那时的马关县城没有洋气的高楼,没有喧嚣的舞厅,更没有往来的车水马龙,只有几条青石板铺成长长的街道,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两旁的店铺是一排排木板房,有的已经歪斜。街上偶尔一只狗或一群小鸡大摇大摆走过,
一副悠哉游哉、旁若无人的样子。店铺内显得很昏暗,也很简陋。货架上陈列着不多的当地土产:草果、八角、干蘑菇以及解放鞋、塑料凉鞋、两角多钱一包的金沙江烟等。阳光从密密匝匝的长满青苔的瓦房上投射下来,挟裹着雨过天晴、下午时分的清新凉爽,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空荡。即使那时是“战争时期”,古街古道也如梦如烟,深邃悠然。临街多数人家堂屋的正面墙上,都并排贴着两幅领袖像:一是已去世的毛泽东主席,一是已经卸任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大概老百姓还不知道外边政治时事的变迁,现任领袖是胡耀邦啊。或许,他们懒得去取下来,天高皇帝远,管他呢。还有,几乎家家堂屋上方都有一个“天地国亲师”的牌位。那时,文革批判“孝子贤孙”的流毒还存在,“天地君亲师”看起来很刺眼,还有点“封资修”的味道。不过,马关人很聪明,把本是“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国亲师”,不效皇帝效祖国,你没说的吧?
面对眼前的满街霓虹闪烁,满街灯火辉煌,满街“发廊”“数码”,欧阳厚尧说:这就是你要寻找的当年的老街道。再一条条走下去,货郎街、板子街,兴隆街,全是一个人头济济的不夜之城。“老”在何处呢?只不过比起我们下榻的马关宾馆那一带的道路更窄一些罢了。感叹重重中,显然在我记忆深处的那个“马关”已被眼前的繁华取代了。其实,我与当年的马关也只是一面之交的那种“怀旧情结”,马关今日的变迁应该在意料之中。新崭崭的马关,给予我心灵一种深切的抚慰和欣喜。
点击马关
这次在马关的几天时间,尽管是“走马看花”,但我还是认认真真看到了一个个内蕴深含、外貌巨变的经典诱惑。
我真没想到,马关农村的山山水水也变得如此美丽迷人。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绿色的牧场。青山隐隐、峰峦重重,几分清瘦,几分苍莽。群山、丘陵郁郁葱葱,一片生机,一片浪漫。近山墨绿,远岭淡蓝,车在青山绿树、岚雾轻盈间行驶,时而有水库如天镜降落又映照蓝天,牛群如绅士般在碧草茵茵的牧场悠然自得,好一幅美丽如画的自然山水。真正是“狼烟已不复,祥和在边关。”
那个叫“古林箐”的地方,当地的宣传材料上称为“天然氧吧”。苍莽的原始森林覆盖得那样地自然如初,新我如故。进山时大雾茫茫,开着车灯顺着林中小道缓慢移动。到了森林深处天气骤晴,初夏的阳光斜射进那些参天树丛,投下一道道光柱,愈发显得幽深神秘;散射光则在草坪上渲染着浓淡不一的鲜嫩。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长筒靴的农民从森林中走出来,背着个化肥口袋,嘴里悠然地叼着一根烟管,友好而好奇地边走边看我们拿着各式照相机疯狂拍照,似乎在说,这伙人疯了,这么难走的路,这么大的雾,跑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他或许压根没意识到他生活的地方这么美不胜收。另外两个一个戴着斗笠、一个戴着毡帽的农民,则蹲在路边,转动着纯朴生动的眼睛,对我们顾盼频繁。他们身旁的一匹白色公马也歪着脑袋哲学家似的看着我们,样子很滑稽。其实,他们是森林的主人,此刻也是森林的点缀;因为不少照相机对准了他们,他们有几分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走了。这雨后的森林的确非常漂亮,她和密不透风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一样,这儿更显得整体的潇洒清秀,苗条柔媚。林中的空气清新得吸进肺里都是甜丝丝的。我将照相机镜头对准那些不被人注意的细小部位,倒成了一幅幅“艺术品”。一张蜘蛛网,上面缀满了亮闪闪的“珍珠”;一片椭圆形的绿叶,不知名的小虫居然在上面“绣”出了金黄色的人字形图案;古树上的一片青苔,放大后也像一张毛绒绒的绿毯上开满了细小的星星之花。
怪不得,这片森林所在的乡叫“古林箐”,太名副其实了。菁中的古林是一个旅游的宝地。
还有仁和镇阿峨新寨独具特色且内容丰富的农民版画,我本不想再“点击”,因为不少人已经浓墨重彩地写到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何为艺术珍品?“物以稀为贵”即为“珍”。“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之所以“贵”,就是保存下来的越来越“稀”。但是,试问那些古代绘画珍品中有多少是出自农民之手?而且是少数民族之一的壮族农民之手?有多少珍品是表现实实在在的农村生活场景?古代留下来的绘画内容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宗教故事神话传说。而出自农民长满老茧之手刻画的犁地播种捕鱼捞虾等场景,无疑是被人轻视的。然而,马关阿峨新寨的农民不轻视自己,也不轻视自身的生活,他们专心描绘的被一些人不屑一顾的这些作品,不仅是具有农民特色的艺术珍品,而且还是农村生活珍贵的历史史料。我家墙上就挂着一幅阿峨新寨村民卢正刚作的《金秋》,两个壮族夫妇正在用风车(我的家乡叫风簸)扬谷。我是农民的儿子,很喜欢这幅生活气息十足的乡村风情画。但我上大学的女儿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认识“风车”。我想,若干年代后,当农村的风车、犁耙、打粮食的连枷等旧式农具完全退休并被当破烂抛弃完后,恐怕只有在这些画面上寻找到它们的形象了。因为“电”这玩艺已经代替了这些传统古朴的工具。
在马关,还有另一种古老内容的农耕文化。在一个叫马洒寨的地方,居然保留着一个“先农亭”。严格地说,那不是“亭”,是一间不大的木头房偏厦或者小廓。“亭”中有一块红底黄字、而且是繁体字的“神农殿”匾额。它对面还有一块匾额书写着“进士”二字,这是当地有“读书人”的显赫。也就是说。神、人共一亭,农、文共一家。先农亭不大,约有二、三十个平方米,却建于1831年。文革时被毁,当地民众于2006年修复。亭内正面墙上有一牌位,青石雕刻而成,造型优美,花纹醒目,斑驳中闪着岁月磨砺的光泽。显然这是件“乡村古董”。牌位上的小字已经模糊不清,上下对联尚可辨认,大概上联是“永赖农功於后世,”下联是“因开本业在富年”。可能是一种勉励的意思。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里的农民至今仍然像这首古诗一样生活着。他们和汉族一样,千百年来一直崇敬着神农,他给人类带来了农作物种子和农耕技术,他成为“神”,他是农民心中的图腾。但在这儿,他更是一位普通老人,他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而像家中供奉的“天地国亲师”牌位一样,人们像崇尚一位有种地经验的老师一样崇尚他。供奉他老人家的也是壮家人过年过节和招待贵客吃的“七彩饭”,红、黄、紫、蓝、绿、白、赭,是从各色植物土法提取的纯天然色彩,将普通的糯米饭染得像五彩晶莹的宝石。这种壮家人一代代遗传下来的尊农、崇农意识,自然是数千年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农耕民族古老文化的源头和这位俯视天地、生活简朴的神农老人分不开。在壮家人心目中,他远远高于一切“神”的地位。才有在这边远村寨保护了一百多年的“神农殿”,使人的确为之一振并很感动,它与阿峨新寨那些推磨、扬谷、犁田的农民画一样,是农耕文化的珍贵遗产,千万不可轻视。
怀恋马关
苍灰无语的长空下,竖立着两块界碑,一块已经颓废或者死去,那是大清王朝与法帝国主义立的,就
像一个老朽的枯髅,灵魂和肉体都已经剥离本真了。一块为公元2001年立的,标号197,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战争以后的外交成就,在边关的劲风入怀中飘扬着新国界的威严。一座残破已久却还很坚固的拱型“关门”,也是大清王朝留下来的遗物,想必那时是有大辫子清兵把守的。马关的“关”,古时候当主要是指这儿。如今的萋萋枯草,累累裂痕,遮掩不住当年一个王朝的尊严。那些守关的兵士也好,土勇也好,在这如今也还很荒芜的地方餐风宿露,戎马一生,还是值得人钦服。站在古老的关碟上极目四望,近山巍巍,远山淡淡,中间颇为开阔。阵阵山风掠过峰峦,国界两边感受到的是同一种清凉,同一种爽怡。中国—侧是两排歪歪旧旧的油毛毡房,似乎是为临时集市搭起的铺面。对方一侧树着一面孤零零的他们的国旗,标示着他们还有人守卫。据说中国这边这片广阔的丘陵地带,很快要“开发”了,已经修好了一条足有6车道的水泥路,不过两边还是无声无息的红土。下次再来或许这儿已是一个热闹的边境集市。
与这儿的国境线相隔不远,是罗家坪大山,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耸立在边境上的一座战斗的山,英雄的山。如今,那些英雄们到哪里去了?登上雨雾濛濛的山顶,只有“人在阵地在”、“以阵地为家、以艰苦为荣”等标语写在已经没有军人驻扎的营房墙上。硝烟散了,枪炮声走远了,边境宁静了,主峰阵地便成为“遗址”,旅游者的照相机收进的是一片居高临下的青山绿水,是一片要靠解说才知道的浴血阵地。当年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已被炸毁,地雷被排除。好哇,非常好!他妈的,人类不需要战争,需要的是和平、是和谐,是经济建设与发展。此时此刻,我故地重游感情复杂,就像一口已经隐没多年的沉钟被撞响了。尽管我没和“猫耳洞大王”尹国亮一道挖过战壕,也没和“神炮排”的战士们打过炮,我当初只是一名到这儿采访过、生活过的军旅作家,但是罗家坪还是令人难忘的一个地名。相信,那些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战斗过、并坚守了十多个春秋的指战员们更难忘记。陪同我们参观的马关县女宣传部长熊廷韦在山下的金厂乡当过党委书记,她说,那时每年她都要接待不少到罗家坪扫祭、缅怀的老兵。他们常常激情沉默后,泪洒罗家坪。
要离开罗家坪时,我提出车子能否拐到金厂街上看看。尽管车上人很多,人们还是理解我那点“怀旧”心情,车子绕到了山下的金厂。这儿,大概过去开采过金矿,所以叫金厂。打仗那时,金厂是最前线,军车、马帮挤满了街道。所谓“街”,也就是两排歪歪斜斜的油毛毡房或破瓦房,吃碗米线都困难。眼下的金厂,俨若县城一条街,油毛毡房已变成了一幢幢三、四层高的楼房。这天正好是赶街天,街子两头停满了摩托车和汽车,一把把大红篷伞下摆堆着各色商品,街上人头济济,一片喧哗。除了买卖农用品和土杂品外,电饭煲、电视机、收音机、西装夹克各式皮鞋……仅这些商品名字,你看不出这儿仅仅是山乡小集。而那些来自境外的越南边民、越南盔帽、越南吊床、苏式望远镜、瑞士军刀……,又说明这儿是边关一个开放的跨国贸易集镇。
要离开马关了,告别的手高扬着,我该说的“再见”却说不出来。熊部长和我的“本家兄弟”欧阳厚尧等一行人一直把我们送到70多公里外的文山机场。半个多小时的飞机后,马关又将变得很遥远。但它英勇而苍劲、深刻而热情、朴犷而美丽的形象真真切切在我心中拂之不去。
“再见吧”!临上飞机时我才终于说出这句话,依依不舍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