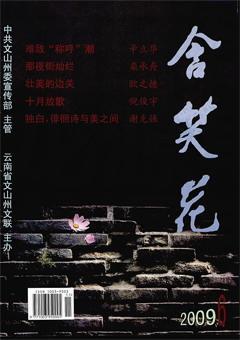难敌“称呼”潮
辛立华
那天山子给我来了电话,非要约我到县城那个比较高档的饭店去喝酒。我问他还约了什么人,他说就我一个,我才应了他。山子是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班又同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某个小机关工作。此人一贯不务正业,和我一样总是好写一些招有关领导骂的文章,又不会也不愿意溜须拍马讨领导高兴,所以工作二十多年才混了个副科长。
按时来到饭店,山子已经在此等候了。见我来了,头一句话就说:“石头,今天我请你来这饭店喝酒,你是不是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不怕你不高兴,自从你当上了那个狗屁的副科长以后,你的眼睛可就往上长了。甭说对别人,就是对我这个从小和你一起光屁股玩泥长大的人,你不也是癞蛤蟆撞上长虫皮——躲得越远越好吗?所以我就想,你呀,请我来这儿喝酒,一定是撞上什么腻味的事了,才舍得出这血。往小了说,你是马屁没拍好拍头儿的脸上了,挨了一脚,窝了一肚子火,找我诉诉苦。往大了说,你是哪件事办砸了,找我讨讨高招儿,看怎么才能糊弄过去。好事吗?是你这副科长往上提了半级,跟我显摆显摆。坏事吗?是你泡小姐的事让你老婆知道了。想请我在嫂子那儿抹抹稀泥。对不对?”我俩见面就逗。
山子一听就不乐意了,翻着白眼儿对我说:“嘿!叫你这么一说,我简直是大伯背兄弟媳妇过河——一点好儿没有了。我说石头啊,你就不会往高一层的境界想一想?说白了,你就不会想到我研究出什么来了?比如说……”
“打住。研究?就你?我还不了解?整天琢磨着不是谁还欠你一顿酒啊,就是打听谁的丈夫这几天不在家啦,要么就是计算着哪位领导的老爹老妈该过生日了,要么……”
“行了行了。”山子拦住了我的话,说:“你呀,敲锣边儿的话少说,鸿门宴的酒少喝,站缸沿儿的事儿少干,别人的老婆少摸。点你的菜。今天我要好好跟你喝几杯,好好跟你聊聊我最新的研究成果,让你知道知道我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也省得你整天看不起我。”山子一招手叫来了服务小姐,一指菜单对我说:“点,挑你爱吃的,点。”
我摆了摆手,对山子说:“客随主便,还是你点吧。反正是你做东,你点什么我吃什么。酒吗,要是听我的,就来一瓶儿二锅头,每人半斤,什么时候喝完什么时候为止,怎么样?”
山子把嘴一咧,很是看不起地对我说:“半斤,那叫喝酒吗?”
“嘿!小牛儿撅尾巴——来劲了是不是?那你说,喝多少才算喝酒?”我不服地对他说。
“喝多少?告诉你吧石头,我们喝酒,从来都是以半斤起步。半斤以后就没谱儿了,也许一斤,也许一斤半。较起劲来,二斤三斤也会喝,这么跟你说吧,什么时候喝得管媳妇叫丈母娘了,管小姨子叫老婆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吓了一跳,说:“我的天,这哪是喝酒啊,这是玩命啊!”
山子哈哈一笑,说:“瞧把你给吓的。放心吧兄弟,咱哥儿俩是不会那么喝的,何况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呢。好,我点就我点。小姐,记着啊,凉菜:芥末鸭掌、小葱儿拌豆腐、麻辣田螺。热菜:一条酸菜鱼、铁板腰花儿,像咱们这岁数的,多吃点儿腰花儿好。再来个红焖羊肉,怎么样?”
“行了。比不了你们吃公款,扔多少也不心疼。今儿个是你自己掏钱,省两块是两块。”
山子冲服务小姐一摆手,说:“行了,快点儿啊。”接着又调侃地对我说:“你们写小说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怎么说话写文章都爱带刺儿啊?也难怪当头儿的都不喜欢你们这种人,就连我有时候看着你都别扭。”
我笑了两声说:“那也是你当上那个狗屁的副科长以后才有的感觉。”
“嘿!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你……”
正好服务小姐把凉菜和酒端上来了,我便趁机拦住了山子的话,说:“打住,菜上了,酒也来了,咱们先喝酒。就用这啤酒杯,每人一个,一杯半斤,省得打架。”我把一瓶二锅头分别倒入了两个啤酒杯,说:“这杯归我,这杯给你。今天是你请我,整两句吧。”
山子乐了,说:“你这么一说整两句,倒把我要说的主题给提前钩出来了。”
我把嘴一咧,说:“喝酒就说喝酒的话,还弄什么主题?我看你真是好有一比啊。”
“比什么?”山子的两只小豆眼儿紧紧地看着我问。
“好比那:高粱穗儿插花瓶——根本算不上花儿。癞蛤蟆玩儿双杠——根本摸不着杆儿。野兔子跳大神——根本成不了仙儿。看厕所的称经理——根本不是官儿。”
山子不满意地说:“瞧这一套一套的。我说,你爷爷是不是卖过盆儿啊?”
我笑了笑说:“我爷爷没卖过盆儿,我爷爷锔过盆儿。甭拽,说,什么主题?”
“什么主题?刚才,你不说‘说两句,非要说‘整两句,将‘说字换成‘整字,这就是我要说的主题。眼下我正在研究的理论性文章,题目就叫《称呼的蜕变》。”
“蜕变?我只知道你把情报告诉了敌人那叫叛变。”
“你才叛徒呢。”
我一本正经地说:“说实话,你这《称呼的蜕变》,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来,先喝口酒,边喝我边跟你说。喝。”山子深深地喝了一口。
“喝。”我也深深地喝了一口。
山子吃了一口菜,故意摆出一副很深奥的样子对我说:“怎么跟你说呢?这么跟你说吧。我问你,眼下,你在你妻子的心目中,对你这个丈夫的称呼,是不是还有效?”
“是不是还有效?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眼下,你妻子是不是还管你叫丈夫?”
我不爱听了,很不满地对他说:“这不是废话吗?告诉你吧,我妻子和我结婚这么多年了,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凡是需要把我介绍给别人时,不是说这是我丈夫,就是说这是我爱人。怎么,是不是请我喝顿酒,想让我妻子管你叫丈夫呀?”
“你这叫抬杠。蜕变两个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不紧不慢地对他说:“你听着,蜕变一词是这么解释的:泛指人或事物发生质变。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第998页,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对。”山子也喝了一口酒,说:“现在我正在研究的《称呼的蜕变》,说的就是眼下好多的称呼就是发生了质变。就说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吧,就发生了质变。”
我觉得山子说的这几句话对我要写的那篇文章很有帮助,就决定开始装傻。说:“怎么讲?”
“以前不是称丈夫就是称爱人。向别人介绍也都这么说:这是我丈夫某某某,这是我爱人某某某。现在变了。”
“变什么了?”
“这是我老公。”
“这没错儿啊?眼下年轻的妻子,大都管自己的丈夫叫老公,这是现代夫妻之间一种亲昵的表现,也是时代潮流的一种体现。就连我的妻子,有时候也老公老公地这么叫我。怎么了?”
“怎么了?我听着别扭。”山子说完这话狠狠地吃了一大口芥末鸭掌,因为吃的太多,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边乐边对他说:“那是你的观念太老。跟不上形势,赶不上时髦,追不上流行,够不上新潮。”
山子擦了擦眼泪说:“再怎么新潮,再怎么亲昵,也不能管自己的丈夫叫老公啊?老公是什么玩意儿?
老公是过去的太监。你老婆管你叫老公,那你儿子是哪儿来的?”
“哪儿挨哪儿啊这是?你这纯粹是夜壶打喷嚏——满嘴喷尿。喝酒,喝酒。把这杯喝下去再胡说八道啊,免得旁边那几个喝酒的揍你。告诉你吧,眼下叫的老公,与过去的太监,本质上完全不同,两码事。喝酒,喝酒。”
“喝。”山子喝了一口酒,接着对我说:“两码事?那好。可是,就说这小葱儿拌豆腐吧。明明就是小葱儿拌豆腐,可那‘宫廷大酒楼里非得叫雪山青松,你说气人不气人?”
“雪山青松比小葱儿拌豆腐听着新潮、时髦、现代感强。”我故意气他。
“得了吧你。”山子很气愤地说:“强不强的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出来,可吃着还是小葱儿拌豆腐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是存心气人?”
“那是你自找。它就是叫青蛙洗澡,碍你哪根儿筋疼了?管它叫什么呢,是小葱儿拌豆腐不就结了?要我说,你这是拉屎揪耳朵——多此一举。”
“什么呀,我气的并不是它叫什么,我气的是同样的小葱儿拌豆腐,可价钱却比这儿贵三倍。”
我乐了,说:“甭说,肯定是你自己花的钱。”
“多新鲜呀,”山子喝了一口酒,又忿忿地说:“更可气的是,吃完饭我刚要去结账,我儿子把我拦住了,他让我在这儿等着,他说他去买丹(单)。”
“那是你儿子要花钱,孝顺。你要是生这气,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孝顺?少跟我来这套,早干什么来的?看我吃饱了才去买丹,我还吃得下去吗?再说了,他也应该先问问这丹我爱吃不爱吃啊?是仁丹呢还是仙丹?啊,看我吃饱了,弄几个小素丸子糊弄我?”
我赶紧拦住了山子的话,说:“行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还仁丹仙丹呢?买单,就是结账。真是吃公款吃惯了还有人结账,所以连买单就是结账都不知道?我都跟着你脸红。行了行了,喝你的酒吧。就这水平,还研究呢?别腰里挂只死耗子——假充打猎的了。”
山子不服地说:“买单就是结账?那买双呢?”
我不满地对他说:“你这叫抬杠。”
山子哈哈一笑,说:“抬杠?你要认为我在抬杠,这就对喽。”山子一下严肃起来,说:“告诉你吧,这就是我要研究的主题,就是称呼的蜕变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不便与危害,而真正的危害并不是这些,是那些关于官职称呼的蜕变给人们带来的不便与危害。”
我也很严肃地说:“有这么严重吗?”
“有哇?”山子正要接着往下说,服务小姐把酸菜鱼端上来了。山子用筷子一指,说:“来,尝尝做的怎么样。”说着就夹了一块鱼放进了嘴里,吧叽了两下嘴,说:“行,够味儿。来,吃啊。”见我吃了一块挺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你刚才说有这么严重吗?告诉你吧,有。有的还是我亲身经历的。就因为这个,我才研究这个问题。”
“亲身经历?那我得好好听听。”说完这话我点上了一支烟。
山子也点上了一支烟,说:“这是上个星期日的早上在我家发生的事。星期日了,孩子又不在家,我就想睡个懒觉。你嫂子呢,挺早就和几个伙伴儿扭秧歌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不正是睡懒觉的机会吗?嘿!我睡得正香呢,电话铃儿把我给吵醒了,睁眼一看,刚七点半多一点儿,你说气人不气人?”
“气人也得接呀,你知道是谁打来的,要是有什么要紧事呢。”
“是啊,我怕耽误事,就赶紧抓起了电话,喂了一声,对方就搭话了,是个女的,声音倒是挺甜的,可她说的头一句话就把我给气坏了。”
“说什么了?”
“您好,请问遗嘱在吗?”
“遗嘱?谁的遗嘱啊?”
“是啊。当时我就愣了,心想我们家二十多年没死人了,怎么开口就要遗嘱啊?再说了,我父母都活得好好的呢,而且我父亲就独儿一个,就是我爷爷奶奶死的时候有什么遗嘱,也早给我父亲了,也轮不到别人跟我要啊?大清早的弄这事。添堵吗这不是?”
我笑了笑,说:“有句话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啊,会不会你爷爷在外面有个私生的儿子啊?”
山子立马就瞪起了双眼,忿忿地对我说:“你爷爷还在外面胡搞呢。”
我笑着对山子说:“别生气,开个玩笑,再说你爷爷都死这么多年了,说什么也没关系。对了,肯定是对方打错了。”
“这还像句人话。”山子喝了一口酒,说:“我说了一句打错了,就把电话撂了。”
“接着睡。”
“睡什么呀?我撂下电话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电话铃儿又响了。”
“那就接吧。”
“是啊。我抓起电话一听,还是那女的,还是那句话:您好,请问遗嘱在吗?”
我喝了一口酒,说:“要我说呀,弄不好这里头真的有事,你应该仔细问问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别耽误了,说不定这里头真有什么故事呢。”
“有屁故事。”山子不满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正在写长篇小说呢,像这些张家长李家短了,三只蛤蟆五只眼了,瘸腿儿的公鸡蹦的远了的嘎古事特别上心。芝麻粒儿大的事,到了你手里就了不得了。故事?你爷爷还有故事呢。这是诚心捣乱,这是电话骚扰。气得我狠狠地说道,打错了,叭地就把电话撂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是够气人的。”
“更气人的还在后头那。我钻进被窝没有两分钟,电话铃儿又响了。”
“爱响不响,干脆你就甭理它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不行啊。我外甥在外地上大学,平时根本没工夫,只有星期日这天才有工夫给我打个电话。真要是他打来的,你不接,不是耽误事儿吗?”
“那就接吧。”
“是啊。我抓起电话一听。”
“你外甥来的?”
山子忿忿地说:“什么呀,还是那女的,还是那句话,您好,请问遗嘱在吗?”
我再一次笑了,而且是特坏的那种。
山子明白我的意思,翻了我一眼说:“你甭弄这坏乐,有什么屁你就放。”
我说:“你呀,别再说打错了,真得好好问问她。我敢保证,这里面肯定有事。”
山子恼火地说:“我没那工夫。气得我狠狠地给了她一句:有病啊你?”
“你别急啊。”
“能不急吗我?大礼拜天的要是有人没完没了地跟你要遗嘱,你能不急?”
“要说也是,放着我,我也早急了。那么,你给了对方这么一句,对方说什么了?”
“嗨!对方一听我说了这么一句,态度也立马变得很不友好起来,倔倔地说:你那到底是不是宜主任家?我一听这话,当时就傻了。”
“宜主任家?哪儿挨哪儿啊这是?”
山子唉了一声说:“你忘了,你嫂子不是姓宜吗?在乡计划生育办公室当副主任。”
“那干嘛非要说宜主在不在啊?早说找宜主任不就没这麻烦了吗?仙鹤打架——绕脖子吗这不是?”
“谁说不是啊。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你嫂子扭秧歌回来了,我就赶紧把电话递给了她。等她接完电话我把刚才的事跟她一说,她乐了。她这么一乐,我的火儿更大了,说你乐什么乐?今儿个我这懒觉没睡好不说,更烦的是没完没了的跟我要遗嘱。到底怎么回事,你得给我说清楚了。”
我觉着这事挺有意思,就急忙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服务小姐端上了铁板腰花儿。山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立即吐了出来,咧着嘴对我说:“什
么味儿啊这是?你尝尝,怎么又臊又臭啊?”
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一嚼,也立即吐了出来,说:“味儿是不对。臊点儿还说得过去,可这臭就不对了。”我冲着旁边一位服务小姐喊道:“哎,小姐,小姐你过来。”
小姐走了过来,十分客气地对我和山子说:“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
山子板着脸对小姐说:“把你们老板叫来。”
小姐仍是十分客气地对山子说:“怎么了先生?如果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能先跟我说说吗?只要我能解决的,我就尽快给您解决。”
山子说:“也好。那你就尝尝这铁板腰花儿是什么味儿。”
小姐端起盘子闻了闻,十分抱歉地对我和山子说:“对不起了两位先生,味儿是不太对。这是我们的错儿,请二位先生原谅。我这就给您二位去换,而且按着我们饭店的规定,这道菜免费了。二位稍等,马上就给二位换来。”
服务小姐走后,我问山子:“接着说你那电话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山子“嗨”了一声说:“你嫂子说呀,眼下好多的行政部门和机关单位,人们对副职的领导都这么称呼。”
“怎么称呼?”我故意问道。
“就是把那个副字去掉。像你嫂子她们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正主任,就直接称呼主任。而其他的三位副主任,一个姓水的,就叫水主。”
我笑了,说:“干脆叫水煮鱼得了。”
山子接着说:“一个姓宫的,就叫宫主。”
“宫主?男的女的?”
“男的,五十多岁了。谁见了都宫主宫主地叫,他还觉着挺美呢。”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简直是八十岁的老太太穿超短裙儿——不知道什么叫丑了。”山子也乐了,说:“偏偏你嫂子姓宜,就成了遗嘱了。”
我说:“不这么叫不行吗?”
山子说:“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大气候的问题。眼下人们都很浮躁,都很虚荣,好多人都对什么什么长的,什么什么理的特别地看重。就拿我们村的二膘子来说吧,你也知道,买了三辆旧摩的,雇了三个外地小伙子给他拉黑活儿,他还是印了一大堆明片,见着谁都一本正经地递上一张。那明片上不就那么鲜鲜亮亮地印着他的名字,后面的官职是:飙风客运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吗?连这么一个主儿都对职务这么看重,更甭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了。别看一个副职都红了眼似的争,真要争上了你叫人家副什么什么的,人家还真不乐意听。甭别人,就你嫂子,有时候我说她,你不就一个乡级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吗,干嘛整天牛哄哄的呀?她就不爱听了,就跟我瞪眼了,说你少给我带那个副字,我不爱听。嘿,后来我这么一观察啊,你猜怎么着,敢情好多的副职领导,确实不愿听那个副字。所以,人们就对副职领导,大都这么称呼了。”
我故意装傻地说:“那人们都怎么称呼你呀?”
山子说:“也这么称呼。”
“怎么称呼?”
山子不满地对我说:“你傻啊是怎么着?我说了半天合着都对牛弹琴了?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厅级领导,你怎么称呼人家?”
“这还不好办?厅长就叫厅长呗。”
“还有五个副的呢,你怎么称呼?”
“这更好办了,赵副厅长、钱副厅长、孙副厅长、李副……”
山子做了一个停的动作,说:“停。”
我继续装傻,说:“怎么了?不对是怎么着?”
山子喝了一口酒,看不起我似的说:“就你这么称呼人家,你的事就是能办,也得吹灯。”
我不服地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什么赵副厅长钱副厅长的,人家最不爱听的就是那个副字。”
“副字怎么了?当年周恩来任副主席的时候,人们不都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地叫吗?听着多亲切啊。怎么,现在任个小小的副科长就不爱听那个副字了?那么多的副职中央首长都不计较这个,怎么官儿越小这毛病倒越大呢?不这么称呼怎么称呼?非得把那个副字去了,直接赵厅长、钱厅长、孙厅长的叫?”
山子连连摆手,说:“更不行。你这么叫,那几个副厅长倒是满意了,可正厅长不乐意了。要是我,我也不干呀,啊,都厅长厅长地叫着,那谁还知道我是一把手啊?也就是说,我这一把手还往哪儿摆呢,啊?”
“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怎么才能行呢?”
山子夹了一块红焖羊肉,挺潇洒地扔进了嘴里,边嚼边说:“只能这么称呼:赵厅、钱厅、孙厅、李厅。这么一来大家都高兴。大家高兴了,你的日子才能好过。不然的话,赵厅背后给你一脚,钱厅暗地掐你一把,孙厅冷不防给你使个绊子,李厅偷偷捅你一刀。你说,你这日子还怎么过?”
“没法儿过了。没别的,我自己就得上吊去。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凡是副职的领导都得这么叫?”
山子使劲点了两下头,肯定地说:“为了‘山寨的安全,只能这样。”
“我要是偏不这样呢?”我故意逗他。
山子十分认真地说:“甭说你非要较这劲了,就是你一不留神没把这称呼问题把握好,灾难就会落到你头上。”
“没这么严重吧?”
“没有?”山子端起了酒杯,说:“来,喝了这口酒我慢慢跟你说。”山子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又一连吃了好几口菜,刚要对我说,服务小姐把重新做的铁板腰花儿端上来了,很是客气地对我俩说:“二位先生好,请您尝尝这次做的怎么样。”
山子夹了一块放进了嘴里,很是夸张地吧叽了几下嘴,又轻轻地点了两下头,这才微笑着对服务小姐说:“嗯,这回还差不多。行。小姐,今儿个我们哥儿俩高兴,就不说什么了,往后呢,还真得注意。今天也就遇上我们哥儿俩了,要是遇到死较真儿的,那麻烦可就大了。行了,忙你的去吧。”
服务小姐十分礼貌地对我俩说:“谢谢二位先生了,今后我们一定加强管理,并希望二位先生常来。”小姐说完这话,款款地走了。
我用手指点了山子几下,说:“贫不贫啊你?怎么一见到漂亮小姐话就那么多呀?”
山子不说话,只是嘿嘿地乐。
我说:“你这一乐都是坏乐。”
“喝你的酒吧。来,再来一口。”山子和我又喝了一口酒,说:“我有个表弟,在一个局机关工作。具体是什么局咱就不说了,这么多吃饭喝酒的,还是不说为好,免得招惹是非。我表弟在局办公室当主任,主要负责接待上级领导。”
“这工作好啊,不是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吗:办公室主任是管家,吃喝的大权手里拿,东游西逛陪领导,白吃白喝加白拿,弄好了还能往上爬。”
“得了吧你。往上爬?我表弟就是因为这称呼问题没把握好,上个月,他的办公室主任被拿下来了。”
“怎么回事?”
山子点上了一支烟,狠吸了两口,说:“上个月,他们上级部门一位新上任的吴局长,到他们单位检查工作,作为局办公室主任的他,接待工作自然是非他莫属了。”
我也点上了一支烟,说:“这有什么呀?就这活儿,对于你表弟来说,还不是黄鼠狼抓小鸡儿——手拿把儿攥吗?”
山子“嗨”了一声说:“攥什么呦!头一句话,就惹吴局长和他们的局长不乐意了。”
“说什么了他?”
“因为吴局长是新上任的,也就不认识他们局的几位主要领导。我表弟呢,就有了一项向吴局长介绍他们局几位主要领导的任务。”
“那有什么呀,几位领导的名字全在他心里装着呐,合着眼也说不错啊。”
“是啊。吴局长一到,也不知我表弟是犯迷瞪了还是活该他倒霉,指着他们局的局长就对吴局长说:吴局长,这是我们傅局长。”
我说:“正局长没在家?”
山子一拍桌子,说:“什么呀,他们的正局长姓傅。”
“嘿!哪儿那么巧。”
“巧的还在后头那。当时,吴局长的脸就拉下来了,十分不满地对我表弟说:怎么,你们正局长干什么去了?”
“这就不乐意了。”
“吴局长的话音刚落,旁边的一位大胖子立马往前迈了两步,腰一哈,头一低,恭恭敬敬地说:吴局长您好,我就是郑局长。”
“怎么回事?”
“胖子是副局长,姓郑。”
“好吗,猴儿吃麻花儿一满拧了。再说了,你表弟干了那么多年的办公室主任,整天围着领导转,对如何称呼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清清楚楚啊?”
“是啊。其实我表弟对几位领导的称呼一直都是特别谨慎的,平时无论见了谁都能恰到好处地将称呼问题处理好的,不知那天他是怎么了,就把这称呼问题给弄砸了。等吴局长弄明白后,冲我表弟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他永远也忘不了的话。”
“说什么了?”
“有这样干工作的吗,啊?马马虎虎的,啊?谁先谁后,你总该清楚吧,啊?你这个同志,啊,得好好锻炼锻炼啦,啊。”
“一句一个‘啊,什么毛病呀这是?”
“就因为这句话,第二天,我表弟就被调到一个科里成科员儿了。”
“这真是人要倒霉呀,放个蔫儿屁都砸脚后跟,喝口凉水都塞牙啊!看来,这称呼问题把握不好,还真的能给人带来灾难。”
“对。”山子十分严肃地说:“这就是我要研究这个课题的主要因素。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悲哀,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股逆流。”
我一拍桌子,赞许地对山子一伸大拇指,说:“行啊你,还真是说得满有道理的啊!看来,我还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好,就冲这一点,我得敬你一杯。来,深深的,喝它一口。喝。”
“喝。”山子放下酒杯接着说:“表面上看,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怎么称呼问题,实际上是某些人对权力的一种显示与欲望。而这种显示与欲望,往往就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或大或小的灾难。”
我显得很兴奋地说:“你能再举个例子吗?”
山子说:“好,那我就再给你说一个。你嫂子她们村儿里有个胡大爷,今年六十五岁。上个星期的一天,胡大爷去一个什么院办事。胡……。”
我拦住了山子的话,说:“能说出具体是什么院吗?”
山子摆了摆手。说:“为了‘山寨的安全,我看就免了吧。咱们只说事儿,怎么样?”
我想也是,就说:“也好,省得喝口凉水塞牙、放个蔫儿屁砸脚后跟、坐在炕头儿上车轧脚、大冬天的让蚊子踢着。”
“可胡大爷就大冬天的让蚊子踢着了。”
“说。”
“那天早上,胡大爷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了县城,左打听右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院。按着传达室的人说的,胡大爷来到了三楼办公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看了胡大爷的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胡大爷说:大爷,您这事儿啊,得到钱院那儿盖个章。”
“这回我知道了,钱院,就是钱副院长。那意思是说,胡大爷要办的事,归钱副院长管,对不对?”
“对呀。可胡大爷哪儿知道这些权权巴巴的事儿啊?在村儿里,见着村长支书什么的,他都是二狗子三驴子什么的直呼小名儿,也没听谁叫过张村李村什么的,所以胡大爷就把钱院理解为前院儿了。”
“好哇,就跟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树上骑个猴儿,让范伟理解为树上七个猴儿一样。”
“是啊。胡大爷从三楼下到一楼,站在楼门口喘了喘气儿往前一看,前面确实还有一座楼。当胡大爷看清那楼足有八层时,心里顿时就是一颤,心说这办公室别在上面的楼啊!”
“含糊了。”
“再怎么含糊也得去啊。胡大爷来到一楼的传达室把情况一说,传达室的人往上一指,说办公室在六楼。”
“好嘛,整整增加了—倍。可这没关系啊,五层以上的楼就该有电梯了。”
“是有电梯,可胡大爷不知道啊。再说你就是告诉他有电梯,他也不坐。他说那玩意儿不把牢,跟打水的辘轳似的,吊绳一断,还不把人给摔散了啊。”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山子“哎”了一声说:“怪难为胡大爷啊,吭哧吭哧爬上了六楼,还是瞎跑了。办公室的人看完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胡大爷说,真对不起了大爷,您啊,得到李院那儿看看。”
“就是李副院长那儿。可胡大爷这六层楼算是白爬了。”
“关键的是胡大爷又把李院领会成‘里院儿了。”
听到这儿我的气都直往上拱,忿忿地说:“什么事啊这叫?就因为这么一个副字,多少无辜的人就得跟着倒霉。”
山子说:“可不是吗。胡大爷一听这六层楼又白爬了,腿一打软儿,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夜里我没做倒霉的梦啊?没办法,胡大爷从六楼又一层一层地下到了一楼,站在一楼门口边擦汗边往里看,里院还真有一座楼。让胡大爷高兴的是,那是一座二层小楼儿。”
幸亏是二层小楼。要是十二层,胡大爷还不立马晕过去啊?关键的是这二层小楼能不能把问题解决了,别在跑完这二层小楼真的再来个十二层?那可就把胡大爷给坑到家了。
山子一拍大腿,说:“这话还真让你给说着了。胡大爷来到这二层小楼连话都懒得说了,把介绍信往上一递就坐在一把椅子上等着发落了。接待胡大爷的是个姑娘,姑娘看完介绍信冲胡大爷微微一笑,说对不起了大爷,您这事儿啊,应该归庞院那儿管。”
“啊?”我差一点儿被一口酒呛着,咳嗽了半天才缓过劲来,红着眼忿忿地说:“又把老爷子支使到旁边的院子了?他们要是有十个八个的副院长,老爷子得让他们给折腾散架了呢。”
“胡大爷的火儿也早顶到脑门儿了,要不是看在是位姑娘的份儿上,他老人家早就翻脸了。老爷子强忍着将火气压了下去,抓起介绍信,二话没说,气哼哼地就走出了这二层小楼。汗,是顺着后脊梁沟儿往下流了。”
“我看呀,什么时候胡大爷的汗唰唰地往外喷了,事儿才算办成。”
山子吃了一块酸菜鱼,狠狠地将鱼刺吐在了地上,说:“胡大爷站在楼门口一边喘息一边骂: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呀?就这芝麻粒儿大的小事儿,就让我来回的爬楼梯玩儿?要是西瓜那么大的事,还不得让我爬珠穆郎玛峰啊?我的身子骨儿还算硬朗,不然我就散在这儿了,哪儿的事啊这是?胡大爷一边骂一边透过花墙的圆门往里那么一看,妈哟一声就坐地上了。”
“怎么了?”我忙问。
山子说:“旁边那楼足有十五层啊!”
“哎呦,看来老爷子的命真的要交这儿了。”
“胡大爷坐在那儿发了半天愣,左想右想,前思后虑,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开始爬楼。还算凑合,胡大爷只爬了七层,就来到了办公室。一个小伙子看完胡大爷的介绍信,很和气地对胡大爷刚把话说完,胡大爷就急了。”
“小伙子对胡大爷说什么了?”
“大爷,真对不起您了,您这事儿啊,只能到尚院那儿去办。”
“没法儿不急,离上苑一百多里地呢。”
“这回胡大爷是真急了,一边擦汗一边冲小伙子就嚷开了:好啊,你们这是拿我这个乡下老头子开涮呀?小半天儿了,我没干别的,尽爬楼了。从后院打发到前院,从前院打发到里院,又从里院打发到了旁院。好不容易到了你这儿吧,没想你比他们都狠,一下子就把我打发到了上苑。上苑离这儿一百多里地呐,打车的钱你给是怎么着?这叫什么事啊?听胡大爷这么一通儿的发脾气,小伙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不但没恼反倒乐了。”
“老爷子都快让他们给气疯了,还乐呢?”
“小伙子赶紧给胡大爷倒了一杯水,一边向胡大爷赔不是一边向胡大爷解释,说尚院不是上苑镇的那个上苑,是我们的尚副院长。钱院,就是钱副院长。李院,就是李副院长。胡大爷嘿嘿一笑接上了话茬儿,说旁院就是庞副院长,对不对?小伙子见胡大爷乐了,心才算踏实下来。等胡大爷的火气渐渐退下了之后,小伙子又亲自带着胡大爷往尚副院长办公的地方走了去。胡大爷来到这座楼的楼门前一看,原来正是自己头一次进的那楼。来到二楼尚副院长的办公室,没用两分钟,胡大爷的事就办完了。”
“折腾了大半天,这胡大爷办的到底是什么事啊?”山子“嗨”了一声,说:“购买二两高产新品种的香菜籽儿。”
“啊?二两香菜籽儿,差点儿没把胡大爷的命给要了啊!”
“望着手中的二两香菜籽儿,胡大爷又乐了。乐着乐着胡大爷冲尚副院长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
“尚副院长啊尚副院长,你们这儿的副院长有没有姓依的啊!”
“胡大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尚副院长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问胡大爷。你猜胡大爷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你们这儿要是有姓依的,说不定现在我正在医院排队挂号哪!”
胡大爷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既幽默又讽刺,很是能让人发笑,可我却笑不起来,总是有一种嗓子卡了东西的感觉。吐,又吐不上来。咽,又咽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