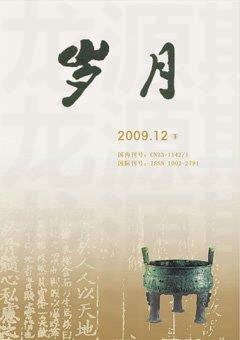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艳情化倾向
徐美媛
唐宋时期并无“流行歌曲”的说法,但实际上,大部分配乐歌唱的唐宋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对此,袁行霈先生即指出:“唐五代北宋的词,基本上可以称为当时的流行歌曲”。[1]谢桃坊先生也认为:“宋词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而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曲。”[2]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表现出诸多异于传统诗文的“另类”特质和社会功能,其中,“词为艳科”便是唐宋词所具有的“另类”特质之一。
一、 流行歌曲属性对唐宋词艳情化倾向的促成
从初唐到盛唐,人们对爱情的咏唱一直都没有消歇。时至中晚唐,伴随着爱情意识的勃发,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更加繁盛。即便是“礼崩乐坏”的晚唐五代,爱情意识在诗文中的表露还是有所节制,或者说是受到约束的。而只有到了唐宋词中,爱情意识才得以淋漓酣畅的抒发,才终于得到了最佳的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从词体本身而言,唐宋词在抒写儿女之情方面与传统诗文相比有其独具的某些优势。
词是一种配乐的抒情韵文,其风格和体式的形成都受到音乐的影响。而词所配合的音乐以燕乐为主,燕乐“高至紧五夹清,低至上一姑洗,卑则过节,高则流荡,甚至佚出均外,此所以为靡靡之乐也。”(《续通典》卷九十《乐六·清乐》附注)管弦冶荡之音特宜于传递缠绵悱恻之情,曲子词之所以将吟咏艳情绮思作为其主要内容,并形成了哀感顽艳、柔靡妩媚的总体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便都与燕乐的基调有关。此外,燕乐纷繁复杂的旋律和节奏决定了曲子词体式的多变,这也更适合于表现微妙幽曲的内心变化。
曲子词的艳情化倾向又与其特殊的创作和传播环境有关。欧阳炯《花间集序》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可见,词是创作和传播于女性环境中的特殊文体。“绮筵公子”作“清绝之词”,付予“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来即席演唱,且能“用助娇娆之态”,这种“声”和“色”的全方位享受给词作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其次,从外部条件而言,唐宋词的艳情化倾向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时代心理(爱情意识的勃发)有关。
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欢宴冶游成了当时的风尚。而宋代“太平日久”的“盛世”局面,就更为冶游之风的盛行创造了极为适宜的社会环境。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北宋)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宴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宴饮游冶活动也频繁地出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汴京元宵,民众张灯宴游“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5]清明时节,士民郊游野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5]在这样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男女之间的交往,如游春踏青时的巧遇,酒筵歌席间的眉目传情,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人们的私生活中也多了一层旖旎香艳的色彩。
二 、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艳情化倾向的表现形态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艳”,主要与女子的美色有关。《说文解字》云:“艳,好而长也。”《诗·小雅·十月》“小序正义”亦云:“美色曰艳。”由此引申,也用以指男女情爱之事。“艳”又有辞藻华美之义,《榖梁传注疏序》“左氏富而艳”疏云:“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由此观之,则所谓“词为艳科”,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词的题材内容以表现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为主;二是在词的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与其题材内容相协调的香艳色调。
先说第一方面。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这就指出了词好写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的文体特征。
在宋代,几乎每一位染指于词的文人,都或多或少地写过表现女性生活或男女情爱的“艳词”。柳永、张先、晏几道、秦观、黄庭坚、周邦彦、贺铸、姜夔、吴文英等以写艳情词而闻名的“词坛高手”自不必论,就连孤高自许、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林和靖,亦以一曲《长相思》将旖旎缠绵的心曲款款道来;一代名相司马温公,也曾写出过《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这样的香软之作;而理学家程颐,“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6]因此朱彝尊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红盐词序》)为了契合曲子词“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的文体特征,有些词人甚至不惜“为文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地杜撰艳情艳事入词。由上而知,就其题材选择而言,唐宋词已经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艳情化倾向。
再说第二方面。
与艳情化的题材内容相适应,唐宋词在艺术表现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熏香掬艳”(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五)的香艳之美。对此,郭麐在《词品》中就作了感性的描述,他说:“杂组成锦,万花为春。五酝酒酽,九华帐新。异彩初结,名香始薰。庄严七宝,其中天人。饮芳食菲,摘星抉云。偶然咳唾,明珠如尘。”(《秾艳》)这种美感特征不但几乎是所有唐宋词(主要是婉约词)之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共识,也成为一些词论家评判词体“本色”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沈义父《乐府指迷》就指出:“作词与诗不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王世贞认为词要“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功,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艺苑卮言》由此可见香艳之美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美感力量。
唐宋词人喜欢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之美,善于“男子而作闺音” (田同之《西圃词说》),这就使得词中充满了浓重的脂粉气息和浓郁的女性化情调。
首先,很多艳情词选取大量与女性生活有关的语汇和意象。女子的体貌服饰,一颦一笑都成为词人着力刻画的对象。而与女性闺阁生活相关联的众多“景语”和“情语”也都经过精心选择,被精描细刻。对此,缪钺先生说得好:“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7]富有女性情韵的意象语汇,织造出婉约香艳、缱绻缠绵的闺阁氛围,激发人们的无穷遐思,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情感暗示。
其次,唐宋词中普遍存在的香艳气息和色调,又与其无处不在的“佳人”形象有关。
翻开唐宋词,就仿佛走进了一个“女性化”的世界,佳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一股股浓郁的脂香粉气也随之迎面扑来。在反映女性生活和男女恋情的词作中,这些明眸善睐、长袖善舞的红粉佳人自然是发散香风艳色的主要“热源”,而在其它题材的作品中,词人们也不忘用“佳人”来点缀,以此“添香增色”。比如, 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观等人的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而在刻画英雄形象时,词人也喜欢用“佳人”形象来妆点和衬托——“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苏轼《念奴娇》)、“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 还有词人对山川景色的描写,也融入了女性的柔美与娇艳,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一词,即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来比拟江南的水和山。甚至在国破家亡以后,最让词人梦萦魂牵的,依然是那软语温存的闺中人“深阁绣帘垂,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蒋捷《贺新郎·兵后寓吴》)。唐宋词对女性美的集中表现,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 既体现了香艳美与柔性美的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也最终成就了唐宋词的“艳科”格局和绮丽风貌。
三 、 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艳情化倾向的价值分析
不可否认,“词为艳科”作为一种题材限制,它确实使唐宋词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觑。但在批判之余,也可看到,词人对于女性生活情感和男女恋情的深度发掘,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审美感受,毕竟具有着一定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未可忽视。
首先,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突出的艳情化倾向不但与当时社会勃兴的爱情意识“相适应”,而且真实地展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不合理制度的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性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
《毛诗·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明确地把情限制在礼义的范围内。然而,符合人类正常天性的爱情意识是压抑不住的,它必然会在适当的时机勃发和张扬。恋情词中对于情爱专注而放肆的抒写,表现出不为传统礼教和伦理所束缚的蓬勃生命力,展现出某些“人性觉醒”和“人性解放”的熠熠光彩。
其次,从美学层面看,“词为艳科”又是对柔性美的集中展现和再发掘。
在唐宋词以前,中国传统文学一直是士大夫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他们牢牢地把持着文学空间的话语权,始终占据着文学表现的焦点。唐宋艳情词则把女性提升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集中大量笔墨描写女性的容貌美、形体美和内心世界,从而突出表现为以柔为美的女性化审美倾向。这不但拓宽了文学表现领域,突破了中国文学“以刚为美”的单一格局,而且为后代文学提供了多样化的审美选择。
再次,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唐宋词的艳情化倾向不但使得宋代“香艳文学”蔚为大观,并且直接影响和沾溉了后代“香艳文学”的发展。如《红楼梦》中宝黛共读《西厢记》,“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牡丹亭》的芳词艳曲,也使得林黛玉“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而在大观园这片乐土上,也处处充满着女性世界所特有艳丽与芬芳。由此可见,就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唐宋艳情词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79.
[2]谢桃坊.再论宋代民间词[A].贵阳:贵州社会科学[J],1987.40.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75-105.
[4]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77.
(作者简介:徐美嫒,宜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