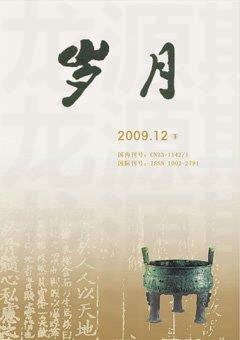论“他者”与《印度之行》
张 著
“他者”在后殖民理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哲学上看,“他者”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对立面或否定因素,为他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肯定。”[1] “他者”是通过文本建构起来的,殖民主义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使自己的征服行为合法化、合理化,最便利的途径是利用文本建构起一个“他者”的世界。在任何的对异国形象进行了直接描写和间接影射的文学作品中,作家都必须选用话语对“他者”的形象的进行文本建构。《印度之行》中的“他者”,是一种对印度形象的话语构建。
一、神秘混乱的“他者”
在《印度之行》第三章中,穆尔夫人在搭桥聚会失败后,与阿德拉严肃地注视着网球场的草地,在她们的眼中:“这不是动人的画卷,东方失去了它那古老的壮丽,沉落为人们无法看到彼岸的深谷。”[2] 的确,在福斯特笔下的印度已经寻找不到对辉煌的印度古代文化的赞叹,曾经拥有灿烂炫目色彩的印度在作家的注视下,留下的是神秘和混乱。
作者描写了被自然力量完全压制的昌德拉普尔。“它根本不像一座城市,而是中间布有零星茅舍的一大片树林,……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印度人居住区。……它们长得高出了令人窒息的贫民区和被人遗忘的庙宇、寻得了阳光和空气,有了比人类或其创造物更加旺盛的生命力。”[2]具有旺盛力量的树木主宰了小镇,正如同神秘的自然主宰着印度大地。同时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还有与生命不可分割的死亡的力量。
在《印度之行》出版的十年之后,福斯特说:“我借助于一场无可解释的混乱……阿德拉在山洞中的经历……来着力表现印度就是不可解释的混乱。”[3]可以说,马拉巴山洞是神秘混乱的“他者”的核心象征。马拉巴山起源于神秘的远古时代,它使人联想到那原始的混沌状态,它的神秘不仅仅来源于仿佛逃离了时间的流逝,“这块巨石的主体变化甚微,好像原始状态依然如故”[2],而且还来自于它自身奇特、无序的风貌,“它们突然平地拔起,错乱无序,……它们跟任何看见的或梦见的东西都毫无关系。说这岩石‘神秘是暗指鬼神,而一切鬼神都没这岩石古老。”[2] 马拉巴山代表着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宇宙世界,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神秘的马拉巴山洞是人类必须面对但又无法了解的宇宙的象征。对任何一位走进山洞的英国人来说,它便意味着深入到印度文化的中心,他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伦理准则必将受到严峻挑战。
作者着意表现一个无序、神秘而混沌的印度:圆拱形的苍穹,带来生命又融合着死亡的恒河,出没着蛇、黄蜂、豹子、骸狗的丛林,当然还有那吞没了一切声音和光线的山洞,这一切自然景观都深深地沉淀在了福斯特笔下那个既神秘又混乱的印度形象之中。
二、 难以交流的“他者”
赛义德认为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的“关键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间持久的对抗”。[4]在福斯特之前的殖民主义文学中,被殖民民族常常被表现为次等、劣势的:“他们或是原始的,未进化完全的;或是类似野兽的,被动物性所占据的;或是孩童的,心智未发育完全的;或是偏执的,具有某种缺陷的。”[1] 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印度代表人物的刻画主要集中在两个印度人身上,阿齐兹和戈德博尔。阿齐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正直、善良、友好、真诚、对印度的自由和独立倾注了热情;戈德博尔信奉印度教,善良、深邃、超脱、具有神秘色彩。与此相对应的英国殖民官员的骄傲自大、狭隘偏执成为了福斯特所批判和讽刺的对象。但福斯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他无法从根源上剖析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他叙述常常不自觉地认同殖民统治者的观点,他肯定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工作效率和冷静的头脑,将他们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行为归结为英国公学的不学无术之风,把殖民统治者对印度人的冷酷无情归咎于英国中产阶级那颗‘发育不良的心,借此寻求巩固和改进为英帝国海外统治的方式。可见,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批评并非为了促进印度的独立运动,而是为了寻找延续帝国统治的良方。”[5] 在对英国的“自我投射”即如何再现殖民地人民的形象上,福斯特不由自主地扭曲和再造了“他者”,最重要的特征体现在“他者”的难以交流上。
福斯特在塑造阿齐兹时采用了多个视角。在殖民主义者朗尼看来,他是一个利用独立精神来博得英国巡回议员赏识的印度人;在菲尔丁看来,他是一个不失高尚的人;在穆尔夫人看来,他是一个有教养的青年人。“明达医院代表的英国殖民权力机构的认同和被殖民奴役的印度人身份造成他主体世界的进一步分裂” [6],使他表现出多个侧面的复杂性格。一方面,阿齐兹是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尊严的知识分子,怀有虔诚的宗教情感和热烈的爱国情绪。另一方面,阿齐兹是一名在英国的殖民话语下被培养出来的医生,他不可避免的受到英国意识形态的影响。阿齐兹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英国殖民主义的视角中,下意识地使用殖民主义话语对他认为属于异教的印度教民众和印度形象进行粗暴的评判。
除了阿齐兹以外,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印度人是戈德博尔。他是神秘、超脱的印度教的化身。他最突出地体现了“他者”的难以言说的神秘和深奥,这种特质是“他者”让英国人难以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原因。戈德博尔虽然能包容各种文化、宗教的差距,但他的超脱世俗,善恶的世界观,使得他在现实矛盾面前采取了消极的逃避态度。对他来说,生命只能算是一次寻求解脱的旅行,而在短暂的旅途中唯一值得追寻的东西是永恒的精神。戈德博尔对现实矛盾的冷漠和逃避,在阿齐兹被审判的事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戈德博尔教授能帮助阿齐兹,判断阿齐兹是否无罪,但戈德博尔此刻关心的却是他将离开这里到茂城开办学校的名字。在他看来马拉巴山事件的真相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善恶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两者都是上帝的两幅面容,一副是显现的,另一副则为隐蔽。”[2]
三、女性化的“他者”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女性和殖民地常常被联系到一起,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的主体特征是在同“他者”的关系中被确立的。 “西方文化中叙述性别‘他者与叙述种族‘他者,采用的是同一套话语,在将东方女性化的同时,也在将女性东方化。”在《印度之行》的“他者”话语建构中就隐含了性别话语特征,这就是印度“他者”所表现出的女性化特征。
在福斯特笔下,女性形象被运用于印度的地貌景观的描写之中。马拉巴山洞是神秘混乱的“他者”的核心象征,更带有典型的女性形体的特征,岩洞代表子宫的意象。马拉巴山洞里面有带肉体感官色彩的细节描写和女性子宫的整体象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女性化“他者”的中心意象。在山洞的内部——“马拉巴山的皮肤终于看到了。那皮肤比任何动物身上的毛皮都美丽,……甚至比情人更富有肉感美。”[2]点亮的火光映在山洞光滑如镜的洞壁里,形成了“一对情侣”,“两个火焰相互接触了,亲吻了,但很快便熄灭了。”[2] 在这样具有强烈暗示性的环境下,具有殖民者和女性双重身份的阿德拉和穆尔夫人都经历了一场精神挑战。在山洞中,阿德拉心中的与女性意识对立的一面迅速占据上风,如情侣般纠缠着的火焰,单调的无休止的回声,使长期受压抑的肉欲也随之苏醒。她意识到她并不爱朗尼,岩洞激发了她潜在的女性意识,这种性本能和对异族的恐惧在特殊的气氛中迅速强化,潜在的种族排斥感使阿德拉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遭到了阿齐兹的侵犯。
穆尔夫人在山洞中也经历了类似的女性意识的苏醒,由于她的宗教思想的影响,穆尔夫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对性别、伦理、宗教的挑战而陷入了分裂和疯狂。她在黑暗的山洞中,“不知是谁触及了她一下她感到透不过气来,一种赤裸裸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像动物的肉趾,打到了她的脸上又堵在了她的嘴上。”[2] 这种赤裸裸的肉欲感让她感到非常的可怕,而山洞激发的女性意识和欲望让她失去了身心的平衡。她也深深地感受到马拉巴山洞的母体子宫意味。对穆尔夫人感受的描写,暗示了神秘而又虚无的马拉巴山洞如同女性的子宫一样,是母体的象征,成为印度文化魂魄的象征。马拉巴山洞具有强大地吞噬能力,也象征着母体的包容性。福斯特运用了女性的包容性、吞噬性的隐喻,唤起了读者对印度的不可言说的,神秘混沌的想象。
总之,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和严厉的批评,但福斯特本人是英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写作,对印度西方式的看法极其根深蒂固,有碍他看到“真正的印度”,使他无法洞察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他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话语也深深地潜入了他的反殖民主义话语当中,其发出的不和谐双声使《印度之行》中的“他者”成为永远的“他者”。
【参考文献】
[1]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2,90.
[2] E.M.福斯特. 印度之行[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9, 4, 136, 136, 198, 136, 136,163.
[3]石海峻. 混沌与蛇:“印度之行”[J],外国文学评论,1996(2):63
[4]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201.
[5]周韵. 试论《印度之行》的后殖民倾向[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9).
[6]陶家俊. 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从《印度之行》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作者简介:张著,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