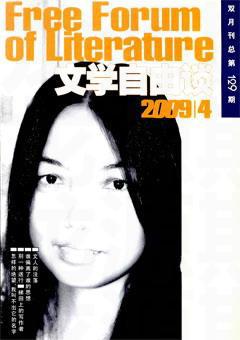不知终旅的文学跋涉者
黄桂元
随着文字岁月的平淡流逝,我的阅读趣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我既不会轻易被虚无缥缈的浪漫呓语所俘获,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就范于伪现实主义的百般调教。但曾经的军旅时光,虽然短暂似梦,却如同难以根除的心症——我知道自己已经注定无法抗拒那种英雄主义文学气质的诱惑了。于是时不时地,会有一个目光坚毅且步履坚实的军旅女作家,常常携着沉甸甸的作品晃动在我的视野,使我不断收获着警醒和振作。
孙晶岩,这个晶莹而坚硬的名字,容易令人想起沐浴在刺目阳光下的峭壁,或是碧蓝海水拍击中的崖石,其凛然、刚正的姿态似乎难以使人产生任何的绮念、邪念。然而正是这个名字,在文坛制造了一种很难漠视的报告文学现象。说起来,我和她还是同年入伍的小兵。公元1970年代某冬,我15岁,她却只有14岁。当然,那时候我们隔山隔水,属于不同的军兵种和各自的地域与环境,不可能彼此相识。只是我早在二十出头就已还原为老百姓,而她至今一身戎装,脚下绵延着无尽的军旅征程,那上面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文学方尖碑,记录着她的激情文字岁月。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一家艺术休闲类的杂志供职,一度正挖空心思四处寻觅稿源。现任《天涯》杂志副主编王雁翎女士曾经是我的同事,调海南之前,她把自己联系的作者孙晶岩慷慨地“移交”给了我。于是一个秋日,便有了我与孙晶岩惟一的一次见面。那次进京组稿,我住在位于沙滩的《求是》杂志招待所,房间在半地下室里,且六人杂居,气味浑浊,洗手间和厕所远在走廊通道的另一头,如此全无诗意的环境,人若不想蓬头垢面都难,显然不适合接待女作者。转天上午,我在万寿路下了地铁,转车赶到解放军后勤学院,见到了身穿便装的女讲师孙晶岩,她步履赳赳,性格爽快,我的笨嘴与她的口才形成了鲜明对比。稿子敲定了,我也松了口气。想来我的风尘仆仆让她有了恻隐之心,于是她请我在附近餐馆就餐。由于下午有课,她送我到公交车站,刚好来了一辆车,本来车里拥挤不堪,我怕耽误她的时间,也顾不得等候下趟车,一狠劲硬挤上去。她后来说,站在那里看到我的半个身子被车门夹住,当时觉得当编辑真的很不容易。
这之后,我曾经给孙晶岩的作品写过评论,同时注意到她的写作长项是那种宏阔视野、超大格局的报告文学,而不是我们这类刊物所需要的艺术类稿子,于是随着刊物风格的变化,我们逐渐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是通过媒体默默在关注着她的写作行踪,也常看到她的一部部长篇报告文学接连问世。最近,我收到了孙晶岩寄自北京的两本新书《五环旗下的中国》与《震不垮的川娃子》,六十几万字,放在手里,只觉得分量很沉。追问这些作品的文本意义是不公平的。孙晶岩无疑是一位极具使命意识和挑战精神的军旅女作家,算上这之前出版的《中国动脉》、《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两卷)、《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中国金融黑洞》、《边关——中国陆路边境海关纪实》等十几部厚厚大书,题材范围之杂、之广,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且多为“国字号”的超大规模,很容易使人怀疑她的精力、体力会不会透支?她毕竟不是钢铸铁打的,而且是单枪匹马,跨越如此不同的领域,难道她真的没有感到过力不从心吗?其实,只要你了解孙晶岩,就会觉得这种选择或许对别人会视为畏途,而对她实在不算什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甚至令许多口大气粗的须眉作家都望而怯步的宏大题材,她却以巾帼姿态从容挑战,长驱直人,且如鱼得水,胜任愉快。于是便有了一次次的创作“井喷”。对我这等胸无大志却仍以文字为生的人,也只能站在远处遥望,为之浩然兴叹。
这当然都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成品结果。那些艰难跋涉之中的文字形成过程,万般滋味,惟有自知,对于相当多以写作为消遣的同行,早已近乎于天方夜谭。当许多作家忙于缩回自我天地、潇洒地完成向“内”转的变身,孙晶岩却一直坚执初衷,冥顽不化,昂然向“外”,不知终旅,这在当代作家中无疑是罕见的。她的身后,不断切换着一道道险峻山岭,一条条湍急河流,一片片泥泞雨路,她的身影也在不断变幻着。殊为可贵的是,她涉猎的这些题材领域没有连贯性,常常是跳跃式的,出其不意的。比如,同是发生在2008年的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北京奥运与四川特大震灾,孙晶岩即使分身乏术,也不曾缺席,硬是通过日以继夜的艰难奔波,出色地完成了写作使命。
《五环旗下的中国》,这个话题的覆盖面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几乎可以涉及现代文明社会方方面面的领域——历史、政治、自然、建筑、经济、科技、艺术、环保、礼仪、习俗、宗教信仰、人间和谐、挑战极限,其综合了硬指标与软科学的异常庞杂的内容,完全可以被视为有关奥运中国如何圆梦的小“百科全书”。她把奥运比喻为“满汉全席”,这当然来自于切身体验。这个全新的写作任务对于她的知识构成、采访技巧、沟通能力、文字功底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考验。孙晶岩说以前自己对科技不够了解,比如治理污水、兴奋剂检测、食品安全监测等知识,都很陌生,仅就体育项目,整个就是“偏科”,只喜欢跳水、体操等观赏性强的项目,对举重、柔道等项目几乎一无所知,但她必须接受挑战,临阵磨枪,加紧“恶补”,尽快进入角色。她是采访北京奥运的惟一“授命”作家,这个身份使得她格外珍惜每一次采访,于是她一度成了奥运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眼里“最麻烦”的人。三年多时间里,她深人到奥运各个领域,与四百多位相关人士长谈,参加了二百多场新闻发布会,几乎是在“死缠烂打”中进行高密度采访。她还加入志愿者行列,甚至亲自跑完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全程。据她说,这还是得益于费孝通先生的教诲,他主张参与式的田野调查,写奥运,她首先也得让自己参与进去。
第一次采访“水立方”那天,她发起了39度高烧,体力本不允许她去,但想到事先约好了国家游泳中心董事长康伟,不能爽约,便硬是自己开车,晕晕忽忽地“飘”到了“水立方”。康伟看见准时赶来的孙晶岩,竟然穿着一件厚厚羽绒服还像是很冷,吃惊之余,大为感慨。他不知道,对于孙晶岩实在不算什么,比这还要艰难几倍的采访太多了。早在十几年前,本来有14个可以选择的采访点,军人的性格却使她“毫不犹豫地把视点瞄向昆仑山”,坚持在高度缺氧、大脑细胞处于浅眠和深眠的状态下完成了《白雪昆仑》和《冬访唐古拉》的采写过程;当年在冬季的湘西,仅仅为了按时交付一篇稿子,她可以顶风冒雪徒步120里山路赶赴车站;写女监纪实,她走访了国内的十多所女监,并与一百多位“服刑姐妹”接触聊天,推心置腹;采访西气东输工程,她曾与工地的石油工人一起过了五个节日……这一切自讨苦吃的行为,当今文坛,除了孙晶岩,还能有谁肯于欣然为之呢?
有的时候,读着孙晶岩的作品,我们会不自觉地忽略掉作家的性别属性。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很难用女性文学的审美尺度来衡量。她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的狭隘的性征局限,而甘愿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大千世界。这种“中性”的写作姿态,显然更适合于她的发挥。不过一旦进入生命危亡的特殊情境,比如写到汶川地震带来的灾难,她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仍然可以使读者感受到她的笔端充满了女性和母爱的万般柔情。
大体说来,当下文坛的写作有两种路数:一种是聪明的、讨巧的、算计的写作,事半功倍,甚至是四两拨千斤,以追求最大化的各种效益;一种是沉稳的、踏实的、甚至显得有些“笨拙”的写作,付出与得到很不成比例,近乎于“不识时务”。但赢得人们敬重的终究还是后者,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孙晶岩,其写作跋涉姿态,体现出的难道不正是鲁迅先生所感叹的那种“脊梁”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