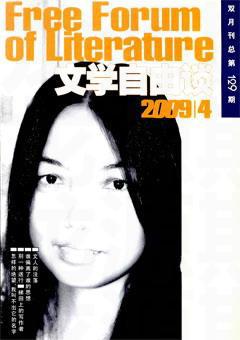作家素描(二十七至二十九)
胡殷红
二十七、蒋巍
蒋巍是我的前领导。记得我们都在《文艺报》时,蒋巍组织过一个论坛,他当主持人,往主席台上一坐,豪情万丈,气势如虹。我们在台下听他哪儿都不挨哪儿的“理论”,外加口口声声的“美眉”,感觉他就像个巧舌如簧的堂子,把四六不靠的话给“文学”起来了。一群旁听的博士生让他给忽悠得晕了菜,会后蜂拥着要电话留地址。蒋巍得意忘形地冲我说,你总说我是中老年妇女的杀手,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也很受年轻女博士欢迎嘛!
蒋巍调中国作协后,和吴秉杰成为互补型搭档。吴秉杰这个人有十分学问,常常只愿讲出三分;蒋巍只有三分学问,却能讲得比十分还像。只要开会蒋巍就亢奋,把笔记本电脑往桌子上一放,照着电脑慷慨陈词。有一次他鸡心鸭肺猪肠子地说了有五六分钟,声音戛然而止,哈哈大笑说:我念错了,不是这篇。孟繁华当场提议,给蒋巍发“中国第一忽悠奖”。还有蒋巍率团参加索菲亚国际笔会那次,他的演说文采飞扬,会后金发碧眼的作家纷纷上前与他热烈握手,俄罗斯著名作家舍浦琴柯上前与他紧紧拥抱,一位法国女作家张开双臂表示:蒋先生,你赢得了这个诗意的夜晚!就这点未必属实的事儿,蒋巍反复说了有小半年。吴秉杰一到这时就皱起眉头说,你换个话题,烦死人了。我说,应该再发蒋巍一个“国际忽悠奖”。
我也奇了怪了,就说蒋巍那长相,把五官拆开来单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再加上一张大嘴叉,实在不咋地,但把零七八碎集中在他脸上排列组合,还就挺有气质,也挺有女人缘。有一次到上海开会,我们女同志逛街请他保驾护航,到了街上他见到漂亮小姐就赞不绝口,进了商店就往女售货员柜台去。我和牛大姐一商量:咱们忽悠他一把。进了五家商场,我们让他买了五双鞋,一会儿说这双鞋很男子气很优雅,一会说那双是国际流行。蒋巍是烧包,买了就穿,从这个商场穿到另一个商场就换上新买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蒋巍背了一堆旧鞋回来,说是你们说他穿上有气质,有什么气质啊,明天就都捐灾区。
我曾给蒋巍定位为:标志性年份里的“腕儿”,蒋巍不乐意,说我对他的态度一贯不端正,要我介绍他时得加上“评论家”三个字。也是,他的《论文学的与时俱进》、《论时尚的文化意义》、《论文学的“中国制造”》等“宏论”,其观点虽然令专业评论家们皱眉头,但我相信,那是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就像他自己说的,公鸡就得打鸣,都不争鸣,天怎么白?
蒋巍出生在哈尔滨,满族后裔,如果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他一准是个“那五”。有一次我们去哈尔滨开会,去前蒋巍就张罗着带我们去玩,说别看自己在北京抡不开,回家乡就能找到恶霸地主的感觉。他嚷嚷着让我们把行李存在前台就跟他走,一路上神气活现地指东道西,见了卖雪糕的说这是哈尔滨的特色,非要请大家吃。喜得我们一人要了两支,到交钱时,他拍着口袋大声喊:谁带钱了?我钱包没带身上。没转一会儿,他咋呼累了,站在马路中央气宇轩昂地挥手打车。车到宾馆,他首长似的扬长而去,剩下我们一群外乡人和乱收费的司机打了一架。
蒋巍有一本散文集叫《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我说,见过吹牛的,没见过你吹这么大的。蒋巍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其实我内心很脆弱很自卑,只有往牛了说才有活下去的勇气。这也许是真的,因为蒋巍无论在作协还是在其他相关开会,能轮上发言,他总是毫无畏惧地表扬自己,而且打不住。有一次领导明确地制止他:蒋巍你就不能谦虚点?蒋巍回答说:我是越骄傲越进步,一谦虚就退步。挺严肃一领导,让蒋巍忽悠得一点没脾气。客观地说,蒋巍骨子里是谦虚的,他特别注意学习作家、评论家的优长之处。用他的话说,他所有的本事都是“偷”来的。
蒋巍当知青时曾写过“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革命绝句”。当了记者以后开始搞报告文学,曾连获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近年的《丛飞震撼》还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到了21世纪,我真看出人才受重视了,中国作家网请他当总监,他为网站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却发现他竟然化名“黑桃”,伪装成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发表了一部网络体长篇小说《今夜艳如玫瑰》,骗来一大批男粉丝,给他留言留信表示爱慕。他为了兜售这部书,光天化日之下,利用职权往别人的研讨会上塞“私货”,记者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他“艳如玫瑰”的笑脸和宣传资料,与会者还以为是走错会场了呢!
说了蒋巍这么多糗事,就是忘了说他那颗富于激情、正义的心。抗洪,抗冰雪,抗地震,蒋巍都到了第一线。不可否认,蒋巍的写作是有力量的。一位农民兄弟因买了假种子告状五年倾家荡产,蒋巍夫妇收留农民住在自家,男主人怒火冲天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你代表谁?》,批评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此文发表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当地官员被查办,农民终获赔偿,央视《新闻调查》还拍了专题片《无果的种子》。还有一个农村未成年女孩遭到歹徒强暴,居然有人利用职权悍然偷改了作案者的血型,放跑歹徒。蒋巍了解情况后连夜写了数千字的《呼兰奇案》,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省市领导当即批示查办,歹徒落网,涉案人员被撤职。
去年,蒋巍到贵州去采访、创作抗冰雪,他一头钻到大山深处数月,写出《灵魂的温度》一书,但当时陪同带路的同志“少见多怪”,对来者饭量比干活的农民还大,什么场合都敢忽悠的作派认识不足,偷偷往作协打了几次电话核实:这人是你们那里的括号正局级作家蒋巍吗?
蒋巍会书法、会画马,能唱歌、能拉琴,踢足球、打冰球,还自封中国作协篮球队总教头。依我看,他那身手,在任何球场上也就一替补队员了。现在他的名片上又多了一行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如果过两天他的名片上再加上两行:中匡I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也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他的确是个才华横溢的忽悠鬼。
二十八、关仁山
关仁山是唐山人。不知道为什么唐山人自嘲自己是“老呔(tan)儿”,好像多少含着点“土”的意思。1997年“三驾马车”驾着辕满世界瞎跑那阵子,我在北京见到了笑模笑样的关仁山和“浑不吝的谈歌。关仁山是年龄最小的那匹马,说话的调儿像赵丽蓉。如今关仁山都当了河北省的作协主席,讲话发言,臭贫聊天,他“咋儿着、咋儿着”的,还是那腔儿,成天笑眯眯的还是那样。
“三驾马车”由三个河北作家组成。何申是大哥,板整有样。谈歌长得就像个车把式还嗜酒,只要喝多了,就得关仁山背着他回家,我管这叫“燕赵悲歌”。老谈在关仁山面前总是倚老卖老“挤兑”小关,可私下里不管醉与不醉都口齿不清地表示:小关写小说扬名立腕时,我还写新闻当记者呢,那时我已读过他不少作品见过他“下”的不少鸡蛋,就是没见过这只下蛋的鸡。然后嘎嘎狂笑,口水四溅地列举关仁山小说,时不时背点段落。凡到这时我都刺激他:把妒嫉当歌儿唱也是妒嫉。谈歌东倒西歪地“正经”起来:我是真挺佩服他,我绝对写不出来,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评论关仁山的作品不是我的专长,更何况作家出版社那本
近四十万字的《关仁山研究专集》摆在眼前,我还能说出啥新鲜的话。只能用现在已经说滥街、成了贬损词儿的“多才多艺再贬一把在书画界写书最多,在文学界书画有名的关仁山。关仁山不会吸烟不会喝酒,拉拢女同志最多也就开张口头支票,但他也得有点啥情趣吧?上中专学过美术,这几年拾起来,调剂一下枯燥的写作生活,我就不说他是附庸风雅了。可这一画也麻烦,没人追着要他的书了,要字要画的不少。听说有一次在县里搞活动,人家介绍关仁山是书协主席,真书协主席恼得又摇头又跺脚。
我去过几次唐山,大街小巷转悠,触目所及尽是关仁山写的大字牌匾和他画的“关葡萄”。带我转陪我看的一干“小吏”,说起关仁山的字画,比关仁山本人还神气招摇。说关仁山在唐山搞的那次个人书画展吧,文学界的朋友也就是想去捧个人场凑个趣。司大出意料,那场面壮观得就像赶菜市场抢便宜货,还尽是手上戴着大金戒指的煤老板,张口就买十来张。他们眼看着一个老外买他一幅画,几千欧元一手钱一手货。前不久,关仁山随陈建功团长到澳大利亚访问,带了两幅装裱好的画,其中一幅葡萄送给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接画时问:葡萄怎么这么红?藤蔓处还闪着金?关仁山说,深红是真朱砂,有的地方点了金粉,避邪呢!悉尼作家笔会副会长谭毅女士向关仁山求字,陈建功调侃:写“少生孩子多养猪,超生违规,扎!扎!扎!”。本来是个玩笑,关仁山回国后还真就按领导指示办了,谭毅不仅得到了又点金又抹朱砂的葡萄还白得了一幅饶有意境的字,高兴得她一个劲打
那年在北京开青创会,正赶上“三驾马车”在道上封跑狂奔得来劲呢,因为何申与谈歌都超岁数了,惟有关仁山独自来北京开会,大家总是打听老何与老谈,关仁山只得端起酒杯豪气干云地代表他俩给大家敬酒。我当时就打电话给谈歌,说关仁山以前不喝酒是装的。谈歌知道关仁山的底儿,心疼地吼叫着:谁批准他代表了?长本事了?告诉他千万别逞能!果不其然,当晚关仁山赴医院输液,一夜未归。
比关仁山岁数大点的人都会背诵“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个警句。我总调侃关仁山:一个人微笑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变的笑脸。你就是装,装这么多年也挺难。自打手机普及到现在,每逢佳节我都能收到关仁山问候的短信,我曾问谈歌他也给你发吗?谈歌非常不屑:我只要接到他肉麻的短信,一准回拨电话训他:有事没有?没事别老骚扰我!谈歌又嘎嘎傻乐说:他哼哼唧唧老实听着。谈歌是个粗人,不管在哪儿喝高了酒站在马路旁就尿,关仁山拦不住,只能给他放哨。谈歌说用不着,你也别憋着。关仁山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胆怯地说,我不敢,我心理素质不好。谈歌扯着嗓门喊,你憋屈自己干嘛,跟我练几回心理素质就上来了!关仁山上车后还嘟嘟囔囔跟大家说,这不好练,我天生胆小。还有一次我们正好在石家庄参加一个会,会中接电话,说谈歌从楼梯上滚下来摔得不轻,会一散关仁山撇下我们就奔了保定。没想到关仁山一到就被瘸着腿拄着棍的谈歌拉上饭桌,他像立了战功的伤兵往主位一坐“可劲儿造”,关仁山插不上嘴,就只有眨巴着眼看他闹腾。其实谁都看出老谈嘴上“东邪西毒”的心里是真暖和。
不能不提的还有关仁山的拿手好戏——唐山方言版的评剧《列宁在1918》。他故意强调“老呔儿”味儿,从不嫌“母语”土,把个挺经典的电影演绎得“掉渣儿”。酒不行,他就唱,这招儿能顶酒使,关仁山特别卖力气。尤其三匹“野马”捆到一起以后,哥儿仨冲出河北唱遍全国。我碰见他们的次数多了,真有点听腻啦,就对关仁山说:你们就像戏班子卖唱的。没隔两天,“三驾马车”奔了浙江,中午作协领导请客,就因为演了这个节目,晚上《江南》杂志又加了一顿,请编辑们看他们演出。关仁山叹息着说:我们这叫一路卖唱到江南啊!天津作家李唯听过他仨“卖唱”,把这个段子写进电影《美丽的大脚》,演员孙海英是用陕西地方腔唱的。那年倪萍主演关仁山的电视剧《天高地厚》开机时,倪萍非让关仁山唱唱“原版”的,听罢,倪萍前仰后合地说:还是唐山味儿地道!
80年代末期,关仁山写过一阵通俗小说,想“改邪归正”的他把最后一本的署名权卖给唐山一书商了。书商手头没钱,过去是批发玉米淀粉的,转让稿费就拿三卡车玉米淀粉顶了。关仁山托朋友帮忙把淀粉卖给了唐山万里香灌肠厂。老板看着除了两颗黑眼珠满脸都是白粉的关仁山,憨厚地说,其实我也用不了这么多,但作家的忙咱得帮,要不然你咋办啊。关仁山心想,人家对作家这么尊重,以后写点真格儿的吧。从那以后,关仁山就开始写他的“雪莲湾”了。没承想正是这一点儿实实在在的感恩心理,成就了他日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白纸门》。《白纸门》里写到的“雪莲湾”,其实就是他的家乡黑沿子村。这几年,镇里请清华大学的设计专家按照关仁山小说描写的民俗,设计了“雪莲湾蓝海新村”,楼群已经拔地而起,把他虚构的世界变成了现实的新农村。村里还在工商局注册了“雪莲湾牌海产品,已经打入城里超市。在唐山市里,雪莲湾海鲜酒楼也已经开张了。
关仁山13岁那年让人从唐山大地震废墟里“刨”出来,虽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刨”他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小子日后能成为这么有名的作家。当然,从13岁至今他为自己的成长付出了多少辛劳,多少努力,只有他自己清楚。正所谓“天道酬勤”,联结磨难与成功的中间环节永远只能是勤劳。
二十九、刘兆林
刘兆林是个蔫巴人儿,扔人堆里既不打眼,也不吭声。如果在大街上搞个随机问答,估计没人相信他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还兼个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头衔,但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这老兄很幽默很有趣,虽然不够开朗还认死理。说他不够开朗吧,他那不够粗壮的“花花肠子”又差不多都是自己写出来的。他新近出版的《在西藏想你》,就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其中亲情、友情、常情被他写得翻江倒海惊心动魄,却没使用一个爱情字样。在“私情”和“旅情里,专写了一批日常生活或旅途中看一眼见一面就念念不忘的小女子们,那苦味和甜味绵长得像扯不断的丝线,还挺有“很斗私心一闪念”的勇气。说他认死理吧,有贼心没贼胆的事他件件自己都能消化了。他和侃爷作家邓刚是“文讲所”同学,他那点酸事邓刚常常当众“糟践”,刘兆林从来不辩不解,听之任之。要我说,他是肠子归肠子,心归心。一个心无恶意的人,还不允许九曲愁肠蠕动蠕动吗?
刘兆林啥事都不张扬,都内敛在腔子里的热血跟开锅的豆浆一样沸腾了,他也很难付诸实施(也许会意念实施?)。了不起的是,他有勇气把自己复杂而多情的心肠书写出来。比如那年一个圆桌会上,有个不相识的漂亮少女与他眉来眼去八小时,他自己感觉特别美好却又没有机会接触,心里闹腾得不行,就写出那篇《一次遗憾》。我说,谁看谁算个什么事,你老兄就把肠子弄“梗阻,,了,你的苦恼都是你悲剧性格自导自演的。刘兆林常常把“剃头挑子”在心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私下享受这种“心里美”的感觉。有一年刘兆林到厦门参加笔会,清一色男人,会议期间终于
碰上个女性,而且给他留下极好印象。过后他想见人家,又怕贸然相约被人耻笑,恰巧赶上自己生日,就以此为名约人家,对方没拒绝,只说如果下雨就算了。我说你巴不得下刀子顶锅也要去吧。他说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看了他写的美文《那年在厦门听雨》,才知道,虽然十八年只如约见过那一面,可厦门的雨一直哗哗啦啦响在刘兆林耳边,连手都没握一下的缺憾,到如今他还跟“贼”似的惦记着。
别看刘兆林现在黑巴溜灰不咋地,据说他年轻时是挺英俊的校官呢。他说当年作为部队代表参加全国文代会第一次进舞场,就碰上一漂亮女士硬拉他下舞池,舞会结束还给他留了电话。回到住所他做梦都梦见那女子,会结束那天终于下决心打个电话,那边痛快请他到家去玩。按过门铃他又犹豫了,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转身想走,门开了。人家公公婆婆、老公、儿子一家人热情地欢迎他,他不禁为自己进门前的卑微之念脸红。这次造访使刘兆林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憧憬,但他不敢把实情告诉老婆,试着先说了跳舞的事,老婆果然正告他:敢上舞场了,没交个女朋友?我说,瞎了吧,要说那女的还请你吃了顿饭,嫂夫人非活剥了你。刘兆林说,我下了好几年工夫,还真把你嫂子劝弄进舞场了,她先是看后是学,往后就天天催我带她去,再后来是她嫌我死囚在家里看啊写啊不陪她提高舞技了。我说,亏得你有本事让家庭不再封闭,不然你自我折磨加两口子互相折磨,早把个家弄散了!这么多年,刘兆林的家不仅没散,而且越来越牢实,这在于他的本事也在于他的情调儿。儿子没上大学时,他常组织一家三口做各种游戏,儿子小时候最爱玩的是开追悼会:三个人轮流主持,轮流躺床上扮死者,轮流听别人给自己致悼词。刘兆林给儿子的悼词,爱用文学虚词评价优点,总用实词批评缺点,儿子不爱‘听时,就猛地“活”过来反驳。刘兆林也特别注意儿子对他的评价。我说,你们小说家肠子不仅花花,而且弯弯真多,追悼会也能当游戏作?!我见过他已是北大文学博士并且出版过长篇小说的儿子,知道儿子也能调治他。就说他有个阶段常把钥匙插在锁孔忘取,儿子为了惩戒他故意把钥匙藏起来,急得他只好忙着换锁,儿子看他急得不行了,就提醒他到电话号码本第一页去找,翻开第一页,夹着一张条:你的心事到《辞海》100页找。翻开《辞海》,里面又夹一张条:你的心事到冰箱解决。刘兆林心急火燎地在鱼肉堆里翻出找了两昼夜的一串钥匙。又气又乐的爹问儿子这是为什么,儿子说这叫“打烙印”,就像你打我一顿我再也忘不了一样。
应该说刘兆林凭着不凡的创作成绩得过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八一文艺奖、庄重文文学奖。80年代《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这两部描写军队生活的中、短篇,使刘兆林一举成名,还有那篇洋洋三万言的散文《父亲祭》,字里行间流露的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令人震撼。
刘兆林很有人情味,他发言讲话,该说的都说,但没有半句官腔官调儿,时常顺嘴忽悠点令人提神开胃的作料。也正因如此,他的自叙传写法的长篇小说《不悔录》,不仅敢于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还勇于揭示一些无法回避也容易惹麻烦的矛盾。但书出了,因他写得真诚,手法也高明,非但没人对号入座,反而获了曹雪芹长篇小说奖。
如果我能有幸也申请参加刘兆林的追悼会游戏,轮上我给刘兆林致悼词,我会这样评价:他虽已如约死去,但他为国家、为民众、为家人的一颗真诚的心,还在怦怦地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