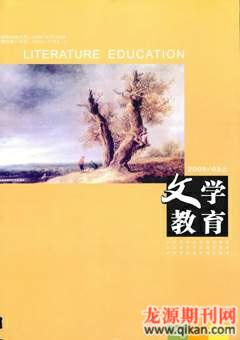走入《背影》精神世界
雷 军 傅晓辉
朱自清生长在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却一直以为“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1]他的创作也总以平民生活为背景,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不得不与平民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俞平伯论朱自清的人生选择时说:“他看人生原只是一种没来由的盲动,但却积极地肯定它,顺它的猝发的要求,求个段落的满足。这便是他底唯一的道路。”[2]创作于1925年的《背影》便是朱自清抓住平民生活一个片断,由心而发“淡香疏影式的笔”,却“捧出了真诚的灵魂”(赵景深语)。
一、触摸背影
《背影》剪辑了一个平民日常生活中的奔丧、送别等片断,粘合成一幅动荡时代人的生存场景。“奔丧”写了家庭衰落,前景黯淡;“送别”写了聚少离多,人各一方;“买桔”写了亲情慰藉,生活艰辛。片断性描写放大了父亲的叮嘱、讲价钱、买桔等常规性细小行为,从中可以品味琐碎里藏匿的深刻,体验平常中包藏的抗争活力。捕捉人日常生活瞬间的表现,摩擦出人生的亮点,以此激励自己不断地前行,是朱自清创作的思维惯性,也是支撑他在黑暗中前行的动力。
《背影》把父亲——这一平民,推到了生活的前台。“买桔”场景是全文的精华所在,也是显示父亲形象的重要一笔。作品用了探身、攀、上缩、微倾等日常语言,专注于描写父亲行动的迂缓和笨拙,以表现一个平民对生活的那份坚韧、信赖、务实。父亲面对生活的挫折和艰辛,表现出的从容和镇定,印证着中国百姓在大革命时代中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对普通生命的坚守,对“活着”本身的朴实理解。反观“我”这类知识分子,似乎有些言大于行的自负以及面对挫折容易迷茫的弱点。文中“我”总以忧伤的眼光看待父亲行为。四次写到“我”的眼泪,这“眼泪”有亲人分别的隐痛,有对未来不可知的担忧,也有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负重而伤感。阿英曾评论,“(朱自清)是带着伤感的眼看着‘现在”。[3]“忧伤”是“我”对生存状态的失望,更是“我”湮没在大时代漩涡中,精神在现实中缺失了“支点”的一种哀伤。
父亲对日常生活的执着,使“我”看到了平民身上闪光的一面,某种程度上转移了“我”的苦闷,但这种生活中亮点只能为“我”带来暂时的感动,无法把“我”从精神的苦难中彻底拯救。但通过触摸背影,“我”触摸到了生活,触摸到了现实,回到了生活的“真”,从中看到了民间的活力,感到了自身的弱性,变更了对平民的视角。
二、与背影的对话
从叙述话语角度看,《背影》中有两套话语体系交织在一起,一套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平民话语,另一套是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话语。父亲的平民化话语略显浅露和直接。作品中多次写到了父亲的“不要紧”、“不放心”“不妥贴”、“不要受凉”、“不要走动”等语言,这些简短、繁琐、重复性语句组合成了一个平民的语系。父亲的话语属于一种大众化、日常化、平面化的语言。直白的语言碎片看出了平民的务实和功利的个性,他们更注重生活的现实表象,对各种赋予生活所谓的意义毫不关心,这不是精神的无知,而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判定。
相比父亲语言的简单通俗,“我”的语言表现出了理性的反思特征。作品以回忆起笔,“回忆”是对事件的再叙述,会改变事件发生的原始样式。回忆型叙述把原来立体的生活压缩成一个直线的事件,“我”可以从容地梳理父亲的行为,反思自己的思想。“我”是所有事情的见证人:通过“我”了解到家庭的不幸和败落;通过“我”看到车站送别时父亲的场景;通过“我”了解了一个平民对生活的执着。“我”在作品中没有直接叙述话语,只有间接的叙述言语,如“我心理嘲笑他的迂……”“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等等。这种间接性叙述言语已不单单是对事件本体的讲述,而侧重于对事件功能的揭示。“我”的话语充满了所指的成分,突出了一种言语的个性化色彩,不断表露出一种情绪和思考,这是对生活意义追逐的结果。事实上,文中除了“我”作为儿子对亲情的反思,还一种更重要的使命性反思。“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暗示了“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此“我”的批判性言语还有履行知识分子使命的意味。
父亲的语言与“我”的言语交叉点是“我”的忏悔意识。从对父亲“迂”的嘲笑到若干年后对自己“真是太聪明”的自责;从对父亲脾气的乖戾述说到最终的理解和思念,“我”在不断通过自我反省来与平民情感沟通。从深层次讲,写父亲是为敞露平民行为方式,批判自我是为知识分子祛魅,这是20年代知识分子从反省个性主义开始向平民靠拢的一个信号。《背影》创作明显削弱了五四时期个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叙述的张力,把“我”放逐到平民——“我们”中间,进行的集体化融合,精英色彩在这里已经消失,大众力量已露微芒。这是因为20年代中期思想革命正日渐淡化,革命思想已显露头角,朱自清看着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不得不思考着“逗留在夹缝中”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和命运。
三、背影的期待
从字面解读,“背影”本身就标识了人之间的一种沟通障碍。作品没有直接写父子之间的情感对话,只用了简单的对白写父子之间陌生的沟通。尤其末尾写道,“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显然父爱是在父子情感相互抵牾中感受的,是在岁月对情感的销蚀中积累的,“背影”是人生对尘世的一种彻悟后的意象传达,尤其是“我”采取了一种批判自我的姿态来接纳父子关系,这表明父子之间感情不是始终完美的,“背影”是爱与痛情怀的载体。
从写意上讲,“背影”是平民人生的一种写照。“我”捕捉到平民生活散落的价值,但对这种价值的理解,采取了忏悔自我、牺牲自我认同的态度,而不是热情由衷地投入平民怀抱,一种感伤情绪始终溢于言表,放弃知识分子的岗位,以退让的姿态去获取平民的认可,这对知识分子是一种精神悲哀。“我”只能与父亲的“背影”相向,而不能正面相对,是写作技巧的一种安排,还是一种精神的距离?平民大潮是否会把“我”推向父亲般的生活;是否改变“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操守;平民生活的平面是否将抹平“我”的理想深度,促使自己毁灭?“我”在沉湎背影的怀念中放逐自己的精神,痛苦无止境的思考成为当时朱自清似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事情。20年代末朱自清最终选择了既不依附大众,也不与大众对立,而是“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寻求暂时的超然,“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4]
在个人生命历程中,朱自清怀着对新知识分子的憧憬,背负旧知识分子的苦难,走入了大众的“背影”里,他的人生选择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诚如诗人唐湜说:“我更爱把朱先生看成这时代受难的到处给人蔑视的知识生活的代表,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5]
注释:
[1]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经典》,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2][3]阿英:《阿英文集》,三联书店出版,1981年,第119页。
[4]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230~232页。
[5]迪文(唐湜):《手》“作者附记”,《中国新诗》第4集。
雷军,傅晓辉,武汉军事经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