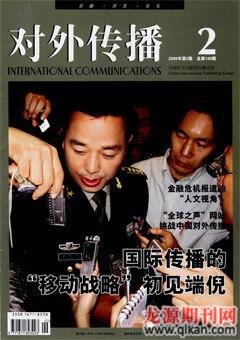跳出别人的框架讲故事
王万征
最近,笔者参加了一场国际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讨论“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国家形象”。会上,美国学者介绍了《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英国学者讲解了英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欧美专家角度不同,但发言意思大致一致: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确实不佳,但问题不在西方记者。西方学者一再强调,西方“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坚守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立足事实客观报道,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新闻管制让西方记者无法获取事实真相”(那就只好“据相关人士透露”了)。外国学者的发言,在会场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一些来自国内的学者也批评“信息公开方面中国政府要做的还很多”。
坦率地说,美英专家的话不无道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一直被西方新闻界奉若圭臬,引无数新闻人士“竞折腰”。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将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化归结于西方记者对事件本身的“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们又无法解释西藏“3.14”事件报道中,西方媒体一方面刻意忽略、隐瞒中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西藏多年发展的客观信息,另一方面,却又相当普遍地捏造事实,甚至张冠李戴、颠倒黑白,公然闭上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眼睛”。要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不能仅仅从新闻传播的技术角度出发,而要跳出新闻传播的框架,分析中国国际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美国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国记者在德黑兰采访一位伊朗青年:美国和中国,喜欢哪个国家?伊朗青年回答:美国在全球搞霸权主义,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美国不好;中国尊重别国主权,奉行和平外交,中国好。记者又问:现在给你一个出国机会,你愿意去哪个国家?伊朗青年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美国!
这个事例至少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在这位伊朗青年眼里,中国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具体作为,远远好于美国;第二,在这位伊朗青年看来,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优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美国对他更有吸引力。简单说,他喜欢中国,但不喜欢社会主义。伊朗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源于在国际舆论传播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西方媒体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毫无前提的“神圣化”,以及对“集权社会主义”的长期不懈的“妖魔化”。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角度看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国家形象,也许会有所启发。
第一,西方媒体重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性、集中性抹黑,而忽略发生在中国的生动的、形象的、即时的、充分体现人性自由与关怀的人与事。
2008年是中国形象的攻关年。举办奥运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山西矿难事件,一个个突发事件让中国的国家形象维护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如果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转移舆论视线,随着中央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召开,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的抹黑将迎来—个高峰期。
分析2008年西方媒体对华报道,明显可看到“两个中国”:一个是符号化、标签化、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中国被塑造为“集权、专制、不透明”的代名词,集中体现于对“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另一个是迅速崛起的“东方巨龙”—快速发展的经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变化巨大的百姓生活,污染严重的山河湖泊……这个中国,形象是复杂的,每天都有夺人眼球的“悲喜剧”上演。汶川大地震中,一位母亲顾不上自己的亲生骨肉,却抢救出了别人的孩子。日本共同社记者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报道此事,感动了很多日本人。可惜这样的报道太少了。这两个中国哪一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大呢?我看前者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框架性的,根深蒂固的,也是先入为主的。
对西方媒体抹黑中国形象的做法,多年来中国的应对策略基本是被动反应式的。我们一直纠缠于就事论事的具体细节。比如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只讲我们在某某方面进步多少,并相应出台一个《美国人权纪录》反驳白宫对我指责。但是,我们始终在别人的框架里讲故事,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无法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在维护最广泛人权方面原本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一理论问题。而西方媒体对社会主义的抵毁却是釜底抽薪的。他们承认中国30年的巨大进步,却否认这种进步背后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要国际媒体上社会主义还是“集权、专制、独裁、压迫人权、不透明”的代名词,中国的一切进步都会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中被大染色。
那么,西方媒体“社会主义红魔”这种极其片面的认识和评判是怎么来的呢?一是源自对苏联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应当承认,西方很多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于苏联时代,“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我们不走苏联路,但却一直戴着苏联的帽子。二是源于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特殊需要。冷战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一场全方位较量,成王败寇,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在这场战役中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从此资本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对社会主义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妖魔化评判框架没有解体,冷战思维也从未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场上退却。
第二,新保守主义盛行,在世界体系内造成意识形态的严重对峙,成为引发世界动荡之源,给中国国家形象客观塑造带来严峻挑战。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大势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美国领衔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一方面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继续追击,且变本加厉,对七零八落的社会主义阵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新保守主义掌权,在意识形态领域扩大了斗争范围,一切“非民主”意识形态,一切“异我族类”,全部纳入打击范围,由此造成冷战以来的数次地区大动荡。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苏联和独联体地区接连上演的“颜色革命”,以及2008年爆发的俄格战争,都与美国自冷战期间沿袭下来的意识形态战略难脱干系。目前,美国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攻略都碰到问题,战略收缩已成定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破产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小布什总统离任前突访伊拉克,本来想为自己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划”行个告别礼,结果却被伊拉克记者扎伊迪砸过来的鞋子抢尽风头,砸醒了他“民主化中东”的春秋大梦。
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斗争看,2008年上演了几场闹剧,比如拉萨
“3·14”事件的舆论斗争、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萨科奇坚持见达赖,德国声称要收容“东突”恐怖分子,这些闹剧揭示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跃升,在很多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议题中,中国的作用愈来愈不可缺少。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同程度地出现萎靡,需要借助中国的庞大市场,实现自身经济结构转型,恢复经济活力,为此不得不“委曲求全”,某种程度上放弃或降低对中国的遏制与批评政策,采取“务实”态度,选择与中国“对话”、“交好”。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清醒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妖魔化,一旦机遇来临(比如社会主义国家要举办奥运会),这种妖魔化行径便变本加厉,不遗余力。
第三,当前,世界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给世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西方发达经济体更是“希望中国能多发挥作用,多承担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这种强大源于改革开放。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大转折当中。从世界格局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光是中国国内的事,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换成国际范围看,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发展模式,西方学者也有人概括为“北京共识”。这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区别很大。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界限也十分明显。如所有制方面,我们不搞全面私有化,公有制为主导,土地改革绝不私有化。这与西方模式区别很大,与非洲模式、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都有区别。中国模式的价值,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化代的道路,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将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竞争态势再次发生方向性转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将处于长期共存、长期交往、长期竞争的格局。《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多年来,资本主义没有迅速灭亡,在我们可见的时间内,资本主义也不会灭亡,也在调整改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并存,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对方有用的东西。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在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方面,我们肯定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爆发的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也让世人看到,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要走弯路的。经济学家指出,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要回归凯恩斯,加强政府监管,这一点,恐怕又要向社会主义学习有效宏观调控了。查韦斯就调侃“布什同志向左转”。
这是世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战略,需要人们放弃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用平等、公正、客观、理性的目光去审视对方。就我们自己来说,要有开放的心态,有开放的勇气,敢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去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实践成功、行之有效的成果;更主要的,我们要建立一套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界的推介战略,主动、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模式的合理性,耐心地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战略,我想提几条粗浅建议:
1、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间交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主动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互通有无、共商发展的氛围。
2、充分利用党际交流渠道。对社会发展、公平正义、文明进步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世界各国政党——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展开交流的根本。
3、充分利用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往往是相对自由的。要想借助学界交流的平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就必须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国际化学者。具备影响西方学术界的能力和水平,以宣传、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为已任。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出去战略,绝不是搞输出革命,这可以从三方面说明: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目的只在于让国际社会认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至于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的建议仍然是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
第三,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瓶“美酒”主动“走出深巷”,向世界“解魅”中国60年发展之谜,与关注中国的外方人士一起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特殊性以及普适性,这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责编周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