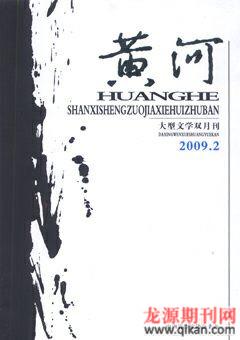聪明的花儿们
李 圆
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起北方的花儿。当然自己生长在北方也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春天来了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到花儿绽放。原因是北方初春的天气往往会反复无常,白天艳阳高照,晚上可能就有寒流入侵。即使一天之内,温差很大也是常有的事情。这种气候环境下,如果花儿贸然开放,难免会遭受“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命运。所以聪明的花儿一直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下寻找最佳开放时机,有时候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个月,在更晚来的某一日或某个清晨,蓦然回首满眼灿烂之余周身馥郁。于是明白,是花儿们开放了。
北方的花儿,因为善于等待而避开一场伤害,也避免夭折的灾难,从而也给自己带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和一生的繁花似锦。
大约在一个月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一场秋雨过后,就看到小巷里阔叶杨的叶子铺就的地毯,厚厚的,踩上去绵绵软软的。一度以为整个城市也萧杀起来,后来发现,乃至今天,仍然有垂柳的枝条飘扬着苍翠着迎接着北风的呼啸。渐渐明白是大的叶子对于风的阻力也大,承受风寒的能力也就差些。看似小的柳叶甚至针叶,平时貌不惊人,在严寒到来时却有着惊人的抵御能力。
听说过在海边生长着两种鸟,一种翅膀宽大飞行高远,一种翅膀窄小飞行低浅,但最后生存下来的却是翅膀窄小的鸟。在长久的生存训练中,生存环境的艰难需要生物来适应,而不是看你一时的高远和短暂的光环。
看到一个情感倾诉栏目中,一个女人一边怀恋着并未有过恋情的“初恋情人”,总想象着“如果”却忽略了日常琐碎,不懂得“规避”不懂得迂回,沉浸在想象中的“过去”,过着看似不幸的日子。不懂得迂回婉转改变现状,从而争取自己的权益,得以施展自己。
其实好多时候,做为旁观者站在远处的时候,以为如果是别人会如何如何,而忘记在自己的位置是否也能做到最好。
好多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怎样把伤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不妨也做朵聪明的花儿、针叶的树、小翅膀的鸟。
海娜
海娜是一种美丽的花儿的名字。乡下的童年,海娜花陪伴着我度过一段美丽的岁月。
海娜是俗名,应该叫凤仙花的。当然还有的地方叫小桃红、女儿花、急性子,更多的时候人们叫它指甲花。
清爽的夏天,大朵大朵的云彩忽而悠悠地信步,忽儿匆匆地迁移。间或会有斑鸠在“咕咕咕”地路过,带来动听的乐音。乡下姥姥家的院子里开着大把大把的花儿,馥郁的花香总能招来成群成群的蜜蜂和三三两两的蜻蜓。这个时候的我,只是在云彩和花儿之间悠悠闲闲地享受着特有的氛围。
对于刚刚懂得自己性别的女孩子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红的、紫的、黄的、白的海娜花了。花儿突然间开得浓浓郁郁,大约就是叫做“花团锦簇”的景象吧?于是学着大孩子们的样子,采来开得最红最艳的海娜花,轻轻地放在一个碗里或者臼子里,采到十来朵时,再找来适量的明矾和煤面子放进去,拿个杵子把混合了明矾和煤面的海娜捣碎。捣着捣着颜色就变得深起来,此时把捣好的花泥包在架豆角的茎叶上,包好放在一个干燥的地方,同时要找十几片架豆角上比较宽阔的叶子也放在一起。准备好这些工作,为的是晚上的盛大“节日”。其间忍不住地再三去看看,巴不得太阳早早下山。
晚上早早地吃了饭,急急地等着大人们忙完了坐好。为的是,拿了放得脱了水分有些韧性的叶片来把指甲包起来。晚上包指甲为的是睡觉时候相对安分些,包裹的时间也长些。加了明矾为的是不褪色,煤面起的作用是让花色更加艳丽。睡觉前往往会端着手指炫耀个没完,直到精疲力尽了,才恋恋不舍地把手指放个安全的不便触碰的地方,怀揣着少女的心事入梦。
那时候以为,染指甲是大人的事情,仿佛长大了才配得上这样的风情。因为看到过,赶在这个季节结婚的新娘子也会把手指甲染得红艳艳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迫不及待地把缠绕着叶子和绳子的手指解开,看看指甲是否染红。端详着自己的手指,想象中也便觉得自己就是待嫁的新娘子了。
白天高高地举着染了红指甲的手指向小朋友炫耀着,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在蓝天白云下似乎要飞翔起来。小时候的欲望是简单的,简单到只用鲜艳的色彩把自己装扮。直到在前几年蹦极,真正像一只鸟儿飞翔起来的时候,才豁然明白自己的野心由来已久,渴望着自由,渴望着飞翔的一颗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长大后发现,还有与海娜花相媲美的五光十色的指甲油。但指甲油颜色虽亮丽,却总比不上指甲花来得持久,来得自然。
而做最美丽的新娘子的梦,也似乎永远停留在那个懵懂的童年了。
朱槿
小时候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种喇叭形状的花儿。红的,紫的,青的……花太多了,凡有草、庄稼生长的地方都能看到,于是每到夏天就成了孩子们手里的玩物。
老人们管这种花叫“打碗碗”,解释为:此花近黄昏家里要吃饭的时候开放,差不多到晚上时分就枯萎了。因为它长得像喇叭,就好像喇叭样地唤人们回家吃饭。我理解可能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端碗”吧?
也许应了那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打碗碗”虽然花期短,但只要有一朵开了,就有争先恐后的花追踪而至,于是,孩子们便肆意地摘来。因其泛滥而且接二连三地开放,不像那些洋牡丹、大丽、鸡冠花,一枝花能开到你不想再看,却仍然怜惜着不肯攀折。在缺少玩具的年代,想想这些“打碗碗”花也是带给人们无穷乐趣的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书上说,这种傍晚开的花学名叫“朱槿”。如果不是介绍的图片和习性跟“打碗碗”吻合,我断然不会想到这么“贱”的花会有这么文雅的名字。
不知是突然知道它“高贵”的名字,还是真的开始怜惜起清纯的花朵了,蓦然觉得“打碗碗”也变得高大起来,虽然只不到两个时辰,或者连一个时辰也不到的花期,但它却努力开放着,把自己的美丽张扬到极致。就是那种“生如夏花”的灿烂吧?
想起昨天还在教训小孩,她总是太在意别人的批评,表扬的话听多了没有了动力,而批评和嘲弄的言语进了耳朵,眼泪就扑扑簌簌地开始做落体运动。情绪老大一阵子转不过弯来。
我总在告诫她,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你如果优秀自然是优秀的,不要因别人的好恶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有不对的地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这些道理对她来说又是似是而非的,好在七岁的孩子也能明白不要在乎别人,只管自己肆意开放尽情表现的道理。
可惜的是,城市公园里专门养的花们中却找不到“朱槿”,不能现身说法一番,也看不到它短暂至极的绚烂,颇为遗憾。
蒿草
城市里又在进行改造,把刚刚修好的补丁拆了,把新近建好的设施进行再“破坏”。整个城市千疮百孔,仿佛被扒掉光鲜衣服的中年人。
拥堵自然不可避免,遇上高峰期,从前一刻钟的路非要你走上个把小时是平常事。
外出办事,从路旁围墙缺口可以看见流动的水沟,还有水沟旁茂密的蒿草,顿时一股似乎只属于野外的清香扑鼻而入。蒿草几乎齐膝,这在城市里司空见惯的水泥高楼圈地中是少有的。远远地望去似乎是个坟场。间或有鸟儿飞过,唧唧喳喳几声之后又去找新的归宿,除此之外,倒显得格外安谧。
一阵风儿吹来,清香沁人心脾,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众人围坐在院子里,爷爷把蒿草扭成粗粗的绳状,点燃来驱赶蚊蝇。
夏夜的院子里格外清爽,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聚在点燃的蒿草周围,嗅着蒿草袅袅地散发出带着中药的味道,看着把蚊蝇驱逐甚至薰死。偶尔爷爷会讲故事给我们小孩子听,什么“刘秀十二走南阳”,什么“关云长败走麦城”……只是后来除了记得几个题目之外,故事早忘记得干干净净,大约心不在焉吧。要不是因为是夜晚早不知道会“野”到哪儿去了。
从小就“疯”,喜欢在小河里抓蝌蚪,喜欢在田野里捕蜻蜓,喜欢去地里拔猪草的时候顺便逮几只蚂蚱或者采几株野花。更甚的时候,把跟着上游水漂下来的的“菜花蛇”抓住来玩。
儿时的记忆在蒿草的味道中流泻出来。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总是蓝的,云总是白的,花总是香的,风总是柔的……
勿忘我
两天大风刮过,天空顿时又明媚起来,尽管还有点清明前的寒冷。
湛蓝的天空下脚步是轻盈的。
带孩子上街看书,又被深紫色的花儿吸引。簇簇勿忘我静静地伫立在鲜艳的花儿们中,安静、平和却又惹人怜爱。
抱了一束回家。
喜欢这个名字——“勿忘我”,只是谁又会记住谁呢,谁又会忘记谁呢?
不大喜欢别人送花,除非送花人没有暧昧的想法。酒鬼在博客里写道,梅兰芳拒绝收别人无端送他的银票并焚毁。不大清楚前因后果,但想到“文艺圈”里的是是非非也会不寒而栗,虽非高傲之人,但总还是不愿意去沾染那份媚俗。
家里的富贵竹还是年前买的,长着长着叶子就开始发黄,但因为自己是买回来的,便“敝花自珍”,舍不得丢弃就修剪一番,竹子兀自挺着,多了好些温情。
心血来潮的时候买了绿萝花,记得是专门去买薰衣草的,只是季节不对,花窖主也没找对。抱了绿萝回来也是弥补点缺憾。绿萝很听话——平常我是不管花儿的,包括喜爱的蝴蝶兰——唯有绿萝,我会把淘米水留下来浇灌它,每天一进门第一映入眼帘的就是它了,看着绿萝的叶子越来越茂盛,藤蔓渐渐地垂下来,像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青儿来的时候我把绿萝摘了几苗送她,后来她说拿回去的绿萝受冻夭折,特意打电话过来要我把绿萝早早摘了帮她养起来。
夜晚写字的时候勿忘我已经在我的案头了,微簇的花儿向上挺着,有点高傲的样子。青花瓷瓶是几个仕女图,并配了明朝郑澜的诗:
东风荡漾百花潭,翠袖迎风酒半酣。
好鸟隔窗催晓色,美人残梦到江南。
桃树下的仕女,幽婉若水,面如桃花。不知道仕女们是否间或会想起曾经要求“勿忘我”的某个人。梦里还是否留有某个人的体温或呢喃?
于是想起,有一种时间叫过去,有一种永恒叫瞬间,有一种爱情叫曾经,有一种失落叫忘记……
罂粟
看到罂粟的图片,一丛丛的妖艳一丛丛的烂漫让人心旌摇荡。
家里养过一株巴西木,去年的时候竟然结出淡淡的花蕊,开出串串白色的小花来,沁人心脾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楼道。
馥郁的香气使人想起小时候在姥姥院子里开放着的夹竹桃来。浓郁得发甜的花香侵袭着,不由地牵动你的脚步寻过去,看那粉簇团团的娇艳花朵。后来才知道夹竹桃是有毒的不过有毒的是它的茎。
关于花,叫不上名来的太多了,算下来记忆深刻的还是罂粟花了。最初见到罂粟花的时候,白的、红的、紫的,是在姑姑乡下的老院里。单片的花瓣,感觉上并无太大异样,有点类似司空见惯的另一种单瓣的有点茸茸的花,虽然我至今叫不上名字来。注意到它,是姑姑告诉我那就是鸦片花,才不由地多看了两眼。
看过消息说,在很早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实施精神侵略,在山西雁北一带曾教人们种植鸦片,从而诱导人们吸食,所以老早前还未禁的时候好多人家都种着观赏。
总觉得罂粟的美丽是因为它的毒性,就像美丽的女人,单单长着一副好皮囊又咋会经久不衰呢?更别提流芳千古了。
“能将花儿的娇艳与致命诱惑,结合得如此完美,也确非罂粟花莫属了。都说罂粟花是邪恶之花,只是这花儿本身,哪有邪恶与善良之分?”
不知道那罂粟是否因为它自身的毒而孤独?
然而,有着如罂粟一样的欲望却会时常地蛊惑、引诱着不安分的心。
欲望太深,填不平无底的洞。
于是不敢遭遇,不敢触碰。
抽身出来,冷眼旁观,妖艳归妖艳,热闹依然是它们的。
自然、舒畅、柔和、宁静,平淡中的寒暄和牵挂,自然而然的波澜不惊,才是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