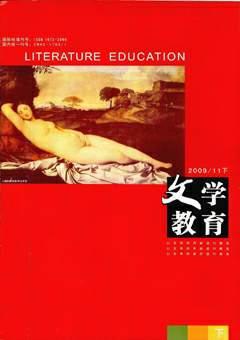疑惑影片《美丽人生》之美
影片《美丽人生》告诉人们,1939年人类正在开始经历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世骇俗的暴力运动。这是一场由法西斯发动的力图剥夺其他民族自由生存空间、时常又表现为灭绝人性的种族灭绝倾向的游戏运动。希特勒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不成熟的孩子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力玩具(坦克或更多)玩一场极不成熟的成人游戏。
希特勒,天真的以为依靠自己的粗暴武力可以永久征服这个世界,灭绝人寰的暴力是他游戏规则的核心,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的过份贪婪污染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时,世界上所有可供反抗的可能与形态,都将被激发出来,到这份上他的灭亡似乎只能是一个迟早的必然宿命。
直至影片前五十分钟,主人公基度在这场人生大游戏中将自己戏谑游戏姿态可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自称王子;始终做着“意念决定一切的游戏”;自称视学官在课堂上的横加恶搞;阔步骑着野蛮人涂抹的“犹太马”驶入酒店大厅将他人的未婚妻“公主”接走……
五十分钟前基度的戏谑带给我们的是愉悦,之后的画面流动将我们拉入的是一场游戏背后的深沉压抑之中。透过儿子祖舒华的两个主观镜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基度前后两次向儿子展示活力四射的“高抬腿”,均在一种被押送的呈现紧张的情境中彰显:一则是走向市政局,预示一场悲剧的即将开始,在外婆开始认可女儿婚姻并给外孙过生日这一“喜”开始的同时,游戏的态度就有了荒凉的陪衬,成为随后的影片叙述中不变的影片底色;另一则是被纳粹士兵押往刑场,路过儿子所躲的铁箱子时,再一次以高抬腿向儿子展示这场游戏中自己的游戏角色与本色。在这之前,父亲还是作为实体的“生”而存在过。
或许出于这种人生态度的萌发,使得基度对于儿子的“谎”变得顺理成章;或许由于纳粹的极端恐怖与单纯孩童世界的强烈对立,使得爱儿子的父亲的“谎”无所不在。儿子在自己生日当天被捕,在押送车上天真地问父亲基度:我们要到那里去?在与众目睽睽的冷漠目光对比里,父亲以一种嬉笑的表情与口吻,将此定义为一次很好玩的、不可轻易揭晓的、不为妈妈知晓的旅行。
到达集中营后,当以一场旅行来界定极端恐怖的地点即固定的集中营显得不恰切的时候,基度改变之前的解释:这是个游戏,是个游戏……我们一起玩,游戏必须守规则,男人一边,女人一边,还有军人,他们主持游戏,很严厉,谁一犯错,谁就要回家,也就是说,你要很小心,但你赢了,你就得到奖品——真正的坦克。
儿子:我已经有一架坦克了!
基度:这架是真的!
儿子:真的?
基度:真的,我本来不想揭晓的!
基度借这句话来贯穿自己定性旅行目的地不可揭晓的神秘感,更为了较好的保持谎言的延续性。坦克,是儿子祖舒华一出场就与之伴随的、贯穿影片始终的道具:当外婆告诉祖舒华明天要给他一份生日大礼,祖舒华反问: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坦克?当儿子嫌弃又脏又臭的集中营,想见妈妈的时候,基度拿坦克来搪塞他。
随后,德国纳粹军官走进宿舍,需要一个翻译来解释营中规则,不懂德语的基度却冒险自告奋勇走了上去。这是影片后半部分叙述中最精彩最滑稽荒诞的一幕,最叫人心潮酸动的蒙太奇段落。不懂德语的基度在绘声绘色地翻译着德国纳粹长官的指令:“大家到齐了,现在游戏开始……”他是在假借“游戏主持者”的权威性,告诉儿子这确是一场游戏,来证明谎言的正当性,指出游戏有三种被淘汰的理由:哭,想妈妈,喊饿。所有的一切似是针对儿子的孩童世界的。然而,儿子从其他孩子那里得知他们并不懂得规则,他们不认可头奖是坦克,也不懂积分。基度辩解:其它孩子太狡猾,不要相信他们,不可能没有坦克。
洗澡事件过后的游戏规则对于孩子变成了躲藏,“让人人以为你失踪,人人以为没有你这个人。”此时,在这座纳粹集中营,能够与希特勒的游戏规则进行抗衡的或许只剩下祖舒华这个孩子所因循的天真,他倔强地坚持不去洗澡,相信游戏,幻想坦克,只有他才留下了最后的一丝纯真。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游戏规则同样是建立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坦克的支撑,谎言无从建构,游戏更免谈规则,我们天真的孩子又怎能如此坚持?孩子再次执意要走,基度只好以顺从的假像,旁敲侧击儿子:我们在领先,早已经告诉你,但你要退出,只好退出,我昨天才看过积分表,(对狱友巴图)我们要走了,我们讨厌这地方,坦克已经造成,抹干净火嘴才开车,记得拉开油门,否则大炮会卡住轮带,还有那支机枪,多么精致,开车前记得松刹掣,我和他要走了,祖舒华要退出,本来驶着坦克走,现在要坐巴士,我和祖舒华走了,大家再见。我们讨厌这地方,(对迟疑不走的儿子)走吧,否则赶不上巴士,走吧,祖舒华!
祖舒华:我怕给雨淋湿,发高烧!
坦克,始终贯穿全片,是祖舒华的精神支柱,成为支持谎言的最强音。纳粹铁蹄狼狈逃窜后,孩子面前果真出现了一辆货真价实的坦克,谎言从此变得不那么纯粹。
影片到此,我想,若没有真坦克的出现,孩子美好幻想或许将被彻底击碎。这不出现的电影叙述拍摄本身,谎言的最终幻灭,纳粹营恐怖电影场景设置,是不是都有可能在儿童演员的心灵成长历程中留下阴影?
坦克最终呈现在了孩子眼前,这看似完美却使我内心疑惑的燃烧则更为猛烈了。使谎言不再纯粹的正是此前谎言的纯粹性的延续,纯粹性谎言却并不因此停止自身的延续:
祖舒华:我们赢了!
母亲:是的,我们赢了!
祖舒华:一千分,好开心啊!我们得到冠军!坐坦克回家!
母亲和祖舒华相拥的姿势共同构成一个V(victory)的画面造型,伴着母子俩甜蜜的笑容,爽朗的笑声,最后“胜利”的表达在此刻最终定格。
母子笑到最后、胜利到最后,均是以建立在谎言之上为基石的。在这整场游戏中,谎言建立在坦克之上,孩子则要躲藏,需要沉默,需要靠坦克建立谎言,建立起孩子心中的坦克,心中的梦想,支撑着他走向最后的胜利。
谎言,即使是善意的谎言,说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的残忍被迫只能以一种谎言的形式去遮盖它恶的一面,又该是谁的过错。
我们最终战胜纳粹,却只能以暴力抵抗暴力,是以孩子幻想着的暴力(坦克的)出现这一事实的最终实现为终点的。
这是一个快乐的传说?美丽人生?
“叫人不可思议”。可谁又能否认正是由于孩子对于坦克的依恋,对于暴力武器的崇拜,才使得自己的生命得以拯救……
秦洪亮,男,湖南科技大学文学系200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