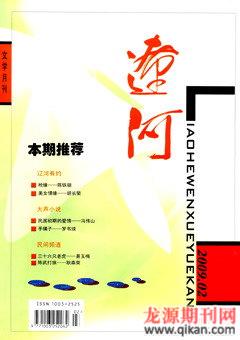居家有竹
冬 语
妻每每要刨去迎门墙下几杆竹的话出口,就像要断我四肢、取我的大脑般让我难受。
竹是她和孩子从搬迁单位移来的,虽只是几枝管插在根须上,在我家出笋长大,但也足令我嘴短;它不像杏树会吐洁白的花,结灿灿的果,不似葡萄铺开掌大的叶遮强光,紫透的酸甜叫你品到冬。这让我智短。我像个无赖贴在竹身上,不知是它护我,还是我护它。
它的到来。让墙面上的瓷砖画竹影湖光活了,湖水潋滟,山色空蒙,画舫也真就托福给我,鸳鸯逐对戏耍。我自己也变活了,像个吉祥童子,把那片荷叶负在肩上,那兰草多像我伸开的手指。我是金鱼,摆动膨胀的身子探访湖石,我的思绪都漂流起来,不能把握,不知它要领我去哪儿,交给谁。
我爱竹,比我爱竹者大有人在。大学士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难道可以替代肉吗?我这素食者一月不见一次肉,肠胃都不答应,身着紫衣的他怎堪忍受?想必宋代苏、粤、川、鲁四大菜系已经成型,苏翁肉吃腻了,只在盘中捡山珍野味来尝鲜,要不就是竹比肉来得香。李商隐就说:嫩箨香苞初出林,五陵论价重如金。吴昌硕曰:客中常有八珍尝,那及山家野笋香。倪瓒道:两两三三荷锄去,归来饭饱笋竹鲜。有这样的美味为食,与田园厮守何乐而不为呢?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天哪,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惟有让我这凡夫俗子仰之弥高,空悲切的份了。无怪乎,自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王子猷起,风流名士们不仅爱竹而且栽竹。
从来爱物多成癖,辛苦移家为竹林。
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
这等尤物,又有谁人不爱呢?为它付出一点辛苦真是超值享受。那岁寒三友是能随便请人家门的吗?堂堂四君子,又岂肯屈尊落座你的太师椅?相对竹林,后人对阮籍、刘伶等七人只以贤人相称,孔巢父、李白等也只落得个逸士雅号。是什么缘由,竹凌驾生物链顶端具大智慧的人类之上,享此殊荣?
竹对人帮助实在巨大,身边之竹席、竹筷、竹椅、竹床、竹篮、折扇、竹扁担、手杖、笔筒、乐器之笛、箫、胡琴、药用之竹茹、竹沥、竹黄、竹荪、远处之竹筏,竹桥……先民之竹箭、竹简、弓刀、真是数不胜数。释迦牟尼讲道的竹林精舍,汉代的甘泉宫都是竹子做的。同是苏翁又说: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竹有一大功能被今人埋没了,它会做人妻是名竹夫人。黄庭坚《竹夫人诗》:我无红袖添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青奴就是指的竹夫人。想炎炎夏日,搂着这样一个通体透凉的夫人,该是多么愜意。如沿用至今,为乡村、城市因贫困而索然寡居的农夫、大男们该解决多大难题,又会带来多少乐趣和精神慰藉。
竹还有一大功能被今人现代化了。想我先民更岁之夜把来竹竿焚得地动雷响,山魈恶鬼无以遁迹。饺子吃的该有多香,国之美酒醺醺于卧榻,四肢又何等舒畅。纵观今日之世界诸族惟我华夏人丁兴旺香火不断,计划生育难抑人口膨胀,为世所罕,竹子功不可没。它走出国门,成为开放之首,一朵朵焰火开放在异国大都邑上空已取代最初的硝烟,惹得黑白洋人呼声一片,踢踏舞步如癫似狂。唉!善良的中国人不懂报专利,拿自己的东西去敲人竹杠,欢乐又喜欢与人分享。
竹子的这些用途也好,衍生物也好,都是人赋予的,说它比人高贵,恐怕有些牵强。
竹子豪爽,且好伺侯。自人我家门,我从不曾喂它一口水,肥料也偏着心眼给了杏树、葡萄。但逢雨水,竹笋破土而出,瞪着眼看它一节节拔高。杏树漫开枝叶来压它,它不躲闪,不弯腰仍旧笔直向上。也从不知占地方,一尺见方,婷婷树起十根竿。秋风扫尽落叶,它葱绿故我。我出门进门,它总有意或无意触摸我,给我眼中生气,给我心里依恋。冬日的雪披在它身上。更显清丽端庄,如身披素纱的伊人。让我忽然觉得,风雪同样是我抵御得了的,我还很年轻,严寒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这不能不让我称奇,它原本有灵性。无怪乎古人要把它人格化。
应将古人比,孤竹有夷齐。——刘过
天地与正色,霜雪坚比心。——吕陶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王安石
我自不开花,免撩风与蝶——郑板桥
干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先贤们就这样比人自比,与竹子合而为一,产生藐视一切的精神魄力,成为人寰之绝唱。但这仍旧是人为的附会,不足以成为竹比人强的理由。
我不知我的竹子是何品种,源自哪里,血统是否高贵。它竿如凝脂的碧玉,节与节之间就像两根木棍对在一起,恰是这个丑陋看似脆弱的部位让我触到坚劲,古人比喻的缜密。它很少落叶,铺满地的,总是葡萄、杏叶,让你秋自心生,让你感叹人生苦短悲凉。竹带给我的情致,不次于佛肚竹、斑竹、紫竹、菲白竹、大眼竹……这些观赏竹。也不在名花牡丹、君子兰……之下。竹叶婆娑,总在讲故事给我听:谢缙在后门贴了一副春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
对门的员外看了不高兴,觉得只有自家才配享用这样的春联,命人砍去竹子。谁知谢缙的对联却长了两个字:门对干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
员外恼火命人将竹子连根挖去,谁知谢缙的对联又长了两个字:门对干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幸亏谢缙只写了竹子,如写房屋,老财或许会将豪宅挖去亦未可知。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征明。文征明要娶杜翰林的女儿杜月芳,杜小姐要试文征明的才学,指着石旁海棠说:花里神仙,无意偏逢蜀客。(蜀客,海棠别称。)文征明看到窗外竹子对道:林中君子,有心来觅香妃。竹子代替月老、红娘来牵红线,如放到现在,婚姻介绍所怕是都要倒闭,征婚广告都要从版面上留出一片清白。
我时常飘飘欲仙,每每以为揭开了竹子面纱,其实却是给我出了一道更大的难题。为竹所惑,想把它看得更为真切,便移上案头,宣纸笔墨伺候。屈指算来也是七度春秋,至今道不出个三、六、九。让我分不清何为关公的偃月刀,何为沉鱼的修尾,何为落雁的飞翼,何为野渡的横舟,何为伴飞的哀鸿,何为包拯的坚躯,何为板桥的遗骨……东坡先生十根竹子一片叶嘲弄的不是王琪,而是我。我这个南腔北调入躲在门后对人说:我不在家,却不敢高攀徐渭这个老师。我的字也正如汪曾祺老人所说之“丑术”难登大雅之堂。我的竹子呵,你翩翩而至我的小院,怎会用不知采自何处的狼毛,蘸着鸡血写给我这样一部难解的天书,让我心甘情愿做你的佣人。你身上的斑点是我滴下的泪痕么?
竹子用枝叶爱抚我,用身体安慰我,从它最神秘处飞出短笛,那牛背上童子的嘴边,田园的气息萌动,夜莺在歌唱。它比维也纳音乐大厅的长笛,提琴来得自然,也比指挥家晃动的身体来得轻松。不经意间我被带回老家,那是一个堂哥的孙子结婚,寒冷的日子,天下着雪,老家门前一群人在扭秧歌,他们为绿衣红腰带包裹,扑粉的白脸,印着几粒红果,腰肢间透出活泼,笑脸上卖弄着顽皮,这群有男有女顽皮的童子。一经打听,他们最年轻的都在五十岁以上,自发组织,每有喜庆,便来捧场,讨两盒喜烟几块糖角,为別人自己都带来欢乐。在这不缺乡情、亲情、友情、热情的故土,酒肉都不缺,我却感到少了什么。
想起来了,是竹子。这里才是它们的原生地,而这群人多像活力盈溢的竹子。我为自己的发现惊奇,认识竹子又要重新开始,就从竹筷开始把,把它探入一座矿床,访胜探幽,做到胸有成竹。
谁家没有竹子呢?谁又会心里没有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