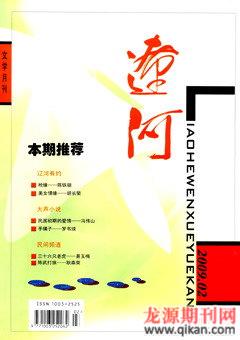站立成一棵大树
暗 沙
一个饭盒
八十年代初,我就读于乡上一所中学,每日往返二十多里路,厚厚的黄上总是迫不及待地掩埋我们的足迹,似乎想恢复本来的沉重,可调皮的孩子们总也不能一步一步稳健前行,他们忽而向前冲去,忽而又返回到原地,打打闹闹中,破坏了一种秩序,使得习惯了安静思考的哲学老人也不得不离开思想的领域,去欣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记载下这一段难忘的旅程。
那时,自行车在学生中算是很罕见的物件了,何况,我们都是贫穷人家的孩子,只能背负着贫穷的思想行走于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每天,村庄还在万籁俱寂中,我们就踩着月影上路了,身后是笨重难看的书包,以及一个烧饼或者一个铝制饭盒。提到饭盒,我总会记得一件事。那天,父亲给我从城里买回一个保温饭盒。这在农村是极少见的。我像以往一样把这个饭盒摆在课桌上,课间,同学们围拢过来,参观这个新鲜事物,可不知道哪位男生,故意拥挤同学,我的饭盒掉在地上,摔碎了,里边的饭菜倒了出来,还冒着热气,这可是入冬以来惟一的一顿冒着热气的饭菜。我哭了,这不光意味着中午得饿肚子,更重要的是摔碎了父亲很久以来才积攒起来的,用以表达对女儿疼爱之情的礼物。我蹲下身子,一边哭一边整理地上的一片狼藉,可这时,耳畔却传来一阵窃笑,这笑声终于把我彻底激怒了,丢下手里的东西,冲上去抓着那名高大的男生伸出了拳头……
这也是我入学以来第一次打架,我自然不是那名男生的对手,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回家的路上,我书包后还挂着那个绿色的保温饭盒,外表看着依然完整漂亮,但里边已经是支离破碎了,就如同我此刻痛苦的心灵。我的眼泪还在不时地流下来,偶尔的一滴,也会飘落进黄土路,可它太微小了,马上就会被扬起的尘埃覆盖,根本寻找不到一丝可渲染的内容。我的脚步也是缓慢的,沉重的,这倒和夕阳的基色很相衬,只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天上的夕阳之大,地上的我之渺小,相互比照下,更显示出我的孤独来。
当快到村口时候,天已经完全地黑了。我感到一丝恐惧,不由向四周望去,万物隐隐绰绰,因为失真,越发显得狰狞。我又要哭了,这时,却听到远处妈妈呼唤的声音:“霞霞,霞霞……”一声紧似一声,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好像声音之处就是太阳,我跌跌撞撞地冲了过去……
饭盒事件就这么成为我对童年记忆里的少数事件之一,那墨绿色的外壳紧紧箍住了我心灵的一角,而母亲的呼唤声就是那个角落里的一粒种子,在经过无数次的风雨,经过无数次的四季轮回后,最终茁壮成长为一棵大树。
可这个成长的过程是多么的不易啊,每每忆起,还会泪雨滂沱,朦胧中,我总会看到一个小姑娘走在黑黢黢的夜色下,走在寂寞无人的山路上,走在苍凉的土地上,走在风雨中……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旅程啊,我不知道,只感觉四季的更替是那么绝情,那么残忍,根本不容我的视线去适应。我总是行走在厚厚的黄土路上,抬头是尘埃,低头是黄土,而我只是黄土中的一名拓荒者,背负了一代人的理想和希望,因为有使命的存在,我只有学会成熟!
一条简单的路
如果说童年行走的黄土路充满了艰辛,那成长的旅程就是苦难的积累,最终诱发的结果,使得思想的外壳爬满了青藤,始终牵着我的灵魂向上攀登、攀登……
我是这样开始每一天的,六点起床,做早餐。七点送孩子上学,七点半上班,八点半准时到单位……一天的日程似乎没有闲暇的时候,可无论时间再怎么拥挤,都不能制约思想火苗的燃烧。
每日的七点半到八点半是我思索的时空,通勤车成为我思索的摇篮。我的摇篮总是行驶于这样一条简单的路上:路的两旁只有青山和土地。青山是真正的青,突兀的岩石也被周围的植被染色,好似十八岁的小伙子刚刚长出了一层淡淡的胡须,使得原本洁白、光滑的肌肤变得青涩起来;土地是真正的桑田,贫瘠的沙土上总不能生长出茂密、碧绿的庄稼来,不是稠稀不均。就是绿中泛黄,给人营养不良的感觉。当然,对于这些景色,我早已熟稔于胸。因此,我不再探出头去,只是在这个大摇篮里微闭双眼,任思想的野马驰骋于天地之间,不给予一丝的羁绊。在这个联想的过程中,我想到简单的旅途中,丢失了行李或遭遇了抢劫:想到了拥挤的街头,我的双脚失去了空间;想到了僻静的山路上,依然有枫叶铺出一条火红的道路;想到平静的湖水中被投入了石子;想到了蜿蜒起伏的山峦;想到了海域那边的人家……脱缰的野马赤裸裸地奔跑,只想寻求个自由和率真。
也因为这些无序的思索,使这条简单的道路变得不简单起来。路上的人物个个都被赋予了复杂的颜色,也因此绚丽多姿起来。
我看到一个个穿黄色马甲的修路工,一年到头,路面上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似乎在他们所能理解的概念里没有了季节的区分,他们总是猫腰低头,修整着那些不太平整的道路;我也看到庄稼地里的农民,在炎阳下播种,在秋风中收割,遮阳的草帽让路人完全看不出他们的年龄,甚至性别;我还看到……看到什么了?还有哪类人呢?我睁大眼睛,四下逡巡,可视线里似乎没有别的人了,难道这条路上只有这两类人吗?不,还有开饭馆的、娱乐厅的、修理厂、电厂等等,和养路工、农民比起来,他们似乎算是“大人物”,可怎么就没入我的视野呢?我没有为这个疑问找寻答案,生怕过于求真的思维反而使我的主人公失真,便对这些“大人物”只是淡然一笑,就转首继续去了望自己看得见的这两类人。不,还有一类,那就是如我般匆匆赶到郊区的上班一族,只不过我是闭着眼睛走人工作环境,而他们却是睁着眼睛在干活,并极尽所能把丑陋雕琢成美丽。
相对于我的这两类主人公,我的确是怯懦的,不敢睁大眼睛去生活,惟恐简单生活背后不简单的锋芒灼伤了我的视线,灼伤了我的灵魂。我只能在这条简单的路上,做不简单的思索,然后把思索的结果加以整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即便这个东西不能作为艺术品,不能被人们所欣赏。我仍然孜孜不倦。这种不知疲倦的码字生活说艺术是在创作,说白了就是打着艺术的幌子在替自己呐喊,因为没有胆量和勇气身体力行地成为一名雕刻家,只好借助假象中的灵魂来完成一次次的雕刻。对于这样的作品,究竟有几个人去品读,那似乎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而我却知道,养路工、农民所镌刻出的实物却是人人都能读懂的。
简单的道路,被我一次次用思想的钉子破坏,却又被我的主人公们一次次修补,这个破坏和修补的过程是怎样的逻辑呢?我不知道,我只在这条简单的路上,把思索的焦点集中到土地上,任季节的颜色把寂寥点燃,任思索的火花激扬出手下的文字,使生活的按部就班有了画外音。我跟着这些音符去谱曲,把道路上零散如柳絮般飘飞的思想重新排列,便有了一首首完整的曲子。于是,“破坏和修补”终成为一个统一体。
我感谢这条简单的道路,感谢这反反复复一小时的旅程,让我的生命学会以凤凰涅槃的姿态行走尘世间,永不消沉和懈怠!
站在阳光下
我想站在阳光下生活,而不是以坐、蹲或卧的姿态!我是对着一棵树宣誓的,树的背景是一片青灰色的天空,苍茫而寂寥。
陕北的冬季也一样是苍茫而寂寥的,阳光发出苍白的光芒,很直白地照在某个墙角,于是,那个地方就成了老农们的休闲场所,他们几乎都是一个姿态,双手插进袖管,蹲着、坐着,好像在等待一个宿命的结局。枯树上有个鸟巢,这是惟一遮挡人视线的实物,心灵因此会有些许的悸动,证明自己还活着。穿过鸟巢望向太阳,阳光突然间变得特别刺眼,惨白惨白的,缺少温暖。
山顶的这棵树不高不矮、瘦骨伶仃,说不清是杨树还是榆树,但绝不是柏树或柳树,柏树是万古长青,柳树是婀娜摇曳,他们的颜色和姿态很自然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位置。这棵树木的枝丫向四方自由地伸展开来,但丝毫没有影响周围的空旷,反而周边的空旷更显示了树木的孤寂。
为什么只有一棵树木,而不是很多棵呢?我不禁疑惑起来。
植树人自然不可能只种一棵树,当他们种下许多株树后,便把希望也播种进去,希望有朝一日,这里的山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青山。可盼啊盼,树苗一棵棵死去,他们希望的火苗也在一点点熄灭,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山顶还存活了一棵树的时候,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死灰复燃”,希望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就因为这棵惟一的树,这棵可以证明一个思想的树。
我凝视着这棵树,感觉有个很尖锐的东西刺痛了心灵,胁迫某种情绪醒来。我鄙夷地看着墙角懒散的肉体,看着只懂得享受温暖,而不自己去点火的人们,终于放弃了试图呐喊的声音,把目光转向了山峦。山峦起起伏伏,蜿蜒曲折,一直向远方延伸。我突然想,如果把这些起伏勾勒出一条线的时候,是个什么轨迹呢?人生的旅途也总是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或上或下,也把这些起伏勾勒出来,那会不会和山峦的起伏线重叠呢?
太阳似乎把自己完全地放逐了,正稳当地立于山顶,用温和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树,于是,那棵树披了一层轻纱,神情虽淡淡漠漠的,却少了几分萧瑟,多了几分豁达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