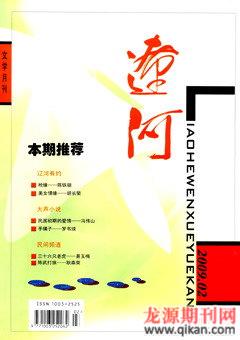年关
蒋文锋
我父亲把一片破瓜柴往灶膛里一塞,灶膛里立即就“噼噼啪啪”地火星四溅,火苗也跟着“突突”地蹿起来。
猴老满恁地还不来。父亲看着灶火上那一大鼎锅“唏唏”作响的水嘀咕道。
“嗷……嗷……”满村里都是猪们声嘶力竭的嚎叫声。腊月二十七,正是农家杀年猪的好日子,屠户作俏呢,杀一头年猪收五十块钱劳神费还请不到师傅。
正强来了,他在门外磨蹭着不敢进门。我父亲出门去喊猴老满碰见了他。“叔。”正强阴阴地叫一声。我父亲没答理,两只手往背后一剪又进了门。正强也跟着进了门。父亲斜一眼正强,鼻子里轻哼了一声。正强勾着头,站在门边;他左手的食指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整个一只手被右手托着;站了好一会才憋出一句话:“叔,砖厂里还有红分吗?”
“没有。”父亲的话硬邦邦地没有余地。
“再给我支点钱吧。”正强眼巴巴地望着我父亲哀求道。
父亲一听,来了火,瞪着眼睛怒道:“你掐着指头算算,你有多长时间没去砖厂了,你还好意思提支钱。”
正强知道拗不过我父亲,哭丧着脸走了。
正强前脚出门,猴老满带着两个徒弟后脚就赶了过来,大家就开始忙着杀年猪了。
“今年的砖价都卖到48块了(指一笼200块砖),你那个红砖厂是赚爆了,杀两只年猪都不过分。”猴老满手里忙着,嘴里也不闲,那口气是想挤兑我父亲请他喝酒。
“砖价是好,就是人手少,经理不过来。”父亲叹道。
“正强呢?他不是给你打下手吗?”
“那满崽古不争气。”父亲有点无奈地答道。
这时又有一个人踅了过来,是正强的老婆菊花。她在隔两丈远的一个屋转角处站定,闪出半个身子来朝这边窥望。
“菊花,是请我们去杀年猪吧。”猴老满眼尖,一眼瞥见菊花。笑问道。
“没年猪杀。”菊花苦笑着答一声。
“进大钱的人还恁小气,你放心。皮子不上两百斤,我少收你十块钱。”猴老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等菊花一句话。
“真的没年猪杀,年都不知道……怎么过……”菊花吞吞吐吐地说,说完就转过身去用手背搓了一下眼睛。
菊花这句话把我父亲的心都刺痛了,父亲狠狠地朝地上“啐”一口,然后冲着菊花冷笑道:“正强不是说天上掉金元宝了?恁地没捡到?”
菊花一听,顿时就抽泣起来了,“叔,正强是一时糊涂,今后不会再去赌了,他把自己的一个手指都剁了……”
我父亲一愣,眼前闪过正强那只缠着厚厚绷带的手指,心中像被狗爪子抓了一下,隐隐地痛。父亲没想到会这样,忍不住喘声大气。
正强是我的一个堂兄,原本也是一个很规矩的庄稼汉子。几年前,他傍着我父亲,合伙办了一个红砖厂;砖厂规模不大,说不上日进斗金,但管理好了,每年也有好几万的红利,日子也慢慢地殷实了。不料这时。正强发飙了,开始偷偷地去买码放吊;中了几回,胆子一下子大了。正强逢人就说:“天上掉金元宝了。”后来就一步一步陷了进去,连砖厂也丢到一边不管了。仅半年时间,把几年来辛苦积攒起来的十多万块钱输了个精光,最后连年猪也被人赶走了,落到连年都过不下的地步。
“赌博这东西沾不得,悔了就好,就是不该把手指给剁了。”猴老满一本正经地说。
可父亲还是说:“活该。”
送走猴老满,父亲就坐在屋子里抽闷烟,脸上像上了一层霜,过年的心情被搅得有些乱;他思量来思量去,心里不免有些自责,就觉得自己尚不如猴老满;这样一想,就不自觉地去了正强家。此刻,正强正托着那只被剁了手指的手蹲在炭火边发傻,像一只蜷着的丧家之狗。我父亲有点于心不忍,就掏出一沓钱来丢到桌子上,然后很温婉地说了句:“天上没有金元宝掉呢!拿去,先把年过了。”
正强抬起头,很迷茫地瞅着我父亲,眼睛里一片模糊,喉咙里“叽咕”噎一下,猫叫似的喊一声:“叔……”
我父亲顿时又来了火,他背过手去,挺了下腰杆,凶巴巴地吼道:“你提点神好不好!过了年给我老老实实待到砖厂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