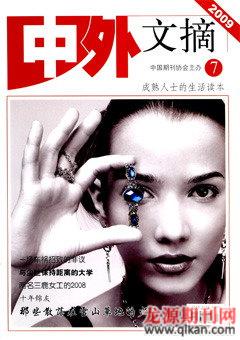卢新华的异国梦
杨 天
30年前的8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登出他的那篇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短篇小说《伤痕》。从那时起,卢新华便成为了一个传奇。而由此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
当鲜花和光环摆在这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他选择了抛弃、放手,迈出国门,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从零开始,延续他新的传奇。
从未离开过文学
1974年,他在山东曲阜当侦察兵。值班站岗时,酝酿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小诗——《侦察兵爱山》,刊登在《曲阜文艺》上。此后,他大受鼓舞,不时有诗刊登在当地的《工农兵诗画专刊》上。
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卢新华人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班里成立兴趣小组,发表过诗歌的他理所当然地被分进了诗歌组。可他却坚决“跳槽”到了小说组。“我觉得比起诗歌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小说的影响和读者群更大。同时,诗歌不适宜表达思想,自己对时代的思索,必须通过必要的人物形象才能表达。”
进校后,他读了大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希望能直接师承他们的文风,用小说的形式对现实加以批判。《伤痕》正是这种阅读背景下的产物。这个故事最初定名为《心伤》,后来改作《伤痕》。讲的是一个与亲情和爱情有关的故事:女青年王晓华,在“文革”中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多年来对母亲心存怨恨。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在她的自我改造过程中,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主流的“上进”行列。恋人又由于自己的家庭问题而不能上大学,被迫中止往来。八年后,重病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终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作品充满自信的卢新华,曾兴冲冲地捧着《伤痕》请几位老师和同学指教,结果他们并不热烈的反应就像一盆冷水,一度浇熄了卢新华心中的热情之火。这篇小说由此被他锁进书桌,但没过多久卢新华把它当做墙报稿上交了,上交的第三天,它便成为了班级墙报的头条,十七张稿纸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一场关于《伤痕》的争论在校园中迅速展开。复旦大学为此特别组织了一场学术讨论会。
由于写作突破了某些禁区,《伤痕》的公开发表并非一帆风顺。《文汇报》要去手稿后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杳无音信;后来转投《人民文学》又遭退稿,卢新华有些心寒。幸运的是,他最终等到了《文汇报》的消息,要求他做些修改后予以发表。
修改意见提了16条,比如: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因担心有人会说“‘四人帮都粉碎了,天下怎还会一片漆黑呢?”于是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的春天了”。而小说为了避免太过压抑,也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1978年8月11日,修改后的《伤痕》正式在《文汇报》刊登。
当天的《文汇报》被争相购买,紧急加印到了破天荒的150万份。
《伤痕》的发表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讨论,一直持续到次年秋。在此期间,大批因与《伤痕》题材类似而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作品相继问世。1984年底,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伤痕文学”作出评价——“一系列带有浓重悲壮色彩的中短篇小说,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伤痕》之后,卢新华也写过一些或长或短的小说,但再也没能产生那般轰动的影响。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远离了公众的视线。直到20年后,一本名为《细节》的小说出现在书摊上,有人突然惊讶地叫起来:哎呀,这是卢新华吗?他还在写书呀!《细节》仅是卢新华搁笔多年后的练笔之作,真正带他回归文学的,是2004年付梓的《紫禁女》。“我做过许多事,但在我的心里,我认为自己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文学。”他说。
在美国赌场当发牌手
1986年的一个夜晚,在素有“小巴黎”之称的美国洛杉矶西木区,一群踩着三轮车载人观光游览的白人车夫中多出了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男子。那是卢新华第一天上班,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客人,还被警察开了张罚单。正沮丧间,生意从天而降,一对白人夫妇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坡的骑行之后,汗流浃背的他得到了25美元车资和20美元小费。
从那以后,当地人经常能看到个整天乐呵呵地踩着三轮车的身影。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在中国曾经有着怎样的名气。
“那是一段让我充满喜悦和自豪的经历,我一直对此很得意。”卢新华细数踩三轮车的种种好处:没有时间的限制、可以练习英语、锻炼身体、还能挣到不少小费。“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卸下曾经的光环,一切从零做起,重新出发。既然三轮车夫都能做,我觉得自己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包袱了。”对于这条,卢新华尤其看重。
当年,《伤痕》的发表使卢新华一夜之间头顶众多光环: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他,成为“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他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到学校,经常一周数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毕业时,许多很好的就业机会摆在面前。思虑再三,他婉拒了最具诱惑的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一职,选择去《文汇报》做一名普通记者。“我很清楚自己是个情绪化的人,不适合从政。更重要的是,冥冥之中,我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可能更属于文学,更适合做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化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卢新华从未停止。而报社交稿压力下的写作令他颇不适应,渐渐地,他动起了经商的念头。这一回,命运并未眷顾他。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下海的文人,卢新华在深圳办公司的尝试不久就告失败。于是,另一个大学时就曾有过的想法浮出水面:出国留学。不久,怀揣着仅有的500多美元,卢新华踏上了异国土地。在那里,靠着踩三轮车挣来的钱,他在两年后攻下了加州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也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了美国。
毕业后,卢新华依然想先尽快完成养家糊口的任务。可在美国商海几经沉浮,所有的投资,除了在中国买了一处房产还算增值外,其余的都打了水漂。
1992年,卢新华谋到了一份薪水颇丰的工作:在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赌场当发牌员。这份似乎与踩三轮同样不太“体面”的职业,卢新华说自己做得很开心。
发牌员干了七年,从新手到“资深”。多年后回国,他为老同学们表演,一位同学事后对媒体说:“卢新华发牌手势之优美,已到了
艺术的境界”。
卢新华将人生比作进电影院看电影。
“每个人都想坐第10排中间的位置,但坐上去以后别人跟你说,这是他的位置,于是你往后坐,第11排、第12排、第13排……走到最后发现这才是自己的位置,但这个时候,电影已经落幕了……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对号入座,最迅速、最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放手如来”
赌桌之上,卢新华阅牌无数,也同样阅人无数。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赌桌上选女婿,因为赌性是人性中最突出的一种性质,赌品亦是人品。在我看来,发牌员工作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观察人性,思考人生。”卢新华对本刊记者说,“每一个民族的人都会在赌桌上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个性。像阿拉伯人多脾气急;犹太人几乎从不给小费;韩国人出手大方,但一输钱常常沉不住气;日本人比较斯文;中国人爱面子,永远随大流……都是我从赌桌上得到的极其深刻的感性印象。”
赌场的工作让卢新华对于财富有了新的看法。在他看来,财富具备水一样的特性,可以冻结、流动,甚至蒸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工作间隙,卢新华几乎全部交给了书本。他看书很杂,除小说、理论专著之外,还有《佛经》、《道德经》等。一次,他正坐在赌场入口处的沙发上研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忽听身旁爆出一阵大笑,一个客人摇着头对身边的—伙人直嚷嚷:“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闹哄哄的赌场里,还有个人在读佛经,滑稽吧!”
“那是一个最物欲的场所,看一个最精神化的东西会帮助你从这个最物欲化的世界里迅速解脱出来。”卢新华自有道理。如今,一本《金刚经》仍摆在他书桌上最容易拿到的地方。
从赌场辞职后,卢新华终于又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新书《紫禁女》让人们对他的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他当年的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在《紫禁女》问世后评价自己的学生,“在人生道路上兜了一圈,看似回到原来的起点,其实却是‘更上一层楼了”。
他家中书房里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一幅用玻璃框装裱的条幅,上书四字:“放手如来”。这颇具禅意的箴言,是卢新华多年来感悟出的人生真谛。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