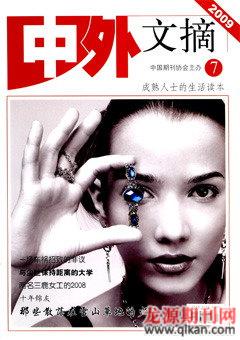两个美国间谍的中国故事
毕 苑
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一部很有趣的书:1958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
作者是一对年轻的美国新婚夫妇: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1949年前后,他们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同时利用工作生活之便,为美国海军部提供中国社会情况的报告。所以,他们在1951年因为“替美国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两人在中国监狱服刑4年后,被驱逐回国。著作是他们对改造经历的回忆。
李克夫妇是1949年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看到中国民众的悲惨境遇,美国教授的奢华和中国教授的寒酸生活,体会出学生、教授渴望变革和“解放”的心情;他们参加了学生们的国庆游行,感受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口号,看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作风以及他们眼中闪出的“荣誉的光芒”。1949年又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变动的年份。即使经历了北京围城,李克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承认和援助。但是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说,把李克的理论“打得粉碎”;就连他们领事馆的人员都认为,此后两国将面临着公开的政治战了。美国政府做出了政策调整,希望抛弃了蒋介石政府、加入到联合政府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外选择道路,甚至在8月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站起来,这样,“华盛顿方面就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们企图扶助推翻共产党与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人民政府的活动”。连李克都认为,“白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第31页)。而李克在北京的直接任务,就是探听人们所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对于李克,主要是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通过和清华教授的接触,李克不安地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步的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我和又安则在朝相反的方向走”(第37页)。李克原本认为,青年人的转变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从革命大学短期理论学习班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不过是个性不成熟的孩子;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为李克所尊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李克觉得,这些人有坚实的西方教育基础,要动摇他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忠诚,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的好几位亲密朋友都完全转过身来反对西方,他震惊了,“感到非常沮丧和伤心”。特别是1951年,李克“怀着厌恶的心情眼看着燕京的教师和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冗长的群众自我检查会”,面对着同事、朋友、亲人和大堆人群,“他们痛斥自己过去崇拜西方的奴隶思想”,“情绪激昂”甚至“禁不住痛哭流涕”。李克难以理解的是,“除了集体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朝鲜战争产生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之外,看来这种集会并没有应用任何压力”(第122页)然而正是朝鲜战争,成为李克夫妇个人生活上的转折点。
李克29岁生日那天,中国军队雄赳赳跨过了鸭绿江。他们意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对个人前途可能带来的威胁,希望尽快回国。但是事不遂人愿,在反击国民党特务和破坏分子的运动中,他们先后被逮捕,开始了4年的牢狱生涯。
“改造”在李克夫妇的中国经验中,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中国人积极“改造思想”的场景,不时在李克脑中浮现,现在轮到他这个美国人了。
他参加9号监房的学习,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听大家谈“地主是怎样得到土地的”;讨论并不限于毛泽东论文的范围,这让李克感到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的乡村,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成为‘中国通的本钱天天都在增加”(第133页)。但是他承认,他们都低估了监管人员,并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喊几声“毛泽东万岁”或者是“斯大林万岁”就可以过关的。当他想用轻松的自我检查来浑水摸鱼时,引起了组长的愤怒。李克也被激怒了,豁出去说:“我搞不通我为什么不能请律师。”这个思想立刻遭到大家的批判,有人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第156页)。这样的回答当然不符合李克所熟悉的“传统习惯”,但是他觉得无法反驳。虽然他承认,“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反对墨守法律的”,不能用常规法则要求当下的法权。但是落实到个人,这个规则未免显得冷酷。
“改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进行。除了交待罪行外,李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如黑人问题、政治腐败、公民自由、匪徒组织等,都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某一天,一个犯人说美国的工人都住贫民窟。李克愤怒地反驳:“我父亲就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并没有住贫民窟。事实上,我们工人的生活全都比你们中国人好得多。”但是另一位投机商犯人立即坚持说,李克的父亲一定是一个工贼。这些鸡毛蒜皮的口角不算什么,“最最难办的就得算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了”。不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一位同组犯人老廖看到报纸头条新闻上写着“击落敌机二百架,重创三百架”,立刻欢呼雀跃:“我们消灭了五百架美国飞机。”李克脱口而出:“两百架。另外三百架飞跑啦。”(第192页)在和狱友的争辩中,李克意识到自己是坚决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
但是,李克对于朝鲜战争的敌对态度在1952年冬季之后发生了转变。
起因是老廖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国战斗机驾驶员在朝鲜一个村庄投放汽油弹后被击落,中国军队出发去捉拿他。同时有一架美国直升飞机前来营救。可想而知,就在飞行员攀登飞机软梯、营救即将成功的时刻,中国军队开了火,把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都击落了下来。故事很简单,刺激李克的是中国人的反应。听故事的人“全神贯注”到“着迷”,李克恍然大悟——大家对这些死去的美国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国人是没脸、反复无常的敌人,只是一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甚至来自我的故乡西雅图。接着我又想到,就在这个时刻,在美国一定有千百人正读着一个极其相似的故事,不同的仅仅是,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中国人。”
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这一段叙述打动。这次经历使李克彻底地认识到,“那些死去的都是有脸的人”,“朝鲜战争必须停止”(第192页)。
各式各样人物的交往和改变给李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中国监狱的“改造”和狱友的变化有了
深入的体会。
1955年底,李克的小组新来了一位狱友,这人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兵,脑门上横刺了一句恶毒的反共口号。他的罪行并不重,人也不坏。大家反复讲道理,终于让他不再担心自己被杀头,而且对于过去的行为有所痛悔。但他还是沉闷着,发呆,从不参加学习会。最后大家发现他的心结就在那额头上的刺字,于是纷纷安慰他说,新社会不会有人为这个责备他。但是所有的劝慰都无济于事。忽然有一天,他被叫出了监房。整整一天,“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前额包上了纱布,但是眼睛却闪烁着光辉”。原来,政府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手术去掉了他额上的刺字。“从此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完全变了,简直像奇迹一样”(第225页)。他说,政府帮他卸掉了“千斤重担”。
李克也同意,对于犯人的改造,最重要的是监狱干部给犯人的直接帮助。他认为,在1951年到1952年间,监狱干部的工作比较机械消极,过分重视阶级出身。1955年后,监狱当局也认为过分惩罚是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缓了许多。他举例说,一位管理员很让人感动。他查夜极为细心,大家总能听到他在检查监房时喊:“把肚子盖好,不要着凉啦。”这个关照每每让李克发笑,因为他始终“不能严肃对待中国家庭认为肚子特别容易受寒的道理”(第225页)。
李克后来体会认为,“中国政府是真正想做到公公正正的”(第157页)。他们监狱的卫生和生活也始终在改善之中。大家向蚊子苍蝇和寄生虫发动猛攻,对老鼠采取各种措施,注射防疫针,狱医用各种办法保护大家的健康;伙食也大大改进了;“食物调配得很好”,“定期洗澡”还有“正规的体操制度”,生活上“舒服多了”(第169页)。
这样,“到了1953年初,大多数在监狱呆过一段时期的犯人都开始有某些进步的表现”。改变在于犯人们不再留恋过去或者幻想国民党重来,连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也不再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了。李克总结认为,“这种转变一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的理论的胜利,但主要的还是历史本身促成的。”这“历史本身”是什么呢?李克讲道,1953年1月的一天,监狱的扩音器传来了公布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美国人愿谈判,我们就谈判,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打,但是,我们要同时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这时整个监狱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新建设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老廖“眼睛闪烁着光芒,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才知道做中国人的光荣”(第221页)。
上世纪50年代的粮食问题当然还是困扰国家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的问题。李又安描述了女狱友们一次关于统购统销的讨论。当时一位年纪较大的妇女抱怨统购统销“太不像话”,让她家买不够蒸馒头的面粉。有人温和地解释说:“可以尽量买玉米面和小米,并不是不够吃呀。”小组长孟小梅来了一番讲解和教育:“你再想想这对全中国的其他人有什么意义。过去,在你家成天吃馒头和大米饭的时候,那些人能吃上点儿高粱或是黑豆就算是走运了。还有许多人得靠白薯和树叶过活……要是像你们这样的家庭还是吃那么多白面,那白面就会不够大伙儿吃的。咱们农民所增加的产量还不能满足这种急剧增长的需要”(第256页)。妇女们很快都接受了小组长这番道理。
越到李克牢狱生涯的后期,他就越能发现狱友们对于国家进步和个人生活的前景所怀抱的美好畅想。
李克笔下的狱友老韩,缺少教育但并不愚笨。他跟李克学会了加减乘除、小数、简单代数和几何,甚至后来比李克算得还快。他喜欢跟李克讨论农业问题。有一次,他们说到天气变化对庄稼收成的影响,老韩说灌溉太吃力,李克就以他的美国经验随口提示道:“既然华北经常刮风,为什么不利用风车呢?”“风车”引起了老韩的极大兴趣,他连连追问。李克只好把他在美国中西部看到的风车画了一个草图,但是老韩不满足,“要我把每一个小部分一直到一根轴一个齿轮都解释给他听。”李克勉为其难,“终于用了几天工夫设计出一个风车图形”,老韩则“希望释放回家后能在乡村的水井上利用这种风车”。他们畅谈未来的美景,老韩显出欢悦的神色说,“我回家之后要弥补的事情可太多啦。”(第280页)
我们的心情随着李克和李又安的描写变得温馨、感动。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似乎要在那个时刻展开。李又安甚至说,有一天,她们组几位女犯人坐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新建设计划。
小杨说:“过去在中国只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楼房,现在北京就要有好些高大的建筑物了。”另一位妇女得意地说:“我到过一座七层高的楼房。”她的话受到小杨善意的嘲笑:“我看,李又安大概不会认为它很高。他们纽约有真正的摩天大楼,是不是?”当李又安为大家描述了帝国大厦之后,大伙儿啧啧称奇:“它怎么能不倒呢?”“你上过最高那一层吗?”之后话题回到中国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妇女们满怀信心地说:“是的,美国领了先,那儿的工人建设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再过二千年你瞧瞧我们的摩天大楼吧!”(第270页)
读到这里令人泪下。
1955年,李克夫妇先后被“驱逐出境”,最终和亲人团聚。他们面临了“北京释放美国传教士和亲共学者”之类报道的尴尬纠缠,同时他们也对美国麦卡锡尾声时代的复杂性缺乏心理准备。但是他们最终发觉,“美国的民主传统很深,足以打垮这种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倾向”(第311页)。他们不愿改变中国经验带给他们人生观的影响和基本结论,诚实地留下了这本书。
这本书在我们的图书馆静静地躺了许多年,图书管理员费了一点周折才把它从“特别反动类”图书中找出来。从当年手写的卡片借阅记录来看,读过这本书的人并不多,8位读者,借阅年份顺序为1959、1960、1961、1962、1964、1969、1975和1977年。在电脑取代了手写卡片之前,再也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电脑时代,“反动”已经成了一个令年轻一代发笑的词语,一个陈旧到反成先锋的概念。回头来感受那一段历史的温馨和阳光,让人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复杂。
(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