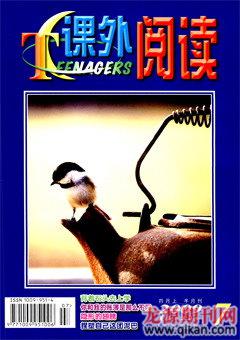打开心扉就看到世界
金 薇
十四岁那年秋天,我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母亲带着我离开小镇,到了陌生的县城,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母亲说这是她的幸福,她希望我理解。我很努力地点点头,泪却涌上来。
坐在县城最好的中学的教室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下课,一个人看着窗外高高的白桦树发呆,再或者,仰头看着天上不停变幻的流云,心飘回了小镇。
在这样的恍惚中,我的成绩直线下降。人也变得像个刺猬,平时沉默得像潭死水。偶尔说话,就是跟人大声吵架。我成了同学限里不折不扣的怪物,没人爱搭理我。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母亲有她的幸福,没人在意我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每天我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在校园里,孤独与绝望如影随形。
那是一节音乐课,我拄着胳膊挡住脸,不肯发出一点点声音来。戴着黑边眼镜的音乐老师何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面前,“你来把这段谱子唱一遍!”我慢腾腾站起来,却坚持沉默着。
课间,我跟在何老师的身后去了办公室,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一阵狂风暴雨,心一点点变冷变硬,心想:如果她训我,我绝对不会客气。
何老师搬了把椅子给我,让我坐。她说:“叫小薇是吧?”我抬头跟她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点了点头。她说:“能跟我说说为什么不快乐吗?”她是唯一一个问我快乐不快乐的人,我的眼里涩涩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呢!
何老师笑了,眉眼弯弯的,像一弯新月,她的短发上别了个小小的鹅黄色的船形卡子,很漂亮。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封闭自己,多交几个朋友,快乐就会找上门来的。”我仍是一言不发。她拉开抽屉,拿出几本书和杂志递给我,“喏,拿去看看,或者会对你有帮助!”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几本《演讲与口才》、《成功之路》。我拿着那些书出门时,何老师喊了一句:“如果你愿意,我想教你打扬琴!”我的背影顿了一下,很快地走出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屋的床上翻何老师借我的书。它与我习惯看的那些忧伤的青春小说很不同。我看了两眼放下,闭上眼睛,想起何老师笑眯眯的一张脸,想她问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的心里颤了一下。睁开眼,捧起杂志,仔细地读了起来,原来,人与人交往,有那么多技巧,一句话这样说可能让人如沐春风,那样说就可能让人暴跳如雷。像我,别人跟我说话时,我总是用反问的口气:“有问题吗?”“不行吗?”“你管得着吗?”一派拒人千里的模样,这样,谁会愿意跟我做朋友呢?
两天后,我把书和杂志还给何老师时,她正坐在阶梯教室里的扬琴旁轻舒双臂打那首《喜洋洋》,曲子欢快得让我的心几乎都成了一只鼓鼓的帆,一曲罢,她问我:“喜欢吗?”我不知道她说的是杂志还是曲子,但是,真的我都喜欢。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到音乐老师光洁的脸上,落到我的身上,暖洋洋的。那天,何老师握住我的手拿住两根琴竹在扬琴上叮叮咚咚地弹奏,那天,我听着自己打出来不成调的曲子,咯咯地笑出了声。
从阶梯教室里出来时,何老师又借了我两本最新杂志,她说;“书不是白看的,看完这两本,你得给老师找来一个好朋友。”我瞪大眼睛,脸涨得通红。何老师说:“我看过你写的作文,很有思想的,相信你能行!”
随后的几天中,我一直在找机会跟班里的同学说话。可是,封闭了自己那么久,冷得像冰山一样,突然跟人家热情,不是很奇怪吗?
突破口是从我同桌那开始的。她很马虎,丢三落四的。平常,上课忘了带书。就干坐着。我是不愿意跟她一起看一本书的。那天,她的语文书又落在家里了,我把自己的书往“三八线”那边推了推。她抬头像看陌生人一样看我,我冲她笑了笑,又把书往她那边推了推。其实,跟人交往有时就是很简单,你的善意她会知道。
没几天,同桌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那些积极向上的书刊也成了她喜爱的读物。我们一起站在何老师面前时,何老师的眼睛又笑成了弯月。她说:“小薇,永远记住,打开心扉,你的心才能让别人进来。”
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记本的扉页上。慢慢地,我有了很多朋友。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我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辩论会,我甚至去电视台演奏扬琴,生活仿佛在一夜间繁花似锦起来。我知道,在我忧郁得如秋天的湖水时,是何老师帮我开启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