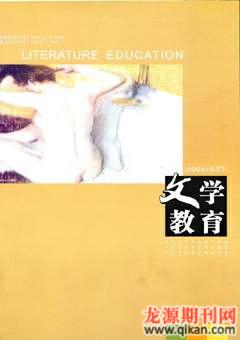乡土文学中的语言与新历史主义
林 玮 刘思宇
一、语言
读奇正小说的时候,汪曾祺的那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迄今为止,奇正先生所发表的小说无一不是语言风格上的用心之作,个性尤为明显。奇正短篇小说的语言可以简单概括为:乡土、生活、口语——“乡土”是对小说整体空间语境的判断,奇正的小说没有都市的喧嚣嘈杂,而在县城和农村之间游走;“生活”是双关的,它既说明奇正小说语言指向“生存”,也指小说所营造的场域是人活着的真实状况;“口语”则是对奇正小说语言形象的基本判断:日常化口语式的讽刺。
从早期的《“古董”出关记》,到《天堂里的微笑》,再到《寄生草》乃至新近的“写真系列”等,作家语言呈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变化。语言的变化伴随着奇正小说走向成熟与深刻,体现着他对小说文体的驾驭和对文学现实价值的逐渐认同。对比《小吃店里》、《桂花树下》和《心梗》、《地火》,奇正对语言的审美趣味已开始改变着他所关注的事件和意义。这符合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结论: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奇正的小说展示了汉语形象美学中常见的维度:用质朴的白描式手段刻画出苍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图。在文化现代性的视野中,这种语言形象可能是落后的,或者缺乏实验性的。但就其作品而言,奇正小说的语言作为作家独特的个性,也为久困于浮皮潦草的汉语形象提供了一种反思的途径。
二、新历史主义
奇正小说的故事基本发生在当代(建国以后)。在刚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包括对新生活的理解)随即被扑面而来的革命运动浪潮颠覆的时代,“人性”开始退缩,生存哲学成为“时代的症候”。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底层人民仍然为着生存(或更好地生存)而退步求全。在《阴阳界》与《探戈》中,这种对人性的历史忧患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家看似随心所欲的笔触隐藏着深刻的焦虑:人,究竟该怎样活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在以一种隐喻性的方式讽刺着历史。
这种讽刺还表现在人物的“行动元”上。举《寄生草》为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救赎”与“被救赎”的一组双关行动元。即赵厅长接受冬桂生理救赎的同时,完成了精神的救赎。作家有意安排救赎与被救赎者在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地位,由此,双方间的张力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呈现出波澜起伏。这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是颇为不易的。此外,现实社会的强大压迫下,个体生命的抗争也是奇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行动元,如《三轮车上》、《大胡子相亲》等。
说到底,奇正小说关注的是被权力话语和社会状况压抑着的命运在自然生存状态中的反弹。奇正笔下的人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没有身影,却构成时代变化的主流。在承担“救赎”角色的行动元中,作家有意安排了女性角色,如《孽海情花》王海英、《地火》秋蕊等,她们大多没受过教育,但其凭借世事洞明和人情达练的社会密码自我塑形,实现了人格上的超脱。可见,作家在暗示着他的人生观:人性建立在生存基础之上,道德伦理无不要
符合人性的天然发展。只有自由而全面的人性,才能实现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状态。
三、语言与新历史主义
研究奇正的小说可以有多种角度,但仅限于小说的人物、故事的情节、对话与心理描写,或谋篇布局的结构等方面,则未必能深入地揭示出作家及其文本的独特价值来。这是我选择语言与新历史主义视角的缘由。
小说是作家经验与虚构成分的重新组合。奇正先生长期的教学生涯和政治经历,及其生活的艰辛是创作的上等素材,然而这并不是其小说文本生成的唯一理由。个人经验、理性价值判断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作家所独有的知识范型,通过知识范型,小说家得以把握现实。“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会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范型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控制着作家语言的风格和运用。奇正知识分子的知识范型决定了其作品表现的是人、人性、社会与生命等多个宏观范畴的精神意义,运用的语言是朴质的口语。奇正的小说语言干净而单调,可视为文学语言的逆时回归,具有相当的审美自主性。在知识分子(精英)的认识范型下,这种小说语言或许难以融入众声喧哗之中,甚至可能边缘化为独白。
我宁可相信奇正小说正是这样一种群氓时代的“精英独白”。
林玮,刘思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