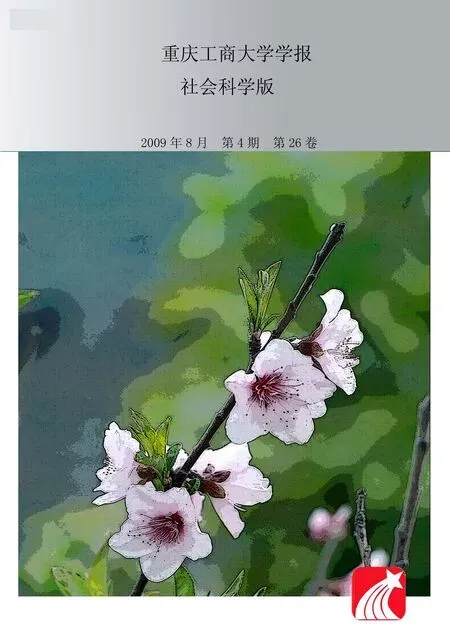两名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情结
——论《红果丛林》的女性主义主题*
娄玉霞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一、引 言
于1973年问世的《红果丛林》(Rubyfruit Jungle)是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1944-)的处女作。该小说主要向读者展示了一名女同性恋者的成长经历。主人公莫莉·博尔特在孩童时期同自己的女伙伴发生了极为亲密的肢体接触行为。中学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她与校拉拉队长身上。大学时,莫莉因与舍友成为同性恋人而被校方开除。之后她只身到了纽约,半工半读地完成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学业,在此期间,她先后与一位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产生亲密关系。最初,因各主要出版社认为该书内容颇具争议性,故都拒绝出版该书。最后,一家小型女同性恋出版社——女儿公司(Daughters Inc.)出版了该书,仅在四年的时间内,便售出了70,000册。该书的意外成功引起了主要出版机构的注意。1977年,班坦图书公司购买了该书的版权,又发行了300,000册。
该书赢得如此之大的读者群(大部分为女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布朗本人是一名同性恋者,并积极参加了各种同性恋及妇女组织和活动。她协助成立了纽约大学的学生同性恋联盟(Student Homophile League);之后加入了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还成为激进女同性恋(Radicalesbians)的一员。这使得她对女同性恋者的处境和要求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并使之在作品中得以体现。第二,正是由于布朗了解同性恋群体所面临的误解和歧视,她在《红果丛林》中塑造了一位集勇气、智慧、美貌和乐观精神于一身的主人公,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消沉、悲观、丑陋的女同性恋主人公形象。第三,该小说出现于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1969年的“石墙酒吧造反”(Stonewall Inn Rebellion)将隐秘的同性恋群体推到了聚光灯下,揭开了他们反抗主流社会、争取权利的序幕。“同性恋解放运动”(the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紧随其后。在这种环境中,很多女同性恋者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创作。“虽然成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不是第一代公开承认她们同性恋关系的群体,但她们却能够确立有记录以来最有生气、最有说服力的‘同性恋文化认同感’(sense of lesbian cultural identity)”[1]。《红果丛林》恰逢此时成书,可谓占据“天时”。
《红果丛林》的畅销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简·鲁尔(Jane Rule)指出,“主人公莫莉生来就是一个激进的同性恋,拒绝各种对女孩的传统限制……。莫莉拍摄了一段关于她继母的影片作为其学位论文,……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无法逃脱充斥着偏见的狭小世界而只能埋头做事的女性。同时,它强调了莫莉在争取自由过程中表现出的非凡的反抗天赋和智慧”[2]。莫莉的形象完全突破了以往小说中悲观厌世的同性恋形象。另外,该书作者也是同性恋者。因此,很多评论家和学者将此书归入同性恋小说之列,并认为该书是“石墙酒吧造反”后同性恋小说的杰出代表,“象征着一场运动、一次姐妹们发起的斗争。”
由此看来,在涉及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红果丛林》可谓是独树一帜。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书中的其它主题。该书作者布朗曾指出,“我一视同仁地描写书中所有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关注、值得描写”[3]。经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红果丛林》一书关注的不仅仅是同性恋问题,女性主义也是其探讨的焦点之一。正如该书主人公莫莉·博尔特(Bolt有“门闩”、“猛冲”等意思)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她一直试图冲破父权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限制,突出女性的地位,找到女性真正的自我。
如今,虽然同性恋文化已培育出了自己的理论——“怪异论”(queer theory),但不可否认,在其发展初期,同性恋文化从女性主义汲取了大量的理论养分。例如,女同性恋者利用女性主义的“反本质论”(anti-essentialism)揭示异性恋为确立并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如何构造性正常/性变态的二元对立。正是基于此,在一段时间内同性恋文化被冠以“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之名,而且“在女性主义者发掘和发展女性文化的活动中,大部分积极分子是女同性恋者”[4]。虽然最终女同性恋者与女性主义者分道扬镳,但前者与后者在文化和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仍然清晰可见。《红果丛林》虽被称为同性恋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作品中却渗透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分析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女性主义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布朗和莫莉的女性主义情结进行分析。
二、社会文化环境
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第19条项宪法修正案,美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至此,美国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在二战期间,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从事曾经为男性所做的工作,支援前线。这使得她们相信,并不是只有男性才能养家糊口,女性同样可以做到。但二战后,麦卡锡主义四处蔓延,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都被视为共产党,而且“反共偏执狂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强调必须巩固‘核心家庭’”[5]。于是,大量刚刚摆脱家庭桎梏的女性又被赶进了牢笼,继续担当家庭主妇、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据统计“50年代末,美国妇女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1400万姑娘不到17岁便定了婚;……职业妇女的比例从1930年的15%降到了1960年的11%;……独身妇女比例从19世纪末的20%降到二十世纪中的5%”。[4]当时的社会环境只容许女性在家庭这个范围内活动,女人的职责就是操持家务、服侍丈夫、照顾孩子。莫莉的长辈詹妮弗和卡丽都以此作为她们的生活准则。
詹妮弗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婚后她有了两个儿子,在1956年夏又产下一子,但婴儿早夭,她也因患癌症面临生命危险。可她从不把自己的痛苦向别人诉说。她丈夫说:“她从不告诉我她的病痛。她什么都不和我说。如果她早让我知道她感觉不对劲的话,我会带她去看医生的”。[6]她母亲弗洛伦斯对她的评价是:“我女儿,詹妮弗,从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觉得找医生花费高。还有,不管她有什么麻烦都会牵扯到肚子里的孩子……她做了她认为正确的事”。她的姊妹卡丽说:“女人得了病总是不让她们的男人知道。可詹妮弗比大部分人更沉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要求女人放弃自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丈夫和孩子。正因为詹妮弗的行为符合了这一要求,她的葬礼上“挤满了咖啡谷(家乡名)的男女老少”。
其实,并非詹妮弗本人不想把痛苦告知他人,而是当时的父权社会不允许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失声状态,处于“他者”位置。因此,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语言系统中完全找寻不到她们的声音,她们自己也成了男性语言的使用者。她们没有话语权,意味着她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她们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履行并逐渐认同父权社会向她们提出的要求。这使得女性最终失去了自我。
《红果丛林》成书时正值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人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女性所处的“他者”地位上,“其主要的特征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全面清理批判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7]莫莉向我们展示了她为颠覆父权文化所构建的性别角色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玩“医生——护士”游戏时,尽管伙伴谢丽尔反复说:“只有男孩才能当医生”,[6]莫莉却坚持扮演医生;母亲卡丽让她学做家务,她却从家中逃跑;让她母亲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她让他们(男孩们)做什么,他们都听她的”;在学校,她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而“卡丽和弗洛伦斯感到蒙羞”,前者认为“我(莫莉)是女性的叛徒”,后者“的确认为这很奇怪”,所以“只要我在家就得和她们争吵”;在纽约,莫莉决定学习导演专业,希望能“打破电影界的性别障碍”;关于婚姻,她的态度是“我就不结婚”。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已经接受了男性确定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就不难理解她们为何对意欲改变女性现状的积极分子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这并不能阻挡莫莉,她要通过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传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体制发起挑战,要证实父权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定位是错误的,要“彻底铲除滋生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土壤” 。[7]
三、打破家庭、婚姻和就业三方面的性别角色束缚
布朗本身作为一名积极的女性主义者,在《红果丛林》中深刻反思了女性所处的社会从属地位。她笔下的主人公莫莉试图从各个方面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
家庭被认为是父权制的主要机构,是父权制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维护男性的统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每个家庭中,男性家长被赋予支配妻子和子女的绝对权力。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权威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家庭是一个财政单位,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家长。传统认为,男性外出工作所获得的收入是一个家庭最主要的或唯一的经济来源,而女性则完全由丈夫或父亲供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青年妇女的最高理想就是“有一座漂亮的房子、有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4]
“家庭的主要贡献是使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男权制思想体系中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主要是通过他们父母的榜样和告诫)”。[8]为了让女儿莫莉具备男权社会所规定的家庭主妇的资格,卡丽为她安排了“淑女方案”(即,举止合宜、做饭、打扫屋子、缝制衣物),希望她能过上幸福生活,但莫莉却设法逃脱,正如热尔曼·格利尔(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中所说的那样,“家务活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一点事能衍生出很多事,没完没了。……只能打破这个循环,没有别的办法”。[9]莫莉接连拒绝接受本身角色的行为惹怒母亲,招致毒打。母亲对女儿的暴力行为说明,她已经完全接受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并且她要把这一观点传递给下一代,当她的努力失败时,她要通过某种方式维护父权制的权威。
家庭暴力也是男性绝对权威的体现。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实际上把自己归入了丈夫的财产清单,这意味着后者可以对前者任意处置。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我们之中很多人成长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家里的男性用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和控制,我们的问题常常由于妇女们也相信有权力的人用暴力来维持权利是正确的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家庭中的有些妇女对孩子使用强制性的权利,……这种暴力与男性对儿童和妇女的暴力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它可能没有那么普遍”[10]。卡丽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曾被丈夫施以暴行。无奈之下,她选择了离婚。而她,一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又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在卡丽看来,女儿的种种举动背离了社会准则,不符合公认的淑女标准,所以,她理应采用语言和肢体暴力惩罚她。这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激发了莫莉的反抗情绪,直至她离家去纽约。
家庭的建立是通过婚姻实现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也是维护父权制的法宝。从根本上来讲,这种婚姻制度只适用于女性,作为男性的统治者为自己设立了双重标准。恩格斯曾指出,在父权制社会,女人必须忠实于家庭,必须坚守贞操,否则将受到严惩,遭受世人唾骂,而男人却不会因为婚外性行为受到任何惩罚。当卡丽与第一任丈夫离婚时,后者和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卡丽离婚“比她丈夫的私奔要恶劣得多。那时你(女人)不能离婚”[6]。当卡丽再婚后,发现卡尔——她的第二任丈夫有外遇。那时她的很多亲友都早已获知此事,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卡尔也没有遭到人们的鄙夷,甚至人们还颇欣赏他的品味,认为他的情人“看起来很高,很优雅”。这是对父权制度的极大讽刺。男性要求女性忠实于婚姻,而他们自己却背叛婚姻、破坏家庭。为防止同样的惨剧发生在莫莉身上,布朗不仅让她远离婚姻,而且安排她加入了同性恋群体。这也正符合当时“激进女同性恋”所提出的主张——成为女同性恋,完全摆脱父权社会,因为“对于很多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脱离父权社会是最终的政治行为”[11]。莫莉无疑是该主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当她数年后与少时好友雷罗伊重逢时,他早已为人夫为人父。雷罗伊的枯燥单调的婚后生活似乎告诉莫莉,她的做法是正确的。
莫莉拒绝婚姻、拒绝建立家庭,她选择做一个完全独立的女人。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到在经济上独立,然而莫莉在就业过程中却屡遭性别歧视。在纽约大学读书时,为了支付学费,莫莉只得自谋出路。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女性主义者所坚持的“工作解放妇女”的观点。但结果并非如此,女性并未被工作解放。第一,大多数女性只被允许从事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例如,护士、教师、服务员、秘书等,这些工作的收入极低,女性不可能由此实现经济独立。而莫莉却要创造奇迹,打破就业领域的性别隔离,她选择攻读纽约大学的导演专业。虽然她曾开玩笑说“……我可能得改变性别才能找到工作”[6],但她不肯放弃。读书期间,她获得了奖学金,并且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然而,她能得到的也只是秘书、公关类的工作。与她同时毕业的一位成绩平平的男生却找到了一份导演助理的工作。事实上,这种状况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改善,纵观中外影视界,男导演的数量远远高于女导演。其实,“直到最近,几乎没有女性能够进入男性控制的职业领域,这些领域的工资是比较高的。1996年,女性中有26%是医生,14%是牙科医生,32%是律师,29%是法官,6%是工程师”[12]。第二,女性在工作中往往会遭受性骚扰。她们的女性身份和低收入往往意味着她们处于受异性支配的地位。莫莉和朋友霍莉在做服务生时,霍莉受到客人的性骚扰,她奋力反击。老板到场后却不问缘由把她辞退。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女性不仅得不到解放,反而更容易受到伤害。第三,即使女性进入被认为是男性控制的领域中,她们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莫莉攻读导演专业时,影棚的摄像机只预定给男生。为完成毕业设计,她只得不经允许私自带走摄影器械。男生所拍摄的多是当时流行的色情暴力片,而她却制作了一部关于卡丽悲惨一生的纪录片。在放映夜,男生的作品赢得阵阵掌声,而她的影片结束时,大家却都静静地离开了,甚至她的老师也一言未发。他们不愿向一位女性表现出欣赏之意,他们不想接受影片中所传达的女性受压迫的观点,因为他们一直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他们怎肯向被统治者低头。尽管挫折重重,莫莉仍坚持不懈。她坚信总有一天她会有机会拍摄电影的,即使她要为此奋斗到50岁,那时她“……将成为密西西比河以北最走红的徐娘”[6]。
四、结语
在这部半自传性的处女作中,布朗将自己所坚持的女性主义观点赋予主人公莫莉,二人共同完成了一次反抗父权制的艰难旅行。她们力图解构父权社会体系(否定家庭、拒绝婚姻、从事男性职业),建构一种容许两性独立、自由、平等的氛围。虽然她们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目标,但她们并不气馁。莫莉决意要继续奋斗直至成功。继《红果丛林》之后,截至2000年,布朗又相继出版了11部小说、2本诗集、1本散文集等等。虽然有人指出在布朗的作品中女性主义渐渐失色,但她一贯关注的女性主义问题仍然贯穿其中。
[参考文献]
[1] Zimmerman, Bonnie.“It Makes a Great Story”: Lesbian Culture and Lesbian Novel [A] .James P.Draper.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Yearbook 1992.Vol 76.[C] .Detroit, Washington, D.C.and London: Gale Research Inc., 1992.431-438.
[2] Rule, Jane.Four Decades of Fiction [A] .Sharon R.Gunton.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8.[C] .Detroit and 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94.72-73.
[3] Ryan, Bryan.(ed).Major 20th-Century Writers: A Selection of Sketches from Contemporary Authors.Vol 1.[M] .Detroit, New York and London: Gale Research Inc., 1991.418.
[4] 王政.女性的崛起: 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145, 48, 51.
[5] 孙宏.“石墙酒吧造反”前后同性恋文学在美国的演变[J] .外国文学研究,2006(2): 122-128.
[6] Brown, Rita Mae.Rubyfruit Jungle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23, 24, 31, 39, 88, 92, 238, 163, 246.
[7] 于冬云.女性主义批评[A] .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21-431.
[8]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 .宋文伟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43.
[9] Greer, Germaine.The Female Eunuch [M] .London: Granada Publishing Ltd., 1971.325.
[10]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M] .小征, 平林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138.
[11] Rupp, Leila J.Lesbian Feminism [A] .Cathy N.Davidson and Linda Wagner-Marti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men’s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92-494.
[12] 马里·里士满·阿沃特.女性的工资收入[A] .詹尼特·A·克莱尼.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C] .李燕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219-241.
——基于对国内某大型形式婚姻网站征婚广告的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