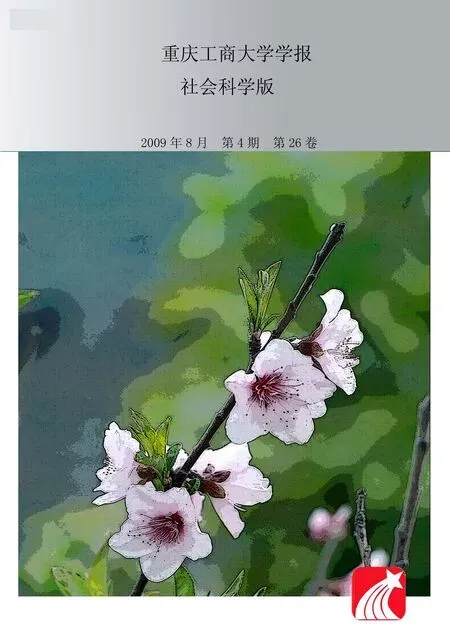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刘蕊杏
(安顺学院中文系,贵州 安顺 561000)
一、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之一:作家群体之比较
南北朝仙道诗的创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帝王、士人、道教徒。南朝仙道诗作家主要为帝王、士人,作家队伍比较庞大;而北朝仙道诗作家则主要是道教徒和一些由南朝入北朝的士人,作家队伍比较薄弱,北朝几乎没有自己的本土士人作家,其比较出色的作家如萧悫、颜之推、萧撝、王褒、庾信等人都是由南朝进入北朝。
南北朝仙道诗作家的这一不平衡现象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一)社会发展的必然
永嘉南渡后,东晋政权依赖南渡士族(侨姓)与江南大族(吴姓)的拥戴而建立,王、庾、谢、桓四大家族,几乎垄断统治的实权。然而刘宋建立以后,帝王及一些功臣大都出自寒门庶族,他们不能再忍受世族的歧视,因此,便从政治上给予世家大族以一定的打击与压抑。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自然会引起他们心态上的变化。他们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单纯地谈玄说道,沉溺于玄虚之中,而必然会更多地产生人生的感慨,这也就使得谈玄之风逐渐地淡化,并进而影响到诗歌的风貌。此时,南朝士人往往便用仙道诗来表现其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情趣,表现对现实社会的疏离和个体生命的超越。
此外,南朝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虽不一定影响文学的质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一定关系。而北方由于多年的战乱,经济崩溃、人民流散、田园荒废,大量士人前往南方。西晋以后,北方世族中的杰出者绝大部分南下投入东晋,留在北方的士人,虽然也是出身于世族,但已不是本族中的佼佼者,这是北方文学队伍组织状况的客观存在。文学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这正是北朝所缺少的。因此,道教在北朝的影响,更多的是纯宗教性质,是较纯粹的宗教信仰,其仙道诗的创作也多集中在道教徒手中。
(二)特殊人群对文学的引领作用
在南朝,文学集团非常多,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其原因是南朝帝王多喜欢文学,他们常招纳文士,进行文咏,因而形成不少的文人集团。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叔宝等,都在邸府招集文士,对形成吟咏之盛的文学创作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南朝仙道诗的创作者们也以帝王、士人为主。而在北朝,就非常缺乏足够力量和数量上的士人、诗人来带动北朝文学的发展。但是有几个人,对北朝文学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就是由南朝进入北朝的庾信、王褒等诗人,他们对融合南北文学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二、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之二:题材内容之比较
(一)南朝仙道诗多为抒情言志之作,诗歌更多描写神仙逍遥美妙的生活,表现作家个人的心志、理想和情趣,对现实社会的疏离和个体生命的超越
首先,“(南方道教徒)是以个人为本位,追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1],这是玄学家们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在道教中的反映,并且和嵇康《养生论》等说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江南的道教大都注重修炼长生,所以当时最被南人重视的是《黄庭经》,《黄庭经》又分《内景经》与《外景经》,都是教人修炼方法的。这种金丹、吐纳之术,大抵盛行于士大夫之间。总之,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以求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联系很少。因此,在南方,即使是帝王的仙道诗,也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中更多表现的是个人的某种心志、理想和情趣。如萧纲《升仙篇》:
“少室堪求道,明光可学仙。丹绘碧林宇,绿玉黄金篇。云车了无辙,风马讵须鞭。灵桃恒可饵,几回三千年。”
诗歌显然写于简文称帝之后,“明光可学仙”可说明这一点。贵为帝王的萧纲,无法像隐逸之士们在山林修炼成仙,于是他将宫中丹绘之处看作道观,将绿玉当作仙书道经,最后诗人选择了一条成仙的捷径——服饵,服食“灵桃”而升仙。总之,虽然萧纲是以帝王的角度来幻想在宫中成仙,但诗中所流露出的都是诗人个人强烈的神仙思想和成仙愿望,而没有带上丝毫的政治色彩。
其次,南朝的世家大族比之北朝,有渐衰渐散的趋势,门阀势力逐渐衰微。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实力渐渐衰退,这种际遇更刺激世家大族牢牢把持对文化的控制权,以显示自己门第的优越性。而世家大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清高孤傲的特质,使其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疏离和个体生命的超越情感。如王融《游仙诗》:
“命驾随所即,烛龙导轻镳。沙泽振寒草,弱水驾冰潮。远翔驰声响,流雪自飘遥。忽与若士遇,长举入云霄。罗绎徒有睨,蟭螟已寥寥。”
王融《游仙诗》前四句写诗人游仙路途,后面突遇若士,诗人跟随他竦入云霄,对大地上嘲笑他的网中之龟、蚊眉中的蟭螟不屑一顾。这里流露出诗人现实中的不得意,而力求在仙诗中摆脱这些烦恼,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打上了强烈渴望脱尘拔俗的情感烙印。这种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的解脱和超越的思想使得南朝道教徒更喜欢一个人在“静室”修炼,而不像北方道教盛行仙坛“靖场”,重集体修炼。戴暠《神仙篇》“阆山金静室,蓬丘银露坛”,就指明南朝道士修炼有“静室”。正如陆修静在改造南天师道(原五斗米道)时,所指出“大道虚寂,绝乎状貌”[2],道士祀神的主要场所“靖室”应该注重“清虚”,“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而已。”[2]
(二)北朝仙道诗多为记事析理之作,诗歌更多描写道教斋蘸仪式,斋戒诵经、劝戒世人要信奉道教,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
“(北方道教徒)是以‘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为‘积善’、‘立功’的手段,以求得上天的福佑而成仙。”[1]北方道教影响最大的寇谦之一派,就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寇谦之改革道教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3]。他曾对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3]于是,“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3]。太武帝所使用的“太平真君”年号也与此教派有很大关系。可见,寇谦之一派已经吸收了许多儒学成分。其实,寇谦之的这种思想,本来在道教中也曾存在,早在《太平经》中,就强调要成仙不死,先要为天地立功,作为人臣,应该辅助君王平天下,上天就会把成仙的妙方赐予其君主,使君臣一同“得俱仙去”[4]。因此,在北方,仙道诗更多的是描写道教斋蘸仪式,斋戒诵经、劝善度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道教的发展情况。如:
郑道昭《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嵿扫石置仙坛诗》:
“寻日爱丘素,嗟月开靖场。东峰青烟寺,西顶白云堂。朱阳台望远,玄灵崖色光。高坛周四岭,中明起前岗。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潇潇步林石,缭缭歌道章。空谷和鸣磬,风岫吐浮香。冷冷□虚唱,郁郁绕松梁。伊余莅东国,杖节牧齐疆。乘务惜暂暇,游此无事方。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长文听远义,门徒森山行。踌蹰念岁述,幽衿烛扶桑。栖盘时自我,岂云蹈行藏。”
与南方重个人在“静室”修炼不同,北方道教盛行仙坛“靖场”,重集体修炼。从此诗可看出,诗人月余就会带着一群门徒,在山上筑仙坛、开靖场。诗中大部分都在描写开靖场的情景,作者平实写来,对这一道教仪式作了形象的反映。
又如《老子化胡经玄歌三十七首 》更是与当时北周反佛的政治背景紧密结合,这些诗歌就是道教徒们用以宣传道教,攻击、诬蔑佛教的,在佛道斗争史中颇有史学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北齐萧悫、颜之推,北周萧撝、王褒、庾信等作家的仙道诗虽然也表现出作家个人的某种心志、理想和情趣,但这些作家都是从南朝进入北朝的,他们的诗歌创作自然难免会受到南朝以个人为本位思想的影响,这也表现出南北朝后期南北诗风的融合趋势。
三、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之三:艺术技巧之比较
(一)南朝仙道诗——排偶精工、声律严整、用典绵密
骈偶、声律、用典,是南朝文学普遍使用的手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朝仙道诗也尤其重视诗歌艺术形式技巧的追求。
沈约是南朝齐、梁文坛领袖。他与王融等在齐永明年间始创声律论,并在创作中自觉运用声律。他的仙道诗就典型表现出骈偶、声律等特色,如《前缓声歌》:
“羽人广宵宴,帐集瑶池东。开霞泛彩霭,澄雾迎香风。龙驾出黄苑,帝服起河宫。九疑轥烟雨,三山驭螭鸿。玉銮乃排月,瑶軷信凌空。神行烛玄漠,帝旆委曾虹。箫歌美嬴女,笙吹悦姬童。琼浆且未洽,羽辔已腾空。息凤曾城曲,灭景清都中。隆佑集皇代,委祚溢华嵩。”
这首诗虽然借用乐府旧题,但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全诗主要描写神仙的聚会,共20句,诗句对偶工整的居多数,中间16句更为突出。“彩霭”对“香风”、“黄苑”对“河宫”、“九疑”对“三山”、“玉銮”对“瑶軷”、“神行”对“帝旆”、“嬴女”对“姬童”等等,这样的遣词组句,全是精心安排的结果,绝非偶一为之。从平仄上看,该诗单句以仄声收尾,双句以平声收尾,音节和谐。在永明体之风气的影响下,更多诗人开始重视排偶、声律。
又如张正见《神仙篇》:
“瀛州分渤澥,阆苑隔虹霓。欲识三山路,须寻千仞溪。石梁云外去,蓬丘雾里迷。年深毁丹灶,学久弃青泥。葛水留还杖,天衢鸣去鸡。六龙骧首起云阁,万里一别何寥廓。玄都府内驾青牛,紫盖山人乘白鹤。浔阳杏花终难朽,武陵桃花未曾落。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同甘玉文枣,俱饮流霞药。鸾歌凤舞集天台,金阙银宫相向开。西王已令青鸟去,东梅还驭赤虬来。魏武还车逢汉女,荆王因梦识阳台。凤盖随云聊蔽日,霓裳杂雨复乘雷。神岳吹笙遥谢手,当知福地有神才。”
全诗虽五七言杂用,但同样也讲究对偶、平仄韵转换,铿锵悦耳。同时,诗中还运用了大量的神仙典故。“葛水留还杖,天衢鸣去鸡”,典出自葛洪《神仙传·壶公》、郭璞《玄中记》;“玄都府内驾青牛,紫盖山人乘白鹤”,典出自《枕中记》;“浔阳杏花终难朽, 武陵桃花未曾落”,典出自《神仙传·董奉》;“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典出自《神异经》;“同甘玉文枣,俱饮流霞药”,典出自《尹喜内传》等等。
总之,排偶、声律、用典,这些都逐渐成为南朝仙道诗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写法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二)北朝仙道诗——不讲排偶、不重声律、很少用典
北朝重气质、重实用的文风,修辞创作手段的落后等原因都造成了北朝仙道诗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技巧,不讲排偶、不重声律、很少用典。
如高允《王子乔》:
“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飞龙翔天庭。遗仪景,云汉酬,光骛电逝忽若浮。骑日月,从列星,跨腾入廓逾杳冥。寻元气,出天门,穷览有无穷道根。”
全诗长短句交错,虽然有一些对偶词语,但并没有形成排比对偶;诗歌基本是平声收句,没有讲究平仄韵律;诗中也没有用典,只是一气呵成地写出王子乔龙翔天庭的经历。
四、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之四:美学特质之比较
(一)南朝仙道诗——婉丽多彩之美、含蓄之美
首先,注意仙人形象的刻画。如周舍《上云乐》:“青眼贸贸,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对西方老胡首先进行了外貌上的详细描写,这一形象既有西域胡人的特色——青眼、高鼻,又充满仙家气质——白发垂地,长眉临须;“非直能俳,又善饮酒”,他爱俳优、善饮酒; “悉知廉节,皆识义方”,他知廉洁、识义方;“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他诸艺具佳,最擅长胡舞。通过一系列的描绘,使西方老胡这一形象生动、鲜活。又如王筠《东南射山诗》对仙人的描写,“还丹改容质,握髓驻流年”,先写仙人服丹改去凡人之质,能握髓不衰、青春永驻;“口含千里雾,掌流五色烟”,他还拥有非比寻常的法术;“琼浆泛金鼎,瑶池溉玉田”,他食的是琼浆玉液、瑶池美玉;“倏忽整龙驾,相遇凤台前”,他倏忽之间,就能飞升上天。这一仙人形象同样刻画得超凡脱尘、十分生动。
其次,南方自然环境绮丽秀美、鸟语花香,这也影响了南朝仙道诗重视环境的描写。如周弘让《春夜醮五岳图文诗》“夜静琼筵谧,月出杏坛明。香烟百和吐,灯色九微清”;沈约《和竟陵王游仙诗二首》(之一)“瑶台风不息,赤水正涟漪”;周子良《保命府丞授诗》“华景辉琼林,清风散紫霄”;张正见《神仙篇》“石梁云外立,蓬丘雾里迷”等等。或是将自然环境写得神仙气氛浓郁,或是直接写神仙世界的环境,都显得超凡脱俗。
再次,使用装饰感强烈的语言。正如阴铿《赋咏得神仙诗》“罗浮银是殿,瀛洲玉作堂”中所描述的,神仙居处都是用金银白玉所造那样绚丽。在南朝仙道诗中,“珠殿”、“紫阙” 、“玉銮”、 “金坛”、“金灶”、“彩霭”、“香风”、“香烟” 、“绛仙”、“绛云”、 “绿玉”等等装饰感强烈的词语屡见不鲜。
南朝仙道诗的含蓄之美主要表现在南朝仙道诗中有关道教典故的运用,构成其独特的审美内涵。诗人将大量道教典故嵌入仙道诗中,浓缩了极其神奇的故事,构造一个扑朔迷离的境界,增加了仙道诗的文化内涵。(关于此点,可参见前文“艺术技巧之比较”)
(二)北朝仙道诗——质朴自然之美、直露之美
北朝仙道诗的质朴自然之美主要表现为不重视形象的刻画,不重视环境的描写,不重视语言的装饰性。且看几首《老子化胡经玄歌》。
《化胡歌八首》(其一):
“我身西化时,登上华岳山。举目看昆仑,须弥了了悬。矫翼履清虚,倏忽到天西。但见西王母,严驾欲东旋。玉女数万千,姿容甚丽妍。天姿绝端严,齐执皇灵书。诵读仙圣经,养我同时姝。将我入天庭,皇老东向坐,身体曒然明。授我仙圣道,接度天下贤。”
《尹喜哀叹五首》(其一):
“尹喜告世人,欲求长生道。莫求时世荣。我昔得道时,身为关府君。一日三赏赐,杂彩以金银。不以为己有,施与贫穷人。白日沾王事,夜便习灵仙。餐松食苦柏,微命乃得存。精诚神明佑,守真仰苍天。感得天地道,遇见老君身。难我以父母,却遗五千文。秘室熟读之,三年易精神。授我仙圣方,都体解自然。”
这些诗歌既不重视形象的塑造,如诗中“老子”、“尹喜”具体形象如何,其高矮胖瘦美丑如何,其性格如何,其爱好如何,诗中都没有体现;也不重视环境的描写,他们所处的神仙世界具体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提及。诗歌还少有装饰性词语,语言没有精心的雕琢之迹,充满质朴自然之美。
此外,北朝仙道诗很少用典,诗歌就像说故事般,只求将事件过程说清楚,将道理说明白,其目的往往就是为了歌颂道教,表现出一种直露之美。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A]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33,233.
[2] 陆先生道门科略[M] .道藏第24册[C]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779, 780.
[3] (北齐)魏收.魏书(第8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051.
[4] 王明.太平经合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39.
——小林正美“新范式道教史”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