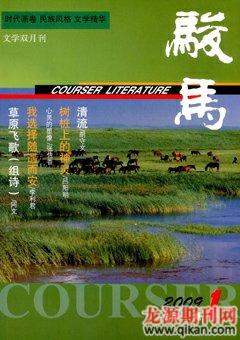树桩上的神灵
吕阳明
一
在一个村庄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的身份是特殊的。在这个种地吃粮的汉族人和放牧吃肉的蒙族人杂居的北方小村落里,苏日特实在是显得有些特别。
没有人还确切地记得苏日特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落的。他好像是在一个秋天清爽的早晨突然出现在我和小伙伴视野中的。那时我们几个被村人统称为“野孩子”的小家伙,正每人裤裆里夹着一根长长的松木杆大呼小叫地在村子里尘土飞扬的空场上疯跑,当时比较瘦弱的我滑了一跤,一头扎在了遍布牛粪和秸秆沫的土地上。那时的我在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总是处于被照顾的地位。我趴在地上感受着冲进鼻孔里的泥土干燥的气息,等待着伙伴们把我扶起来,却忽然感觉到四周一片出奇的寂静,似乎所有的声音掉进无边的旷野中失去了活力。我惊讶地爬起来,看见小伙伴们都站在阳光下望着一个方向呆若木鸡。我顺着伙伴们的目光望过去,一个陌生的老人站在不远处的草地上。在这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里,陌生人是最容易识别的,更不用说他那身奇异的装束了。他长得很高大,古铜色的脸上密布着纵横交错深深的皱纹。虽然看上去有些驼背,可还是掩饰不住一种强壮有力,一双眼睛鹰眼一般闪亮。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头上竟然长着两只角,像小人书上画的鹿一样。我和伙伴们面面相觑。那个人友好地看着我们,甚至向我们伸出一只干枯铁硬的大手。我们这群野孩子都恐惧地盯着他头上那对颤巍巍的犄角,戒备地向后退去。那人向我们走来了,短暂的犹疑之后我和伙伴们像一群炸了窝的小鸟一般扔下一地松木杆四散奔逃……
在一个人人都互相熟识甚至沾亲带故的小村落里,陌生人的出现是最能吸引人们好奇心的,那个忽然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人很快就成了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吸着呛人的旱烟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聊天。男人和唾沫四溅飞短流长的女人们,几天之内就流传了关于这个叫做苏日特老人的故事的好几个版本:
“听说这个怪老头儿是从大森林里来的!”虽然是听说,但说话人的脸上分明带着权威肯定的神色。
“大森林?有多大?”另一个人一脸茫然和好奇。
“那谁知道,反正比咱村北坟茔地旁边那片树林子大多了,里面有的是獐狍野鹿,有老虎也说不定……这老头儿就是猎人。”“权威人士”说。
“猎人?啊呀呀,阿弥陀佛,那是要杀生的啊!”一个胖得圆滚滚的女人一边用她宽阔的板牙撕扯着一块牛肉干,一边惊讶地喊着,语气情真意切悲天悯人。
“猎人?那些活兽跑得飞快,追不上不就要挨饿了?”一个人打着酒嗝,有些幸灾乐祸。
“嗤——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样笨得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我听说那些猎人吹上一阵口哨,野兽们就乖乖地跑来摇头摆尾地等着挨枪子!”
“呀!啧啧啧……”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和将信将疑的赞叹声。
太阳西斜,人群渐渐散去,散放的牛羊“哞哞——咩咩——”地叫着,悠闲地走在一条条回村的小路上,村庄里高低错落的小土房的烟囱里渐次涌起淡淡的炊烟。听完大人们闲聊,我拖着两条土黑的鼻涕回到我家的土房,正想将看到和听到的“重大新闻”讲给终日里愁眉苦脸的父母亲,却发现一脸怯懦的父亲正耷拉着两条泥腿,更加愁苦地坐在摇摇欲坠的木板炕沿上没命地抽着旱烟。而母亲一脸惶恐地搓着皲裂的手掌木然地站在地上。在炕沿的另一端,坐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老人,身后的炕席上放着一顶奇特的小皮帽,帽子上面赫然挺立着两只犄角。我吓了一跳,向后一退,险些被门槛绊倒。
那人坐在那里,和善地看着我。父亲大概对我的手足无措和冒失很恼火,瞪了我一眼说:“叫大姑父!”
我张了张嘴,没有叫出来。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称谓。我是在这之后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它的确切含义的。大姑夫——这个把我们吓得四散奔逃的陌生人是我父亲的第二任大姐夫。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大姑年轻时远嫁到了比我们这个北方小村庄更加靠北的异乡……
夜晚,家中忽然多了一个成员的新奇感让我睡不着觉,我在热乎乎的土炕上翻来覆去,听着纸棚顶上老鼠的跑动吵闹声,心里满是对那睡在西屋陌生亲属的好奇。让我惊讶的是,我的父母亲似乎也都在为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变化一夜无眠。
“家中的口粮自己都不够,哪有给他吃的……这日子怎么过……喝西北风啊……”母亲低低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
一阵沉默寂静。
“破坏公路是大罪吧,政府要不是照顾他,怕是要下大狱了……怎么给弄到这儿来了……还不如让他下大狱……”母亲在喋喋不休。
接着,还是让人喘不上气来的沉默寂静。
“在这儿要是再捅出什么娄子,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去蹲笆篱子,不如……”母亲继续喋喋不休。
“闭上你的臭嘴,没人要把你当哑巴卖喽!那年我得病要不是大姐给寄来的二十块钱和一棵人参,我早到阎王爷的生死簿上划勾打挑去了,你的良心让狗吃了?”黑暗中父亲的低声怒骂像一把落下的铡草刀,使母亲的嘀咕声戛然而止。父亲虽然在村人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但在母亲面前还是摆出一副男子汉的威严。
每当父亲发火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恼人的寂静中,我睡着了。
老猎人就这样在我家四处透风的西屋住下了。虽然西屋狭小的窗户下面有一个覆盖着尘土的小炕,但让我们惊异的是苏日特老人似乎不了解它的用途,夜晚来临,他就随便裹上一件破旧的大皮袄睡在冰冷的地上。
我对这位陌生的大姑夫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苏日特大姑夫时常一个人走向村外的田野和树林,当他归来的时候,总是能带回来几只麻雀,有一次甚至带回来一只野兔。多少年过去了,我还一直认为烤麻雀是这世间顶级的美味。在母亲生火做饭的时候,父亲就将麻雀用泥箍好,埋在灶下的火灰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烤好了,敲开外面的泥壳,一股诱人的肉香直冲鼻孔,烤熟的麻雀没有了羽毛显得比原来小了许多,香喷喷油亮亮地摆出好看的造型。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麻雀胸脯上的大块肉先吃进嘴里,然后掏出内脏,余下的部分我就可以慢慢品尝了,高兴的话我还可以分给一起玩耍的野孩子们几只。看着他们在我面前露出羡慕和讨好的神情,我得意极了。
烦恼是父母亲的,对于我来说,苏日特大姑夫的到来带给我很多快乐。
二
那一年冬季,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枯黄单调的旷野上只有比往年温暖一些的风在田野和树林间刮过。刚入冬,村里几户人家的羊接二连三地得了“转头疯”,没几天我家羊圈里的几只羊也开始前仆后继不知疲倦地原地转个不停,一直转到倒地死去。母亲心痛得将眼泪和鼻涕不断地抹在衣袖上,父亲铁青着脸将羊头扔掉,然后将死羊剥皮,按照当地的习惯将手把肉煮到了锅里。
在父母亲悲凄的神色里,我强忍着能吃到羊肉的喜悦,一天到晚吃得五饱六撑的。但这种暗喜没能持续几天,恐慌就笼罩了我们整个家庭。随着村里越来越多的羊旋转不已,恼怒的村民开始纷纷传说是苏日特这个突然出现的外乡人将灾祸带到了村子里。我弄不明白那些羊着了魔一般地转来转去与终日沉默寡言的苏日特大姑夫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村里平日带着我一起疯玩儿的野孩子们忽然之间都躲得我远远的。我耐不住寂寞跑去找他们玩儿,他们一个个对我怒目而视,我讨好地举着香喷喷的烤麻雀来笼络人心,可他们“呸、呸”地吐上几口唾沫就都跑了。
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一阵嘈杂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胡乱地穿好衣服跑到院子里,正看到一群乡人踹开紧扣的院门冲进来,为首的是一个粗壮的蒙族红脸汉子。父亲站在土房门口,看着冲进来的乡人吓得颤抖不止。
“你……你们有什么事?”父亲的声音都变了调。
“老嘎瘩,不关你的事,你知道,现在羊群里来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这样下去我们的羊都要死光了,我们不为难你,让那只狼滚出来……”红脸大汉喊着,同来的乡人们也都骂骂咧咧地随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