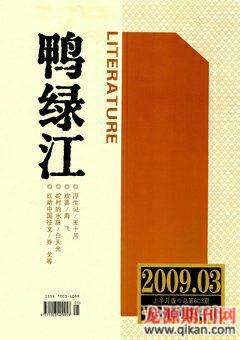谎言
曾 野
曾野,曾用笔名叶耳,湖南洞口人,2005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见于《青年文学》《中国作家》《大家》《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作品》《特区文学》《红豆》等刊物。有小说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等年选。曾获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金小说”全国中短篇小说优秀奖等。
还是来了。
在马小灰的煽风点火下,父亲他老人家说动了我。父亲说,既然复读了两年都没考上,再复读也不是个话。你看看人家马小灰。父亲用一种复杂的表情面向我,父亲的这种表情称得上百感交集,表明了这里面有太多的元素。父亲说,依我看,你还是跟马小灰去深圳吧。
父亲的话我是明白的,你看看人家马小灰。单这一句话,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内容,马小灰连初中都没念完,却在深圳做上了经理,好多漂亮女人围着他团团转。而我呢?我是一个只差两分就可以读上重点大学的高中生,心有不甘的我,复读了一年,未果。又复读了一年,还是名落孙山。本来还想复读的,听了父亲这一番话,我哪里还有勇气呢?父亲说得对,不管怎么样,去深圳看看再说吧。
到了深圳,马小灰就变了一个人。他修改了自己的口音,用的不再是客里山的话,而是叽哩呱啦的粤语。比如,碰到熟人,他就会说妮好,妮咳边度?碰到漂亮的女孩,他就会说,靓女,边度玩也。马小灰说,在这里,我熟人多得很呢!我想做经理的就是不一样。他还洋气地用粤语称呼我为靓仔。惠惠就笑了,弥漫着一种深南的悠长气息。惠惠是马小灰带回去的第几个女人,我已经记不得了。惠惠性感而白嫩,像白嫩的豆腐,一不小心就会裂开娇媚。惠惠一到东莞她的手机就响了,说有人急找她,打的走了。我就跟在马小灰后面屁颠屁颠地上了另外一辆的士。
马小灰对我说,惠惠这女人除了有股骚味我喜欢外,其他我都不喜欢。
他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马小灰抱着惠惠当着我的面打KISS的时候,还甜言蜜语地低吟:我的小妖精,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喜欢!
马小灰说,惠惠的乳房使我无数次想起客里山的豆腐。暖心入味。
我一直很难把马小灰的名字与和女人有着永无休止的缠绵连在一起。在客里山时,马小灰家和我家只隔开两扇窗的风景。马小灰从小不爱念书,倒是有着天性的早熟聪慧,有事没事就爱往村里那些长得乖态的姐姐家里窜。好几次我还发现这个流着鼻涕的小子居然趴在那些乖态的姐姐们的窗前鬼鬼祟祟。马小灰像墙上的狗尾草,一不留神就长高了,成熟的马小灰长得一点也不灰,高高大大。像匹马。
马小灰的出现没有给客里山带来多大的变化,他就像我们每天在村上看到的每一个人,不过是有着一张不同的面孔而已。
马小灰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话都是特别的。这是马小灰自己讲出来的。马小灰说,你们还别不信。马小灰说话总爱跑高调,像不小心碰到了一根琴弦,铮的响一声。马小灰无师自通学会了抽烟。马小灰喜欢抽烟,不是一支一支地抽,而是一包一包地抽。马小灰还爱喝点酒,喝的都是度数很高的酒。马小灰喝酒的时候总爱长叹一口气,然后笑一声,说,兄弟啊,真不错。要是与女人在一起喝酒,他准会说,这酒真美!马小灰艳福不浅,走到哪里都会有女人喜欢他,但马小灰看不出自己到底喜欢谁。在马小灰眼里,他被人喜欢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马小灰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想到这里,马小灰就会意味深长地露出笑来,轻轻巧巧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叨在嘴上,拧开打火机。一支烟,一种想法。马小灰的心里堆满了蜜的感觉。
那些德高望重的客里山人就看不惯马小灰这号人,说这号人能有啥出息呢?满嘴大话,一点也不诚实。好吃懒做,净爱做梦。可就是这么一个说大话、好吃懒做的人,却有一天一个人跑去了南方深圳,几年回来,穿得一身洋气还带回了个妩媚生姿的靓丽女人,说是他的女朋友。还花了十几万在家里盖了一栋新楼房。大家这才知道马小灰在深圳发财了。再细一打探,方知马小灰原来在深圳开了一个小公司哩!这对于客里山的人来说,无疑像一锅烧开的水,沸腾了整个小村。真应了客里山那句老话:懒人有懒福哩!
跟马小灰来了深圳,我才深知谎言是多么可怕。说谎的人根本不把说谎当一回事。
在女人那里,男人的话信不得真,都是七荤八素的瞎吹。用男人的词语总结,那就是扯蛋。女人看来,男人只不过是个贼而已。想要了,就在女人面前孩子一样软硬兼施,有灯没灯的,只要贴着呼吸就能把夜晚弄得虚张声势,流光溢彩。女人的身体就像男人的镜子,把一些可怜的想象照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蕾得梦公司对面的一家好运来餐馆里,我问马小灰,你的公司怎么净是漂亮女人?正说着,我突然间发现“蕾得梦”三个字后面还写着几行细小的字:推油九十八、按摩双钟六十八、桑拿一条龙四百八十八等。我正想问,马小灰仰起脖子咕噜猛喝了一口酒,很庄重地对我说,马小桥,实话对你讲,我开的不是什么公司,是一家有小姐服务的发廊。他的话说得坚实有力,有一股始料未及的匪气。
来广东之前,我就听在外面打工回去的人讲,广东的发廊不像家里的发廊,广东的发廊不是用来理发的,而是用来做“那个”的。所以当马小灰这么一讲,我的心里就起了鸡皮疙瘩。我看着马小灰,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马小灰却像没事似的说,小桥,只要你在我这儿好好干,我一个月给你两千块。我说我能干什么呀?帮我联系业务呀!我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马小灰就来火了,从嘴里甩出一句粗话,是粤语:我鸟你老母。这句话像他嘴里呕出来的一口污秽黏糊的浓痰,在我的脚下顿感可鄙。
原本以为马小灰开的是真正的公司,所以我才在父母的劝说下随马小灰南下打工。来到了这里,才明白马小灰瞎吹一通的公司原本就不曾存在过,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义愤填膺的孤独和无聊。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知道,我来的车费是马小灰给的,就算我不干了,回去的车费还是要靠马小灰出。如果惹恼了他,我连回也回不了。我不说话的时候,马小灰的脸色就温和了许多,吧嗒一声,马小灰点燃了一支烟,把另一支扔给了我。
马小灰说,干不干,住下来再说。我只得聋哑昏聩地点点头。
在没来南方打工时,马小灰正在家乡一个随便撒尿不怕女人看到的农村。马小灰在家里只有两件事可干:耕田和种地。他用一个未成熟男人的样子模仿农民的动作。每一次在水波荡漾的水田里耕田时,父亲就会粗着他上了年纪的声音对马小灰说,你现在要学会使用这个,因为你将来是一个农民。在客里山,那个堆放石头和绿色的小山村,除了耕田就是种地。女的种地,男的耕田。小孩放牛。马小灰十九岁了,却还什么都不会。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读书考试没有一次及过格,每次考试不及格,老师都会爬山越岭地走十几里山路来到马小灰的家。问他父亲,这孩子怎么了?还能怎么样?笨呗。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老师来马小灰家N次后就再也不来了。老师真觉得不好意思再来了。最后,马小灰没能读完初中就辍了学。辍学的原因也许你猜对了一个,但读书老不及格只是一个方面,家里穷才是马小灰无法继续读书的主要原因。不读更好,巴不得呢!对于马小灰来说,读书是一件磨时间的事情。大部分时间老师在台上讲,他就在台下打瞌睡。老师就会走到他的身边,拧着他的耳朵大声说,你这个猪,你这个猪哦。全班同学就会跟着哄堂大笑。可马小灰天性不怕羞,马小灰还拿眼睛直直地对视着老师的眼神。老师就把马小灰的耳朵放下来,摇了摇头,说一句让马小灰听来云里雾里的话:猪仔不可搞也(孺子不可教也)。这事传到了马小灰父亲那儿,被聪明的父亲也运用到了他的生活哲学里。每次考试不及格时,父亲就学老师的样,也把马小灰的耳朵拧起来,嘴里大声喊道:你这个猪,你这个猪哦。
不过马小灰有时候想想自己对于农村生活的无知,真觉得自己是个猪呢!马小灰跟母亲种了那么长时间的地,可他还是不知道种花生要种几粒,麦子要在什么时候种,油菜花是用来吃的还是用来榨油的呢。每次问起母亲,母亲既好气又好笑。有次跟母亲去地里拔花生,大家都是一撮撮地拔出来,而马小灰却是一根根地拔。母亲见了就叹着长长的气说,你这样下去,将来何得了哦?
父亲可不像母亲,每次看到马小灰耕田那个没出息的样就会粗着带酒味的声音向他砸去:
“你个娘卖X的,我压你娘啊。”
“你这个猪,这个猪哦。”
有时候,我们想那样,而生活却往往这样。
天空呈现了比想象还要遥远的绵延无期。在乡村的另一端,女人永远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似点点星光游弋在星空浩瀚的城市。男人奔走于这星罗棋布的气流之中,他们喜新悦目的足迹构成了另一条道路。道路伸向远方。夜晚就从这条道路里穿过来,像蛇咬噬着世界的寂寞,这寂寞却有着多种角度。
发廊的夜是醉人的夜,我睡在二楼的一间小屋里,能闻到女性身上散发出来的浓浓的味道,能很清晰地听到女性呻吟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听上去都很矫情,但我还是从这些或高或低的声音里感受到了我一生从未有过的激情。她们的声音破门而入,朝着我的床上、我的身上挤。它们在深邃的空间里引诱着我,插翅难逃的幸福沿着身体的想象力顺流而下。夜空通体发出跃跃欲试的光亮,每一颗光亮都很蜇人。这使我想起了马小灰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漂亮的女人一到了晚上全都是狐狸。
她们弄伤了我对于南方的第一个想象。
记得马小灰每次打南方回来总要到我家串门,前脚进门后脚就动粗言,动不动就当着我父亲的面说,操,小桥还读个尻子大学,把一个家读成这样。二十好几了,连个女人也没碰过。父亲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但他深知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好处。父亲叼着那根长长的旱烟杆粗着脖子反驳:将来就得有知识有文化,你晓得么?你懂么?
我呸。没钱有文化有个卵用。马小灰唾沫四溅。
你看看你们这个茅草石头搭的窝,哪像个家,还文化呢!
马小灰的这句话深深击中了我们的要害。眼下我们正缺钱交学费呢。每次看到家里的处境,我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自卑感。
马小灰那天在我家呆的时间很长,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和马小灰一块儿的还有他的女人惠惠。这是一个让人看一眼就会胡思乱想的女人,她说话爱噘着嘴,两个小酒窝里就旋转起一种风情,她爱笑,笑起来咯咯地响,眼睛就拉出一条温柔的线,把你的神牵住,把你的魂缠住。这个叫惠惠的女人有一股我从未见过的味儿。很妖。很狐。很美。
马小灰最爱喝我父亲烤的玉米酒,说我父亲的玉米酒特醇,喝了就想与女人干那事儿。我们知道马小灰是个油惯了嘴的人,嘴粗,习惯了都不在意。我偷偷瞟了一眼惠惠,她好像也早已习惯了这样,还笑了起来,响得厉害。马小灰的酒喝得多,话也多。马小灰说,小桥跟我去广东打工吧。去我的公司,包你有钱赚。父母亲都不吭声。只有我知道,他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咬着嘴唇,不说话。马小灰又喝了几杯后,打着饱嗝和惠惠左抱右拥地走了。走出家门口很远了,还回过头来喊了一句:小桥要去,他的车票我买。
醒来后的南方,阳光说不出来地刺眼。
马小灰问我睡得还好?我说还好。只是心里多了一层别样的滋味。我呆在马小灰的发廊像个无所事事的混混。除了看那些美丽的小手给男人洗头捶背外,我有时候还想一些平时没想过的问题,要是我跟她们其中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做那个,会是什么样呢?我为自己冷不丁蹦出这么奇怪的想法而感到好笑。我发现这里的女孩都很好看,她们嘴唇丰满,眼睛里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性感。她们的胸脯饱满而开阔,可以盛下所有男人想入非非的眼神。她们风情万种,她们舒缓流丽。她们像熟透了的水稻,在男人的河流里金光闪闪,感人至深。她们真美。这么一想,我的脸上就明显有了一抹绯红。我知道,我还是个羞涩的少年。
当我的眼光落在一个工号叫092的女孩脸上时,她的眼睛也正好与我对视,她的眼神有一种让我似曾相见的感觉。像小菊,又像眉儿。她们都是我曾经的女朋友。说是女朋友,还不如说是我一厢情愿的暗恋对象。
小菊念高二时去过我的家乡客里山,去的时候是冬天,小菊和我走了十几里山路才走到。小菊边走边埋怨,说这哪是人呆的地方啊。小菊只在我家住了一晚,就想走了。我怎么也留不住。后来小菊再也没有来过客里山。
眉儿也去过客里山,与小菊不同的是,眉儿觉得客里山是个山水青翠的地方,诗意且浪漫。尽管要翻山越岭走很长的山路,但眉儿却不觉得累不觉得苦。当我把眉儿带进我那座用石头垒成的家时,眉儿望着到处被柴火熏黑的墙壁和结满蜘蛛网的房间流泪了。眉儿说,真没想到啊,你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这样一句话,让我好长时间沉浸在忧伤的回忆里。
我想起了国外一位叫杜拉斯的女作家说的一句话:你越是拒绝,越是反对,就越是在生活。
092的目光只与我的目光轻轻一碰,就移开了。她的眼睛像窗外的天气,清澈干净。她不像其他女孩,一直盯着你看,有些胆大的,还会从嘴里蹦出一句,看什么看,想打主意呀!我看她时,她不敢看我,只给我一张红润的脸庞。她的害羞让我觉得纯真,于是有了喜欢她的感觉。心血来潮的冲动涌遍了我的全身,我听见它们涌动的声音在奔跑。我就又大着胆子拿眼看她,我真想知道,她为何要干这个?
晚上,我对马小灰说,我想单独见见092号这个女孩。马小灰很饱气地笑了笑:你小子也想呀!好,我成全你,不过我跟你说,她可还是个处女,刚从外地弄来的,你小子可要好心伺候哦!嘿嘿!嘿嘿!嘿嘿!一连三声的嘿嘿,让我有了一种更难以言说的情绪。马小灰把我想到哪儿去了?我又怎么会在这么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呆下去呢。
马小灰暧昧的笑让我连想多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了。
可我还是回到我居住的小房间里,在那里等待092的到来。
092来了,她穿着一套好看的花裙子。身上还散发着刚冲完凉的沐浴气味。她很害羞,时而看一下我就又立刻把眼睛移开。她并不漂亮的身材却很丰满。我望着她的眼睛,竟也有了几分羞怯。
我试着用语言与她交流。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我再问,她说名字是不能讲给客人听的,你叫我92号就行了。我又问,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不到半个月。那你以前干什么?读书。你为何要干这个呢?她不说话,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开始暗红。她时不时看墙上挂着的钟,突然说,我们开始吧。她就脱起衣服来,她脱衣服的动作熟悉而又陌生,当她白花花的奶子在与我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暴无遗时,我听见了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它们就像手枪里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我的气息以及细水长流的汗水如此寂寞。我像一颗等待燃烧的种子,真想就这样盛开了。
她开始脱最后一条内裤,我不知为何,却有了一种良心上的犯罪感。我大声呵斥:别脱了,把衣服全部穿上。她被我的声音震住了,瓷在那里。
她惊慌失措的样子,像一只受伤的鸟。把衣服穿上。我的语气明显温和了许多。她开始穿衣服,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一下子成熟起来了。她穿衣服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穿好了。我把床腾出一半,示意她坐,她坐了下来。我说,谁叫你脱衣服呢?老板说要我好好招待你的。我苦笑了笑,我叫马小桥,是马小灰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她过了好久才告诉我说她叫鱼想,广西人。我说,你是怎么来做这个的?她突然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让我感到了莫名其妙的难过。她的哭声有着泥土的温柔,绵软且厚润。
在鱼想的叙述中,我才知道鱼想和她的哥哥今年高考都考上了重点大学。但家里太穷,无法供他们上大学。她就自告奋勇地辍了学。尽管如此,哥哥的巨额学费还是无法拿出来,家里人到处借,可借遍了整个小村子也是相差甚远。她想到了在东莞打工的中学同学小蔓,就跑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上给小蔓打电话。小蔓听了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给她家汇来了八千元钱。她觉得小蔓真是她这一生的知己。小蔓叫她也来东莞打工,她就来了这里,当她知道是干这种事情时,她死活都不同意。但小蔓的话却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小蔓说,只要你在这里干一个月,我就不要你还那八千元钱。再说了,像你这样的人,要技术没技术,要经验没经验,你能干什么呀?你哥哥的学费又要等着你每年都寄,你到哪儿去挣呀?小蔓的话让她在人生的路上开始迷失了自己。她终于留了下来。
她留了下来,心里的理想却远去了。五彩缤纷的理想被南方炙热的阳光照射得疮痍满目。她感受到疼痛了吗?
我在鱼想的叙述里,找到了一种忧伤的共鸣。我告诉鱼想,如果不是因为只差两分,我现在也是一个大学生了。鱼想说,那你还可以再考呀!我说我都补考两次了,无奈之下才想到来这里打工,可不曾想……鱼想问我,你还准备回去复读吗?我说,现在还没决定,也许还会吧。鱼想就哦了一声,不再问了。我说鱼想别在这里打工好吗?换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鱼想望着我,好久都不说话,我突然觉得不说话的鱼想好美,像我暗恋的眉儿。我说鱼想我能吻你一下吗?鱼想就闭上了眼,鱼想的脸让我生动起来。
这个夜晚对于我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杂乱无章的心思在黑暗里面面相觑,黑暗很深,深不见底。她们被强大的灯光燃烧,没有人可以看到黑夜里的遥远。她们比一个人的命运还要遥远。她们像狐狸,却有着绵羊一样洁净的心。
我还是离开了马小灰的蕾得梦发廊。我要鱼想也走,鱼想执意不肯,我走的那天,看到鱼想的眼神哀怨而又忧伤。那一刻,我的心里竟像有了千万只蚂蚁在爬动。
马小灰很不高兴,说我这个人一点意思也没有。一个劲地说我。还动不动地来两句粤语,我鸟你老母操海。话很难听,但马小灰还是给了我三百元回家的路费。我没有选择回家,我选择了另外寻找工作。
那个下午的阳光很好,可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我提着行李离开了蕾得梦,离开了马小灰。
我开始了没有规律的生活。
我花二十元钱买了一辆废旧的单车。每天一早,便骑着单车漫无目的地找工作,在一些形形色色的招聘广告前停下脚步,可结果总是让我心灰意冷大失所望。我几乎找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还是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好不容易碰到一家五金厂招杂工,可匆匆赶到厂门前一站,啊,来应聘的人还真不少,有百来人,且手里都拿着形色各异的大中专文凭。难道杂工也讲究文凭吗?我莫名其妙地笑了一声,生气地走开了,我不知道是笑自己还是笑这些公司的领导。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晃荡在无人喝彩的城市。
“哐当”一声,我的单车在失去平衡时重重地撞在了深南路的电线杆上,我的头也肿了一块,我狠狠地从内心里吼了一句:我压你娘。“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心痛懊恼时刻,我奇迹般地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则招聘男女公关的广告。我虽然没有做过公关,但凭我这流利的普通话和一手漂亮的文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顾不上刚才的“糟糕”了,按照上面的要求欣喜若狂地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屏着呼吸喂了一声。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只短短的几分钟,我又大失所望了。这哪里是去做公关,用那小姐的话说是专门接待服务港澳台小姐的工作。说得不像话一点就是去做“男妓”。不知为何,我又想起了鱼想。她还好吗?一想起她要跟那么多不相干的男人在一起做那个,我的心里就有几十种痛。我想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我苦笑了笑。那天,我是推着单车回到出租屋的,我已经没有力气骑车了。
我决定回家。
临走的时候,我想去见见鱼想。我真想叫她回家,尽管我知道我的规劝肯定是苍白无力的。到了蕾得梦发廊,看到门口站着的花枝招展的姑娘们,看着那么多令人反胃的绅士的脸,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见鱼想。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