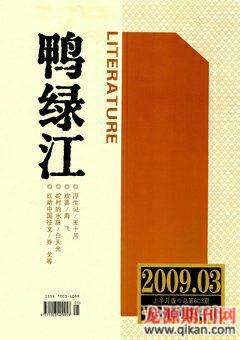杀猪
付久江,1975年生于内蒙古敖汉旗,现供职于辽宁省朝阳市第三地质大队。2007年毕业于辽宁文学院第五届新锐作家班,曾有小说发表于《芒种》《北方文学》等报刊杂志。
棉絮样的雪下了半天又一夜,清晨,天放晴了。这时,懒惰的太阳还没爬上村东的橡树山,给人的感觉天是被这满世界的白雪给照亮的。我■着没膝盖的积雪往村西走,途中我好几次停下脚步,用棉袄袖蹭着嘴唇上的清鼻涕,打量着眼前的村庄。房屋像是从雪地里突然冒出来的大蘑菇,一堆一堆的,顶着厚厚的白帽子。世界仿佛浑然天成。
我去村西二奶奶家拿杀猪的侵条刀,那刀一尺二寸长,韭菜叶厚的刀背,弓背形的刀刃,顺着猪脖子捅进去,割断咽喉的同时,一下子就能捅到猪心上。刀是老辈子就有的,不属于谁家,而是属于整个烧锅店村。属于整个烧锅店的还有一杆大秤,扁担长的秤杆足有茶杯那么粗,能称三百斤重的东西。大秤在村东五常爷家里,清晨起来,父亲吩咐我去拿刀时,他就去五常爷家取大秤了。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杀猪是势在必行了。我家的小花妞已是在劫难逃了。
昨天傍晚,母亲冒着雪,往猪食槽里只倒了些温好的清泔水,撒上一把苞谷面,引诱着小花妞喝了个水饱。半夜雪下得正大时,睡梦中我听见小花妞吱吱呀呀的嚎叫,嘴巴子把猪圈门拱得咣咣响。它肚子里早就没食了,那盆清泔水想必早就变成两泡尿水,冻成硬硬的冰坨了。朦胧中我听见母亲叹了口气说,还拱啥呀拱?不是不给你吃,给你吃了也白搭呀。我就突然警醒了,杀猪前的猪是不喂的,喂了也只能变成粪便拉出去,只给它喝些泔水,清清肠子。黑暗中我咬着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小花妞呀我的小花妞,看来你真是活不过明天了。
我恨父亲,更恨那个骗他的人。
秋末,父亲赊了村里人的葵花籽,满满装了一大汽车,贩到远处,又贩回一大汽车苹果。我们这里水果奇缺。走时的父亲是踌躇满志的,回来时打开车的苫布,父亲呆住了,只有外面几筐是装车时看见的红彤彤的苹果,再往里,全是烂得淌水的冻苹果。苹果是在父亲与人家喝酒时被调了包,几千块钱就这样打水漂了。为了堵住父亲捅出来的这个大窟窿,母亲忍痛卖掉了肥猪大老黑,抵了那些催得紧的外债。
这回可好,过年杀猪,只有拿我的小花妞开刀了。如果有大老黑在该多好,那家伙二百多斤重,整天懒洋洋地趴在圈里蹲膘,一副绝对该杀的架势。
小花妞是我和母亲春天时去赶集,在集市上买回来的。七八个猪羔子里,我一眼就相中了小花妞,小花妞不像别的猪羔子那样吱哇乱叫,稀屎尿水撒得满地都是,它四蹄紧绑着躺在地上,既不拉也不尿,微眯着双眼,一副顺其自然安于天命的姿态。
我对母亲说,妈,咱们就要它。母亲看了看小花妞黑白相间的皮毛说,这样的猪杀出来的皮色不好。我说妈,杀猪又不是看的,是吃的,你看它多干净,多听话,不淘,不会拱圈门子。也许是我的话说动了母亲,也许母亲本来就相中了小花妞,只是想压压卖猪人的价,最终母亲买回了小花妞。
小花妞刚到我们家时,被以主人自居的大老黑欺负得够呛。大老黑吃饱了撑的,没事就咬它,还把小花妞从絮好柴草的窝里往外拱。我就拿着长长的竹竿站在圈门外扎大老黑。大老黑开始还不明白,还委屈,渐渐地它好像明白自己失宠了,容忍下了小花妞。
小花妞是知道我于它有知遇之恩的,每次见到我放学回来,都会扭着它的花屁股,跟在我后面,哼哼哼、哼哼哼地叫,好像说,快快快,快去给我割猪草。放下书包,我拿起镰刀上山割猪草,割回来的猪草洒在猪圈里,我要小花妞先吃个够。我拿着和猪食的木板守在一旁,大老黑一抢我就打它的天灵盖。母亲就喊,傻孩子哎,让大老黑吃,年根底下我们还要杀它呢。
谁能想到呢,父亲做买卖遭了骗,大老黑被卖了抵债,挨刀的轮到了小花妞。
二奶奶家的大黄狗见了我,吼着往上扑,被我一脚踹了个翻盘儿,粘了一身雪末子,哀叫着往回跑。顺子叔拿着几个双响,叼着烟走出来,说,是东子啊,又谁惹你了,拿我们家大黄出气。我说你家大黄狗眼看人低,该打!
顺子叔白了我一眼,没理我这茬儿,伸舌头舔了舔双响屁股,把它立在墙头的石头上,冻住了,点燃,嗵——咣!一股药香在寒风中瞬息飘散,纸屑天女散花般飘落,花花绿绿地撒在洁白的雪地上。
二奶奶家满屋杀猪菜的味道。我凑到炕沿的火盆边,烤僵冷的双手。大孙子,吃块猪肉,肥肥的,满嘴油。二奶奶双手撑着炕挪坐到火盆前,皱鸡皮样的手一指桌子。顺子婶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筷,听了二奶奶的话,手里的菜盆就迟疑了一下。
我低下头,嗓眼儿里咕噜了一口涎水,摇摇头说,不吃了,今天我家也杀猪。
这一刻我心里对父亲的怨恨突然少了许多,父亲说的没错,不杀猪,这年就没个年滋味。唉,要是大老黑不卖该多好。
你家的猪不是卖了吗?二奶奶已经点着了她的大烟袋,吧地抽一口烟。
我说,杀小花妞。
二奶奶嘿喽一声咳嗽,把一口浓痰吐在火盆里,用灰埋了,说,一个猪克郎,能出几斤肉,杀了可惜了。叫你爸爸过来割些肉回去过年得了。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不就那么几天吗。
顺子叔进屋了,看了二奶奶一眼,说,日子各有各的过法,妈你别跟着掺和。
我看看顺子叔油汪汪的嘴巴子说,二奶奶你不知道,我家的小花妞别看小,可是它胖着呢,屁股都圆了。说这话时,我心里酸酸的。
拿上侵条刀,我想起父亲的叮嘱,回头对二奶奶说,二奶奶,晌午到我们家去吃猪血。二奶奶绽出一脸核桃纹儿,说,呦,瞧我这大孙子,心里有奶奶呢。去,一准儿去。我回头又对顺子叔说,叔,带上婶子抱上小妹,你们一家都去。
走出大门,大黄从后面撵出来,在我背后又嚎叫,我回头晃了晃手里的侵条刀,大黄转身就跑,仿佛中了刀。哼,打狗看主人,我就是要那抠门儿的刘顺看看!
二奶奶家是前天杀的猪,杀猪前顺子叔到我家来,对父亲说,五哥五嫂,明个儿带上孩子到我家吃猪血。顺子叔说话时眼睛瞅着地,好像钱掉在我家地上了。父亲说一定去,到时不用你来叫。顺子叔走后,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去!不吃又死不了!听说我们家把猪卖了,你听他让客(qiě)的口气,全是虚的。父亲说这是啥话,让到是礼,去不去在你,不能恁想。
他家杀猪那天,顺子叔也没过来再叫,父亲踌躇一番还是去了。他是代表我们一家去的。回来时父亲突然决定杀猪。父亲喝了点酒,他打着饱嗝说,杀!不杀猪,这年就没个年滋味。
母亲说要杀也得等到年根底下,好赖还能再长几斤肉。
母亲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烧锅店,我们姓刘的虽不是大户,但是枝枝杈杈算起来也有几十口,每年腊月谁家杀猪,都要挨家挨户叫去吃猪血,其实就是吃猪肉。吃完这家吃那家,算起来其实是大拇哥卷煎饼,自个儿吃自个儿,就是老辈子留下来的习俗改不了。虽是这样,这猪的先杀后杀对于精打细算的人家来说可是大有学问:庄户人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肚肠里那点油水早就被粗粮土菜刮拉个精光,头几顿猪肉不吃饱是不会撂筷儿的。再往后吃,吃到腊月门儿,人的肠胃已经满足了,吃也就是个形式,一大家子老少爷们坐在一起,无非就是关上门喝点酒,唠些家长里短、山上地下的闲事。要是在往年,对于杀猪的早晚,吃喝的多少,母亲是不会在乎的,今年不同,父亲做买卖不但没挣钱,而且还赔上了老本,欠了上千元的外债。过了这些年日子,母亲还没有尝到过拉饥荒的滋味,所以心里就装不下,一到夜里就睡不着觉。
父亲说,不差那几天,咱先杀,记住,要想自己心里不难过,就别让人家做事时难做。父亲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挺细的,顺子叔让客的态度让他心里难受。
侵条刀揣在怀里,弓背形的刀刃贴在我的前胸是一条冰凉。想着它从小花妞的脖子捅进去的情景,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已经被侵条刀穿了个洞,飕飕冒着冷风。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我在道上磨蹭着,心想晚回去一会儿,我的小花妞就能多活一会儿。
进了家门,院里的积雪已经除尽,案板早已经摆在院中央,是一扇老辈子留下来的旧门板。母亲在屋里烧水,腾腾的热气从气窗里冒出来翻上屋顶,想去追屋顶的炊烟,却和炊烟一起被风扯了个无影无形。
杀猪匠是大伯家的金锁哥,他穿着油腻腻的破棉袄,见了我说,怎么才回来,打刀子去了吧。
我把刀子扔在案板上,瞪了他一眼说,我就是打刀子去了咋的?要你管?臭金锁,死屠夫!
金锁扑哧一声笑了,说,你个小豆包,还知道屠夫?我要真是屠夫就好了,天天吃猪肉啃猪蹄。
陆陆续续有人进了院子,全是我们老刘家的男人们,他们个个揣着袖,向我家的猪圈张望。我家杀猪的消息已经像猪肉的香味一样,钻进他们的鼻子里。这帮馋鬼!
小花妞不像别人家的瘦克郎,它真的很胖,在圈里没跑上两圈,就让金锁给钳住了后腿,一把摁倒了。另一个叫金良的帮手马上跳进去,帮忙按住,金锁腾出手,手里的绳子连绾几个猪蹄扣,把小花妞的前后蹄绑死,一根扁担顺着小花妞的前后蹄一穿,小花妞就被抬了出来,咣当一声摔在案板上。小花妞仿佛知道大限已到,一改往日的安然优雅,拼命地嚎叫起来。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跑回屋里趴在炕上,双手捂着耳朵,眼泪把脸下的炕席洇湿了一大片。我知道小花妞作为一头猪,是早晚要挨那一刀的,但是我没想到它会死得这样早,还没活到一年,在猪里算是“短寿”了。
再次走出屋门时,我看见的是小花妞横陈在案板上软绵绵的尸体,还有少许的鲜血顺着它脖颈上的伤口滴滴嗒嗒往下淌,落在案板上很快就凝固了。金锁已经在小花妞的左后腿上开了一个小口,用一根胳膊那么长,筷子那么粗的铁条捅进去,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然后扒开小口,鼓起腮帮子往里面吹气,旁边一个人拿着木板不停地拍打着小花妞的身体、肚皮、前胸、后背,脖颈。小花妞的身体就渐渐地鼓起来,像一个奇形怪状的大皮球,头尾和四肢看上去小得可怜。金锁往小花妞的身体里鼓足了气,用根细绳把口子绑住,吆喝众人抬小花妞进了屋,架在热气腾腾的大锅上。大锅里的水,已经被母亲烧得翻花开。随着开水一瓢一瓢浇在小花妞的身上,金锁手里的砖头在浇过的地方嚓嚓嚓,嚓嚓嚓,一通蹭,这时的小花妞就不是小花妞了,黑白相间的猪毛纷纷脱落,眨眼间变成了大白条儿。小花妞又被抬到屋外的案板上,金锁手中又换了一把刀,一把沉甸甸的砍刀,砍下头蹄开膛破肚,掏出下水。这时的猪已经不是猪了,头与身,骨与肉,分离得清清楚楚……金锁脱下外衣,撸起袖子,■猪肠,翻猪肚,院子里开始弥散一股难闻的腥臭气味。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扶着墙哇哇地吐起来。母亲甩着湿漉漉的手跑过来,摸摸我的额头说,东子,是不是要感冒,快进屋。我含着眼泪说,妈我没事,就是恶心。母亲对着猪圈的方向看了看,眼睛突然湿润了,拭了拭我眼角的泪说,东子,过完年再跟妈去集上抓猪,到时咱一定把它养大。
整个杀猪的过程,父亲没有插一下手。只有在给小花妞过秤时,他凑过去看了一下秤杆上的星儿。抬猪的问,多少?父亲张着大嘴笑着说,毛重一百零五斤,哈,不少,不少啦。紧接着他出了院子,开始从村东到村西,挨家挨户叫客。望着父亲的背影,金锁对打下手的金良说,瞧这架势,晌午这顿饭,不得半口猪呀。金良说,三叔这人呀,忒好脸儿,不杀猪也没人挑他。
外屋母亲身旁有了帮手,是村东我的两个婶子,妯娌几个,灌血肠,炖猪肉,捞干饭,不时发出叽叽咯咯的笑声,把个冬日折腾得热闹。母亲脸上,又绽现出久违的笑容。
我躺在炕上,望着屋顶被日子熏黄的纸棚,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吃小花妞的肉,就是馋死了我也不吃。让那些馋鬼吃去吧,他们都得馋痨了。不吃小花妞的肉,他们都活不下去了。
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了。顺子叔也来了,坐在我们家炕上跟人卷纸烟,哧溜哧溜地喝茶水。顺子婶也抱着孩子来了,她把煮好的猪大肠掐了一块,往孩子的嘴里塞。
我扭脸跳到地下,穿过闹哄哄的堂屋去了西屋。西屋小炕上放着一张八仙桌,二奶奶和大奶奶已经被父亲请到了,两个老太太一人一杆大烟袋,把个小屋弄得乌烟瘴气。我磨转身又回到东屋,蜷缩在炕梢的角落里,翻出书包里的连环画,胡乱地翻起来,正翻到“金兀术慌忙躲闪,岳云的锤在他的肚皮上蹭了一下……”金生和小园溜到我身边。金生说,还看那本破《牛头山》呢啊,我那《长坂坡》特有意思,晚上你过去拿。我翻了金生一眼说,你不是不借吗?小园说,金生过去是想等你爸挣到钱,把画册卖给你,谁知你爸赔钱了。金生挥手在小园的后脑勺上扇了一巴掌说,我啥时说要卖给东子了,闭上你的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金生凑近我的耳边说,东子,你爸真的被人骗了吗?是不是假装的,要不你家咋还杀猪呢?
你爸才被骗了呢!我气呼呼地合上画册说,我爸赚钱了,而且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还说,要买全套的《岳飞传》给我呢。
小园说东子你别撒谎了,那天你爸去我家,亲口说的,还说欠我家的钱暂时还不上了。我爸说没事,吃一劝(堑)长一智,以后在外面凡事多长个心眼儿。
我说,扯淡!没有人能骗得了我爸,我爸心眼儿多着呢。
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已经端上桌子,五花肉炖干白菜,瘦肉酸菜炖粉条,猪血肠,酱焖猪肉……来吃猪肉的人陆陆续续进来,挤满了屋子,按部就班地坐下。连二炕上摆了三张八仙桌,坐着女人和孩子,地下放了两张折叠式圆桌,坐的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说,金生小园,你们去吃猪肉吧,可劲儿吃。告诉你们吧,我爸根本没赔钱。
金生说,东子你不吃吗?
我说,你们是客,你们先吃。
你看这孩子,都是自己家人,哪来的客,来,过来挨着四婶坐。四婶抬手招呼我。
我摇摇头说,你们先吃,我不饿。我心里说要不是外面太冷,我早就出去了,懒得看你们那副吃相。
成桶的散白酒拎上来,男人们一人抄一个小碗,鼓咚咚倒满。女的呢,有好喝酒的也掐碗倒点儿,说暖暖身子。
也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在人类所有的表情和动作中,吃相是最丑的,五官挪位,表情贪婪,伴随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声音。
即便心存厌恶,迷人的肉香还是顺着我的鼻孔钻进肚子,像一只温柔的小手,抓挠得我的胃不停地抽搐。我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没出息,今天就不让你吃猪肉,看看馋死馋不死。可是舌下已经积满了涎水,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小花妞了。
母亲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她不停地添菜,手里的盘子上桌来时是满的,下桌去时是空的。父亲则端着个酒碗,挨桌挨个地敬酒。自打做生意被骗以后,父亲好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过。
六叔,我敬您老一个。父亲端着酒碗来到六爷爷跟前。
六爷爷端起酒叹着气说,小斌呀,听六叔一句话,赔就赔了吧,别上火,古语说得好:吃亏是福。那买卖,能做就做,不能做咱下庄稼地,这年头不像旧社会,饿不死人。
六叔你说哪去了,我这是花钱买经验,没啥。六叔我干啦。父亲一仰脖干了碗里的酒。
三哥,兄弟我……父亲又倒了一碗,来到三伯跟前。
小斌!三伯举起酒碗厉声说,你要再提钱看我不扇你!哥今年的收成全村最好,不缺钱花。没事,放心大胆地去干,缺东少西吱声,哥就服你那股子闯劲儿,你嫂子心眼小,别跟她一般见识……
小斌你不要干了……
别让小斌喝了……
那个中午,我蜷缩在角落里,看着父亲穿梭在桌子之间频频地敬酒,脚步踉跄着,像一只飞舞的蝴蝶。
氤氲的酒香肉香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梦见自己躺在盛夏的草场上,身边卧着我的小花妞,它还是那样优雅安详。蓝天上白云悠悠,身下的整个大地仿佛在徐徐飘游……
醒来时太阳已经西斜,屋里空荡荡的,堂屋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是母亲就着锅里的热水在洗涮油乎乎的碗筷。父亲横躺在炕上,摊成个“大”字,呼噜打得像闷雷。母亲见我醒了,就招呼我吃饭。我摇了摇头,我的胃已经停止了反抗,静静地,一丝食欲也没有。
母亲说,你爸吐了,你去院里收拾一下。
我拿着火铲出了屋门,心想爸真不会过日子,肉吃到肚子里又吐出来,可惜了。
父亲送走客人后吐在了墙根下的雪堆上,寒风中吐出的东西已经冻成硬硬的一坨。我用火铲收拾起来。在那堆污秽里,我没有发现一块肉。桌席间父亲光敬酒劝酒了,小花妞的肉,他一口都没动。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