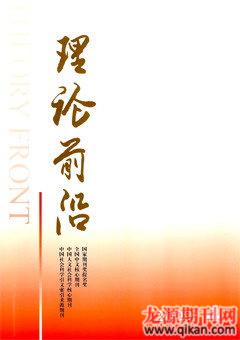法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对策
汪习根 郭孝实
[摘要]践行法治理念,推进中国法治方略,应处理好程序理性与程序人性、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社会公平与法律效率、秩序稳定与和谐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法治;理念;全球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4-0015-02
法治理念是每一个人以及由此连接成的集合体对法治的理解、解释、观点与信念,是关于法治及其价值的“知”、“观”、“信”三者的有机统一体。在当代中国,法治理念作为一个根本性、前导性的问题,对现实法治发展至关重要。而当前存在着不少困扰法治实践的理念困惑与迷失,使法治方略的推进充满挑战与矛盾。因此,对法治实践之路如何选择和选择怎样的法治战略模式,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在选择法治理念的实践路径时,应当集中解决以下四大问题:
(一)程序理性与程序人性
程序理性关注程序的要素细化与逻辑关联。强调严守程序的每一个步骤与环节而不得有任何的简化与省略,更不得超越程序的界限执行法律。程序理性视程序为正义的生命线,但程序理性如果被极端化,就会陷入程序形式主义与机械主义的泥潭,而以程序的过于形式化损害实质正义。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将程序的人性化理念引入程序理性之中,实现理性程序与人性程序、程序的形式化与程序的人性化的统一,是更新程序法治理念的必由之路。所谓人性程序即程序的人性化,是指将人性化思维与情感注入到程序系统之中。使被高度格式化、去人性化的司法步骤与程序设计浸润进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情民风的体恤、对社会弱者的关爱。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弹性化。即在标准程序外辅之以非标准程序,省去不必要的程序环节,只保留程序的核心或者在程序要素的组合方式上予以简省与重构。二是伦理化。程序是排除情感左右进行独立判断的武器,但程序与人伦情理绝非水火不容,因为法则源自法理,而法理出自情理,情、理、法从来就是基本同一的。司法者对程序的参与者应当施以必要的人性关怀,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在与理性程序高度融合后应当凝聚成人本程序理念。三是便民化。程序往往耗时费日,正是在成本高昂的背后才能体现程序正义,因此,程序的执行者更有必要保证司法过程对参与者的方便、便利与便捷。当然,人性程序并不能取代程序的形式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二)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
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究竟孰轻孰重?对此,有人认为法治是个体正义的实现方式,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人权,正义最终必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所以,个体之间的正义是法治的根本。有人认为法治的终极价值只能是社会正义,没有结构性、整体性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个体正义便不复存在。
其实,法治既应实现个体正义,也决不能无视或轻视社会正义。个体正义是法治的立足点。而社会正义是个体正义的基本前提,在个体正义的实现过程中追求社会正义,在社会正义的框架下实现个体正义,达到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才是法治正义的一条根本出路。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关系的二元化和非对称、非平等性,即法律主体的二元化(城乡二元对立)、权利空间的二元化(区域发展不协调)、主体客体的二元化(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仅法治生活中的立法过程应通过构建良法予以解决。而且执法司法也应在消除了这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后才能实现个体正义。
(三)社会公平与法律效率
效率优位于正义的价值排序,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模式,曾引起法律领域的迷惘。其实,法律永远是正义的化身,而不可能成为效率的表征,尽管效率的法律价值渐受重视。社会公平是法治视野下正义与效率关系安排的基本底线,法律效率只能是社会公平之上的效率。为此,要树立以下两个观点:一是实质上的公平效率观。从法治的外在价值目标看,在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公平为重,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去盲目追求经济效率。因为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量,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发展,甚至可能会损害公平、平等地分享机会与获取资源。法律正是以公平的身份介入经济增长以抹去其非公平性的,此时,法律所肩负的使命不是效率而是社会主体公正地配置资源与正义地享受发展成果。二是形式上的公平效率观。从法的内在价值理念看,法律制度尤其是法律程序应当是富有效率的,能够以最低的时间成本、最少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支出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排解纠纷,实现正当利益。否则,一味强调正义的绝对性、永恒性而无视法律成本与后果的比较,必然会妨碍正义的及时实现,此所谓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正义是需要耗时费日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耗费一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成本便难以造就正义,相反可能会因草率马虎、仓促办案而戕害正义、造成冤狱。所以,无论是从法律所追求的外部社会价值还是就法律规范内在的实体与程序设计上讲。法治始终应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效率永远只是在满足了社会公平的价值需求条件下的一种价值理想。
(四)秩序稳定与和谐法治
秩序是法治的一个初始价值,没有无秩序的法治。社会稳定正是法治之秩序观的必然体现。那么,稳定是否是永恒的压倒性至上价值呢?从系统论上讲,法治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法治离不开其他外部系统的支撑,在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中要建构法治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一意义上看,稳定的秩序是前提性、基础性的法治价值需求。然而,从发生学的意义分析,法治的起点并不是秩序,相反它源自于对人治秩序的摧毁,并以人权为立足点,通过机制运行以实现人权为最终归宿。而人权的终极追求依存于正义的法律制度,所以,离开了社会正义与人权保障而谈秩序对法治是毫无意义的。正因此。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并不是同义、等值的。法治和谐包含了秩序稳定,但又远远高于秩序稳定,真正理性的和谐决非“和稀泥”式地强调秩序稳定,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这就是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次序中,以权利为目的而非相反:在权利与权利的层次序列中,重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以个体利益取代甚至否定整体利益;在权力与权利的连带互动中,通过相互监督与约束而又互相辅助与配合之机制,以实现社会公正。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利及权力内部的上述诸多和谐模式共同构成和谐法治体系。因此,倡导法治理念,必须厘清稳定与和谐之关系,防止以秩序稳定取代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于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