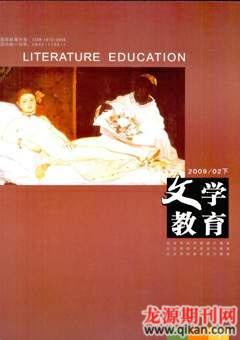耶里内克初期创作的伦理启示
20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艾尔弗雷德·耶里内克,被文坛誉为“女性法西斯主义”,其基本思想的形成在她创作之初的三部小说《我们是诱鸟,宝贝》、《逐爱的女人》和《米夏埃尔》中已大体具备雏形,对性、暴力、虐恋等欲望主题及其裸语直陈的表现形式都有所尝试,后来经《钢琴教师》、《情欲》等作品将这些方面的表现渐趋专注、成熟并推向极端。就现有研究资料对耶利内克的倾向性态度来看,其创作显然属于学术正统少有染指的“性文学”(指着力于对性欲、性爱、性行为和性心理进行艺术审美并深度表现的文学作品)范畴。
当我们面对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无性不成书”已成为作家取悦读者的重要手段,并构筑了一道诱人的文学风情园,先前跟着西方学舌的国内文学终于追上了时代的步伐,与同时期的西方性文学相映生辉。在80年代劳伦斯、杜拉斯、昆德拉、纳博科夫等“涉性文学热”之余,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在不断的诋毁与赞誉中后来居上。她的小说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至上的社会,抓住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她的初期作品体现的权欲、情欲、占有欲、强奸欲、破坏欲等,冲破了传统伦理所能接纳的文学禁区,并以此开启了她文学创作道路的与众不同。更让文坛和读者倍感意外的是瑞典文学院对她作品的认同,除争议与质疑之外,又何尝不意味深长?本文仅借助于耶里内克初期创作的几部作品,探视那些剥离了“爱”的“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商业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需求的同时也放纵着欲望,使固有的道德与禁忌随着一代代世风日下的堕落而松动。生活中的性享乐追求和小说里的“色情描写”,使两性情爱关系中的身体因素凸现出来。20世纪性自由的试验在文学领域全面展开,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道德固守后,60年代最终从法律上解禁的西方世界,各种性学思潮轰轰烈烈登上了大雅之堂。此时闯入文坛的耶里内克及性主题小说有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她的写作思考自然就从这解禁后的性问题开始了。
在《逐爱的女人》中宝拉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去做娼妓,而从陌生男人那里拿到钱来讨好自己的男人,可结果是什么也没得到还被埃里西无情地抛弃。面对同样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却对男性拈花弄草宽容得多,比如海因茨与布丽吉特发生关系时还缠着漂亮的苏茜。当事人显然认同这种性权力的不对等,女性似乎被排斥在性的话语和享受之外,其间两性关系的不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女权运动和性解放之后的泛性年代。早在《我们是诱鸟,宝贝》中,透过作品对性器描写与性行为的刻意渲染,粗俗而悲苦的女性的命运,如同一个人人都可受用的工具一样任意拿放,作品的描绘中到处充满了血腥,到处滋生着暴力。像埃里卡杀死父亲,奥托杀死朋友,女性沦为男性阴谋的帮凶。作者把人类最隐私的东西直露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以展示性的生物禀赋和自然状态。但这种来自性的“生命狂欢”给予我们的警示,一如埃利斯《性心理学》所言:“性是一种充盈于生命中,并提高生命质量的强大的力量,但是,人们对性保持着恐惧的心理。”耶里内克试图用强刺激的矫枉过正让人们习以为常。《米夏埃尔》中写英格·迈泽的八处“我性欲强极了”的自我言说,每次基本重复的描写,把一个女人对性的要求写得如此赤裸,已经开创了先河。接着描写比尔叔叔这个男人的性渴望一段更是一种非常态的发泄。尽管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性是人类饥饿本能,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然而,自然主义式的直白并没有让读者觉着美味可口,正是这种反向效果的追求传达出“性生态”(自然两性关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冲突与和谐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失衡与扭曲的隐喻。
可见,在耶里内克编制的两性关系中,性的生命力展示主体是男人,而动力源却在女人那里。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明确的,只要你是女人,就有先天的“诱惑基因”,你就对男人有一种罪性的吸引。只是这种吸引的结果却产生了力量的倒置,最终反而伤害了女人自己。
二
我们知道,在东西方共同的两性观念里,“爱情——婚姻——性”是三位一体的,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一向经典的理论已经变得纠缠不清。错位了的“性”更多的是一种享乐和繁衍的寄托,而非表达爱情的方式。耶里内克在《逐爱的女人》中描写的两桩婚姻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这些女人通常以嫁人或者其他的某种方式毁灭。”在她们中,一个是有心计却很现实的女人,处心积虑地讨好为了得到能给她带来财产和身份的男人;一个是怀着纯洁爱情幻想的女人却悲惨地被生活所愚弄和抛弃。她们希望在爱的追求中去找到自己的幸福,结果是他们却变成了“性”的奴隶,处境是被无情地占有、屈辱地生存。城里的女工布丽吉特视“两性生活”为一种手段,因为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认识了一个能以后给他生活保障的男人——海因茨,从此她就挖空心思去讨好海因茨和他的家人,甚至奉献她的肉体尽量去满足男人的欲望,通过怀上海因茨的孩子成了他的妻子。但这种性的生命连接却淹没了爱情,也铸成了一桩无爱的婚姻。布丽吉特身上已没有了爱,海因茨呢——不喜欢布丽吉特,但他还是受不了她的诱惑。埃利斯还曾说过:“婚姻和爱情都以性生活为基础,性和谐是婚姻和谐的保证。”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布丽吉特的身上没有看到,在宝拉的身上也没有看到。《逐爱的女人》这样描述宝拉的追求:“学完裁缝以后,享受一下生活,去意大利,花自己挣的钱去看电影……然后结婚跟他生孩子,生活在一起并相爱。”开端是美好的,但她爱上了一个不值得她去爱的人,并且更不应该怀孕,阴差阳错筑成千古之恨,她的梦破灭了。
事实告诉我们,爱在现代生活中早已经不起考验。从理论上讲生活是一个大的百科全书,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饮食起居等无所不包,当然也包括爱情。而作品呈现给读者的冰冷的现实是:生活远远比爱情残酷。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呈现出女人的软弱,女人决不要在消亡的爱情中把自己交付于男人,成为男人“性”发泄的工具。布丽吉特的身体就是女人和不爱她的男人之间的交易资本,这样的两性关系意味着:性成了消费品,只是为了人们提供某种身体上的需要,与婚姻和爱情没有必然关系。在男女的情感世界里,费尔斯通认为,女人在性生活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男人可以割断他们性需要与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而女人则做不到。拥有了浪漫、性和男人,她们才是最幸福的人。宝拉的结局就说明了这点,她们的灵魂被生活压力无情地粉碎后又被肉体吞食,导致爱情在物化灾难中成了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是那样的脆弱而不堪一击。
在性泛滥的欲望化时代,爱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情与爱作为文学主题表现力生成源也越微薄渺茫,性在这个时代成了艺术本身,就如同一个漂亮女人成为大家观摩的对象一样没有一点遮拦。耶利内克通过作品里肆意地性描写,直击人性深层那原始、野蛮而残酷的欲望中心,这不简单地表现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身体的征服,而是时代性意识混乱与两性关系不和谐的表征,从中体现的是文学中欲望叙事的本真意义。在这样一种性解放之后,“性”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游戏被直接暴露于公众的面前,让人们以肉体的渴望填充精神的空虚。爱情的价值消亡后,剩下的就是与权、钱等值的赤裸裸的交换了。
耶里内克的小说从始至终展现出这个时代性的生命力及存在状态,自然还有相随的爱情渐次消亡的过程。耶里内克也想通过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来唤起女性的清醒,以应和福柯对文明的忠告:从性中解放出来!走出人类对性的病态憎恨和偏执迷恋的误区。但文学如何适当地去触动性问题——这一敏感的社会神经?在耶里内克的小说里我们没有找到答案,然而,我们却得到了启示:性爱分离的两性关系作为性解放和技术文明的产物,尽管背离了伊甸园的理想图式,可已经是既成的现实。对此,无论是道德的压抑,还是行为的放纵,都不是自然的表现,更成熟的态度应该是宽容而不过多的关注,当然,炒作是最拙劣的“艺术”方式。而对于评论界来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描述极具借鉴价值:“现在,传统道德受到了动摇,而人们还没有提出新的道德观来取代它。旧时的责任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威力,而我们尚无法清楚而肯定地看到我们新的责任是什么。不同的思想观念拥有相对的看法,我们正在经历一段危机时期。因此,我们不像过去那样感受到道德规则的压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淼霞,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