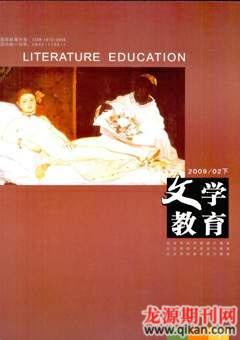向钱看,钟爱书
黄维梁
近年,面对刚入学的研究生,我总是引述苏东坡的话:自孔子圣人,为学必始于观书。我要学生向钱看,到图书馆观观、翻翻、看看钱钟书的书: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又名为《容安馆札记》,三巨册,共二千多页的这本大书,每页都是钱先生观书后写下的笔记: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都是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所说的“文字、文字、文字……”,是字林,是字的森林、丛林、热带雨林,其“繁密”超出古代诗评家钟嵘的想象。
《手稿集》中,从《诗学》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急管繁弦”般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毛笔字,是钱老年轻时就开始写的——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饱蠹楼”音义兼顾,是钱钟书的雅译,就像徐志摩之译Firenze为翡冷翠)。饱蠹楼的书不准外借,钱先生于是天天在楼中蛀书、抄书:这只不厌的蠹虫,被喂饱了诗书。札记有一条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耶稣最容易受诱惑。钱钟书只受书的诱惑,不受别的诱惑。他一生淡泊名利,成大名后曾婉拒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有书万事足,甚至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慨。其实他有忧患,他的著述是忧患之书,是另一种“蚌病成珠”。他一向关心世事时局。《手稿集》第2120页引用米沃什(Milosz)《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的话,说某小说预言了苏联控制下东欧的情况,“绘声绘影”。据钱夫人杨绛女士说,已出版的三巨册《手稿集》,其篇幅大约只有钱氏全部手稿的二十分之一。这些手稿是一部文字传奇。
钱老从小就钟爱书,当爱情来时,他仍亲密地离不开书。据新近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所说,年轻时钱钟书和杨绛初识不久,双方都介绍对方看书。然后是写信:钱、杨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而钱氏写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杨绛日常散步回到屋子里,“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这使人想起钱氏小说《围城》中方鸿渐与唐晓芙谈恋爱时,二人近在咫尺,方却天天写信给唐。由此可见钱钟书钟爱书,还钟爱书信。
他数十年来不喜欢参加形形式式的文学文化活动,而靠通信来与人交游、交往。他是“文人”,也是“读书人”,是名副其实的man of 1etters。他一生大量写作书信,如果有人在海内海外寻寻觅觅后把钱氏书信汇集在—起,这些书信必然汇成“翰”海,成为一大观。
钱老一生读书、做学问、慎思明辨,他打通中外古今,跨越多个学科,著书立说,壮年时兼写小说,成就他卓越的文学事业。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将会不朽,其《管锥篇》也将成为经典;我认为:《钱钟书手稿集》应该也成为永恒的丰碑。哪个地方要举行书展,要举办读书周、读书月之类活动,都不妨竖起这三块书碑,以为装饰——不,以为象征。
去年华南某大城举办“读书月”活动,我参与盛会,并向一位负责人建议:明年(即2008年)是钱钟书先生逝世十周年,“读书月”可安排一个与钱先生有关的节目,可在相关场地陈列《手稿集》三块象征性的书碑。一年已过,金秋又来,但“读书月”不见钱氏的任何踪影。我浏览两岸三地的文艺资讯,除了零零星星忆念钱氏的文章外,也不见任何具有规模的纪念钱氏逝世十周年的活动。查阅资料、点击网页时,倒是有一个发现:有人建议在湖南省涟源市建设一个钱钟书广场。为什么建议在此地,而非钱氏出生地无锡,或者他久居的上海、北京?原来涟源市旧称蓝田,七十年前蓝田创立了“国立师范学院”,钱氏在此教了两年书。其小说《围城》所写的三闾大学,正以此学院为原型;小说的人物也多以现实的儒林为模特儿。古人说“玉出蓝田”,满有精金美玉见解的钱氏名著《谈艺录》,原来也在蓝田酝酿、构思。如今蓝田日久校如烟,但是钱氏的作品仍然发光发热——通俗点来说,仍然卖钱。在涟源即蓝田建一个钱钟书广场,立一座钱氏雕像,竖三块手稿丰碑,以纪念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文化昆仑,我相信文化界一定赞成。
建广场之议大概在多年前提出,不知道是否接受、落实?现今青少年酷爱打电游机,报纸杂志都以图片取悦读者,报刊上影星的一袭罗裙就遮盖掉一二千个文字,球星的一脚就踢走三五首诗歌,文字几乎沦为图像的说明。一些青少年爱看图像。在这个图像喧腾的时代,我们要提倡读书、读文字,因为文字、书本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钱钟书先生一生钟爱文字钟爱书,不管广场建不建,书碑立不立,在纪念钱氏逝世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鼓励青少年——包括年轻的研究生——向钱看,钟爱书。
(选自《文学界》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