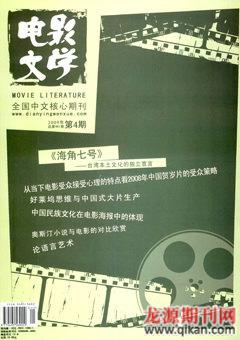生命在继续
张爱民
[摘要]人类发展史上,人们经历了很多天灾人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人们的生命意识从未断绝过。伊朗电影中体现出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虽然不少电影都表现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几乎没有一部影片中带有廉价的感伤主义。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村庄三部曲”《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命在继续》和《橄榄树下的情人》,用艺术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主题。
[关键词]生命;阿巴斯;命意识
“5·12”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我们为地震纪录片中表现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人文意识而深深感动。同为亚洲国家的伊朗,1990年爆发了大地震,约有5万多人死亡,仅在地震中丧生的儿童就超过2万人,20余万人受伤,350万人无家可归。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命在继续》和《橄榄树下的情人》三部影片以伊朗大地震为背景的“村庄三部曲”,表现了相似的生命意识。
三部曲的拍摄地点是位于德黑兰以北几百公里,名为柯克尔和波什特的小村庄及附近地区,这些村落后来在大地震时遭到破坏。震后的第二天,出于感情的原因,阿巴斯就出发去寻找《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影片里的两个小演员,但没找到他们,就去慕尼黑参加影展。1990年6月,大约是大地震后的一个礼拜,阿巴斯在慕尼黑参加影展,参展影片是《哪里是我朋友的家》。记者会中有人问到剧中小孩阿默德及那个村落怎么样了,阿巴斯回答说他们已经都不在了,现场马上陷入一片寂静,然后他叙述灾后前往灾区寻人的经过,当即有位德国的发行商建议开拍这段过程,影片以寻找这两个小孩为目的。阿巴斯当初即构想在《生命在继续》中寻找小孩的故事框架。
《生命在继续》以类似纪录片的写实手法,表现了在地震之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影片的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该片的拍摄地,去寻找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影片中饰演主人公的两个小演员。影片的一开始就把叙述主体定格在了车中父子的身上,父亲不苟言笑、忧心忡忡,儿子机灵可爱、问个不停。这两位主人公构成了影片展开的两条线索:父亲从头至尾目标坚定,立志要克服重重阻挠,找到自己从前的小演员;儿子则秉持着儿童特有的好奇心、活力和善良,更愿意“节外生枝”,用自己的活力映照出了震区中灾民坚强生存的乐观和活力。这对父子的震区之旅在经过了一段漆黑而漫长的隧道之后正式开始,阿巴斯给出的震区的第一组镜头是隧道的黑暗结束后突现的光明,在飞扬的尘土和嘈杂的环境中,百姓、僧侣、警察在废墟中努力地劳动着,背后大喇叭中悠扬的民族音乐响起。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开篇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和主题,它展示了灾难的悲剧性和残酷性,却要在残垣断壁的背景中凸现生的力量。晃动的镜头展现出劫后余生一片狼藉的村庄,当观众正为那些遭受灾难的人们痛惜和伤心时,镜头一转,从那被震坏的门框推出去,门框之外是蔚蓝的天空,明亮的阳光,浓密的绿阴,欢叫的鸟儿,一派生机盎然的诗意景象,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就这样通过长镜头一下子呈现出来,让人豁然开朗,一扫阴霾。门框内外景物的对比寄予了伊朗人对未来的希望,灾难虽然残酷,但是生命依旧美丽。每当言及亲人的死亡,他们虽然面露悲戚之情,但这并不会动摇生者的“生活在继续”的坚定的责任。影片结尾的那个经典的汽车冲上高坡的长镜头,更是形象地同时也寓意深刻地表现了伊朗人民勇往直前、顽强生存的精神。
在影片的结尾处,主人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那两位小演员,但是有路人说看见过他们。镜头的尽处出现了两个小孩。这样的情节设置正是导演阿巴斯有意为之的。虽然他本人第一时间就奔赴震区去寻找那两个小演员,但一旦涉及电影,阿巴斯决定“把所有感性的形式放在一边”,他宁愿用片中两个小演员的缺席作为对地震中两万名死亡儿童的默哀,抛弃了最终喜剧化的悬念,而将主题集中于“对那些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并且尝试迎难而上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展现出勇气和希望”。影片《生命在继续》表层意义上寻找的是当年那两个小演员,实际上影片寻找的是人类生命的希望。阿巴斯在简洁流动的电影影像中赋予的是深沉的哲学意念,该片荣获戛纳电影节的“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和“金摄影机奖”。
《橄榄树下的情人》影片的拍摄地点位于当年拍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乡村,影片表现了该地区经历了一场地震,地震后,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到某个村庄拍一部叫《生命在继续》的影片,导演亲自在当地挑选主要演员,选上了一个正在念书的姑娘塔赫莉和年轻的砖瓦匠侯赛因,在剧中他们饰演一对夫妻。很巧的是,他们俩早已认识,小伙子向姑娘求过婚,但因为目不识丁且没有多少财产,遭到姑娘祖母的拒绝。在拍片的间隙,侯赛因对姑娘照顾有加,不断用言行证明自己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恳请姑娘摆脱祖母的陈腐观点,答应嫁给他,他告诉姑娘,因为地震死了很多人,他们应当完成真主安拉派给他们的生儿育女的义务,因为他是文盲,他的后代不能没有文化,而这位姑娘却受过教育,能弥补这一缺憾。可女方只是埋头读书,一言不发,连头也不点一下。影片拍完了,剧组解散,眼看最后的机会也要溜走。在他人的鼓舞下,侯赛因追随塔赫莉走在她回家的路上,反驳她可能提出拒绝下嫁的理由。小伙子不停说着,姑娘仍始终沉默。这时,摄影机先是跟随他们的脚步,后停在了一个高点上,电影的最后是一个四分钟左右的长镜头,表现的是侯赛因远远地尾随着塔赫莉,两个人一前一后,侯赛因拼命地追着姑娘,遍地的绿色中只看见两个小白点在移动,一开始是越来越近。在几乎看不到的最远处,变为一个大点,可是后来又分开了,小伙子又向摄影机方向跑了回来,一直跑到树丛中,影片就结束了。影片中的人们在困境下的一种沉静之美,巨大的灾难没有动摇人们对实现生活美好愿望的努力。正像影片中那个女孩子怀里抱着的盆花一样。生命总是顽强地散发着热情。
如果说上面两个片子是从正面来表达这一主题的,那么《樱桃的滋味》则从反面回答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阿巴斯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平铺直叙了一个人求死的虚构故事: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巴迪做好自杀的准备,只差一个帮他收尸的人,他驾车四处游荡寻找却屡遭拒绝。失业工人以为他是精神病,士兵则以信仰为借口加以拒绝,却不能解释“军人杀人和自杀有何不同”。神学院学生以伊斯兰教义中不准自杀的戒律劝阻他,但苍白的教义也无法驳倒巴迪的理论:如果自杀是一种罪过,那么不快乐是什么?不快乐的人会伤害别人不也是罪吗?最后一个是土耳其族的老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老人向中年人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年轻时曾因为生活过于艰难想过自杀,当绳子挂在樱桃树枝上时,他看见了久违了的日出,绿色的大地,一群快乐的孩子,品尝了挂在枝头甘甜无比的樱桃,于是觉得活着是美好的,便活了下来,老人要中年人自己去做出选择。阿巴斯其实是想通过老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哪怕是为了生活中最微小的快乐,也要热爱生命。中年人告别老人,开车远去。一个雨夜,他躺在事先挖好的土坑
里,等待死神的降临,可是第二天的早晨他被士兵们的报数声惊醒,从坑里爬出来。在这里,阿巴斯选择了一个开放的结尾,爬出土坑的中年人出现在拍摄的现场,一扫沉闷和压抑。影片的巴迪表面上在寻死,却在四处找人想解答生之困惑,探寻生的意义和价值。这部影片比以往的作品更抽象。充满着浓浓的哲学的诗意,通过巴迪这个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的人的自省之旅再度探索了生命的意义。影片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主人公的要求,这恰是一种对死亡的本能的抗拒。虽然主题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伊朗伊斯兰教文化和伊朗电影的禁区,但阿巴斯想通过镜头传达给人的是存在主义的命题:生存是一种选择,而非责任,你无法选择如何生,却可以选择如何死。假如生命也是一种选择,人们为什么不选择话呢?最终巴迪是否放弃了生命,不得而知,但阿巴斯“以寻死为始,阐述生命可贵”的拍片目的却达到了,他让人们懂得了在人类的生存经验中虽然有沮丧。有失望,但生命毕竟是美好的,其滋味犹如樱桃般甜美,需要人们慢慢品尝。
阿巴斯说:“我记得小时候把自己写的故事给大人看,通常他们都非常谨慎地说挺好,而且往往补充一句:‘可是太悲观了,实际情况没这么糟。我立马就断定他们缺乏独立性,他们屈从于权力。拒绝承认苦难的社会现实。但是今天,当年轻人让我读他们的剧本时。我谨慎地说:‘年轻人,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你也应该试着……从他们的目光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认为生活和经验带给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几年来,尽管处境艰难,但是我的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状态以某种方式反映在我的工作中。”
伊朗电影相对于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电影,具有其独到的冷静与宁静,在喧嚣中保持着静观的态度,是用眼睛、心灵和行动来完成生命的意义。较少的人物对话让他们充满了东方宗教的神秘感——对于话语权力充斥着当代文明而言。在电影结构中不但对白少,而且即使是很少的对自也只是简单地提问,简单地回答,仿佛使人的心灵返回到了古时的纯真年代。伊朗电影的故事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生活。伊朗电影在情节上不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故事性不强,简约散淡,比较贴近生活。影片的节奏也较为舒缓,甚至可以说相当的慢,在具有伊朗特色的风土景物的展示之中呈现诗意美,在平凡的事件中呈现人性与人情的诗意美,在哲理性的思考中寄予诗意之美等。阿巴斯的影片就是这样的,这种风格在他的诗歌也有较好的表现。阿巴斯的诗歌极其简单,甚至这些简单的符号会让你浸染了美感和生命的愉悦之后很快忘记。阿巴斯回到了原本的自然世界,并且把这些简单地记录了下来,他这种孩子式的记录使他获得了轻松自在,御风徐行的生命享受,也使阿巴斯成功地跳出了某些传统的观念和桎梏,获得了诗歌和电影艺术上的新奇飞跃。
理解阿巴斯还是要从他背后坚实的民族文化背景谈起。正如他本人曾说的“梦想要根植于现实”,他整个电影梦想就深深植根在伊朗这块土地上,吮吸着波斯古老哲学的养分。所以,他能够耐心且不动声色地关注人们看似极其普通的生活,然后从中挖掘出深邃的情感世界。
在13世纪的哲理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中,诗人就将施与和满足、驯顺和坚忍等作为理想中圣徒的品德;14世纪的抒情诗人哈菲兹在诗中则抒发了对现实世界的热爱,而对伊朗的电影人影响最为直接的当属大哲学家及诗人欧玛尔·海亚姆,阿巴斯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电影参照了欧玛尔的思想,并且认为“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的灵魂”,即“要想懂得生命,必须接近死亡,亲眼目睹死亡”。
伊朗电影中体现出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虽然不少电影都表现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几乎没有一部影片中带有廉价的感伤主义。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对现世苦难的忍耐,对造就伊朗乐观豁达、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所以伊朗电影始终充满着古老的波斯民族乐观通达的生存态度和对生活的超然,应该说民族精神正是伊朗电影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