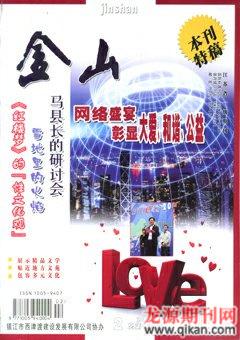《红楼梦》的“性文化观”
郑 文
秦可卿的符号意义首先在于她是“情”的象征,“情可亲”,“情可倾”,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她把贾宝玉“引”上了一条“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漫漫人生路。
众所周知,“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更广义一点说,“性文化”几乎是一切经典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涵。只有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才会像一位三代贫农的老太太所敢于批评的那样,在其“样板”作品中尽写些“孤男寡女”。
然而像《红楼梦》这样,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涉及性文化领域的作品,也并不多见。在中国,由于封建礼教尤其是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以禁欲为中心的性原罪观、性专制观和性污秽观也成为主流的思想。在这种严酷的氛围中,曹雪芹却能在《红楼梦》中表现出一种以生物科学为中心的性自然观,与老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法自然”;与告子所谓“食、色,性也”;与马克思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与鲁迅所谓“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个生命,二要延续这个生命,三要发展这个生命”;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研究等,均可谓不谋而合。而这方面最生动的艺术表现,就出现在贾宝玉到秦可卿卧房里午睡那一段文字之中。
许多论者都怀疑秦可卿是在有意引誘贾宝玉,但从文本的实际描写来看,这实在是冤枉了她。书中明明写着,她本来是带宝玉到上房内间去的,只因宝玉讨厌那里的道学气,这才建议去她房间,而且还落落大方地对众人说:“他能多大呢,就忌讳这些个!”书中还明明写着,不仅有四个丫鬟陪伴着宝玉,外面还有几个小丫头“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而宝玉从梦中惊醒时,秦氏也分明“正在房外”,她又如何能引诱宝玉甚至与其“初试”(有此一说)呢?至于那段著名的关于秦氏卧房的“香艳”描写,实在是曹雪芹在有意调侃贾宝玉这位知识丰富的贵族公子春潮泛滥的“性幻想”。如果我们把“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飞燕立着舞过的”、“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同昌公主制的”、“西子浣过的”、“红娘抱过的”这些虚拟的华丽定语统统去掉,那也不过是说秦氏房中放着镜子、盘子、木瓜、床铺、帐子、被子、枕头而已。你贾宝玉自己因为“性萌动”而浮想联翩,又如何能怪罪秦可卿呢?有趣的是,近读一位先生的文章,说他怀疑秦氏房中应有如同“傻大姐”捡到的“绣香囊”之类的东西,所以依然要怪到她的头上去。这就实在是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文字,的确是经过了重大的删改,但又没有来得及修补完善,致使秦可卿成了一个既重要又模糊,而且充满了矛盾的形象,成了一个符号性、象征性的人物。关于她的出身,关于她的为人,关于她的情孽,关于她的死因,都令人疑窦丛生。在我想来,这个人物的大删大改,似乎反映了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他把秦可卿排在金陵十二钗的末位,还在《红楼梦》曲《好事终》中评论她“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就把贾府的衰败归咎于她了。如果真的按这种“红颜祸水”的思路写下去,那就必将对《红楼梦》的思想品位造成严重的损害,当然也与曹雪芹为“闺阁传照”的初衷有违。所以我怀疑,曹雪芹之所以要作如此大的改动,主要倒不是因为“受命”于脂砚斋,而是“受制”于他自己越来越明确的创作思想。
秦可卿的符号意义首先在于她是“情”的象征,“情可亲”,“情可倾”,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她把贾宝玉“引”上了一条“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漫漫人生路。在贾宝玉从孩子长成一个男人的时候,秦可卿不啻是他的“梦中情人”。而这位令宝玉不胜向往之至的女性,竟然又有一个乳名叫“兼美”:“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曹雪芹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写,所以秦可卿又是“钗黛合一”的象征。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钗黛二人的册子词也是合而为一的。从“色”的角度来讲,宝玉是同时迷恋于黛玉和宝钗的;但他最终选择了黛玉,那就是“传情入色”的结果了。由此,曹雪芹就突出了爱情的关键作用,在此后关于宝黛爱情的大量篇幅中,他又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种纯真情感的优美,这就标志着曹雪芹的性文化观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第十六回秦钟死。在这16回书中,有不少“皮肤淫滥”类的内容:宝玉和袭人的越轨,薛蟠的“龙阳之兴”,众学童的胡闹,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秦钟与智能的偷情,当然本来还有天香楼的遗事……但最终,贾宝玉并没有在这个大染缸中沉沦,反而用他与林黛玉纯洁美好的爱情体现了《红楼梦》性文化观的升华。这种爱情正如恩格斯所言,是“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它完全突破了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把汤显祖笔下杜丽娘爱得死去活来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但又比杜丽娘爱得更加纯情,更加丰富,更加高尚。于是,曹雪芹对宝黛爱情充满诗情画意的精彩描写,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文学中罕见的经典。
曹雪芹不仅生动地展现了爱情的自然与优美,而且把它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描写贾府走向衰败破灭的同时,反映了它备受压抑、摧残乃至毁灭的过程,最终完成了王国维所谓“不得不然”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