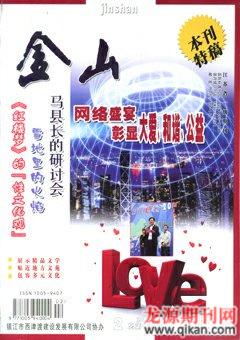媳妇熬成婆
申 弓
姐嫁去的地方叫龙镇岭,是个不大的村子,约有十几户人家,自成一个生产队。姐夫是个腼腆的青年人,对姐很不错。我们都认为姐嫁对了,在那里挺幸福的。
可姐回来时说,家里有个婆婆,钥匙由婆婆掌管着,家里的一切都得经过她。婆婆挺严厉,姐没有自由。这个自由,当然是经济上的,比方想要买些什么,得要婆婆批准,得要婆婆开箱子掏钱。比方要回一趟娘家,也得婆婆准许,所带之物,更得婆婆打点,想多给点都不行。睡得晚些她就要催,还不快睡,明早有事,也浪费灯油。你要起得晚些,她也要来催:还不起来,你看有谁起这么晚的?早起三朝赛一日。
姐的婆婆我见过,是姐嫁去的第三天我去“看朝”时见的,我叫她亲家母,人不高,嘴巴扁扁的,那双眼睛看人眯眯的,不太让人喜欢。最大问题是我们家较穷,所谓穷,也是因为我们兄弟多,所处的生产队分红也低,加上我们还有兄弟三人在读着书,姐初嫁到,心思还放在娘家转不过来,常常想着要多资助一些给我们,只是碍着那严厉的婆婆。有一回,姐在婆婆装好的物品担里悄悄地多加了三升大米,却被婆婆发现了,眯缝着小眼看着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里才是你的家呀。等到有一日我不在了,还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呢。因此,婆婆那串钥匙无论什么时候都随身带着,从没放开过。
姐每回回来,都感到很愧疚,总是跟母亲倾诉家里的番豆婆怎样严厉怎样刻薄,其中最让姐耿耿于怀的就是亲家母裤带上的那串钥匙。
母亲问姐,婆婆有多少岁了?姐说七十多。
母亲便说,恐怕时间不多了,熬吧。
姐便这样熬下来。
几年后,婆婆便死了。
姐便接过了那串亮光光的钥匙。姐算熬出头了。
熬出头的姐,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家庭的总管,见天里要为柴米油盐操劳。熬出头的姐回我们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半年也不回来一趟。到回来时,也不见姐多带东西回来,见着母亲,总是叹息,这家太难当了。言语之间,对已故的婆婆没了怨气,相反倒有了几分的怀念。母亲却感到欣慰,说姐真正长成人了。我知道母亲所说的成人,也就是说姐已进入了角色。到了姐的儿子上学之后,姐再来时,不但没有带东西来,相反,每次总是说阿牛喜欢家里的什么什么,总是要满载而归。当然,这时,我们兄弟都已出来工作了,时常资助家里,家庭经济已比姐好多了。母亲因为生的儿子多,就这么一个女子,也就特别地疼愛,每回都总是帮着姐把带来的袋或箩塞得满满的,并且还要提着送出一程,这正应了“十个女儿九个贼”的说法。
我想,姐要是讨了儿媳妇,她的儿媳妇也一定要说她严厉刻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