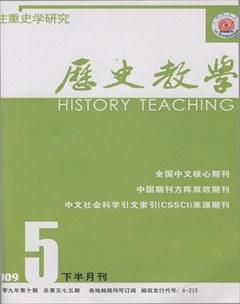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考
郭宗全
[关键词]司马迁,出使西南,受降置郡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0-0084-07
关于司马迁,人们最关注他写《史记》。然而司马迁说自己除了写作《史记》,还曾经“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出使西南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学者给出的说法,有视察慰问、战略调查、传令监军等,似乎在司马迁生平和西汉历史中并不重要。本文通过对司马迁自己的表述、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西南平夷置郡的情况、司马迁出使西南的时间和线路加以考证,认为司马迁是汉武帝开拓西南疆土的中央使节,他在西南接受了众多部族的归降,在今天贵州、重庆、云南东北、四川西部、甘肃南部的广阔地区设置了牂牁、越嶲、沈犁、汶山、武都五郡,在西南夷归入汉朝多民族国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融合和祖国疆域形成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司马迁奉使经略西南这件事应当同他撰写《史记》、开创中国史学那样,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肯定。本文试考证司马迁奉使西南的任务,并阐述其历史作用,向方家求正。
一
《史记》《汉书》明确记载司马迁出使西南的只有一句话:“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是司马迁自述个人的经历。从表述来看,“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的是出使的目的地,“南略邛、笮、昆明”说的是去巴、蜀以南做什么事情。司马迁说自己出使西南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关键是理解“略”“征”二字。
首先,我们看文字家对“略”“征”二字的解释。略字在《说文解字》中置于田部,说明许慎认为此字与土地相关。许慎解释:“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所谓经略土地,当代《说文解字》的注、译家认为就是指划分土地的疆界。例如汤可敬撰的《说文解字今释》云:“经略,同义连用。桂馥《义证》:‘经略犹言经界也。徐灏《段注笺》引戴侗说:‘略:启土而经画疆理之也。”所以汤可敬将许慎“略,经略土地也”一语译为:“略,划定土地的疆界。”李恩江、贾玉民主编的《说文解字译述》对许慎解释语也这样翻译:“略义为经营土地,划定疆域。形声字,田为形符,各为声符。”谷衍奎编的《汉字源流字典》亦云:《说文·田部》认为“略”字“本义为经营土地,划定疆界”。现代文字学者如此理解《说文》对略字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征字在《说文解字》中置于辵部,说明此字与行走相关,其解释云:“征,正行也。从辵,正声。”《尔雅·释言》亦云:“征,正行也。”所谓正行是指有目的远行,《汉字源流字典》的解释最形象:“甲骨文从彳(道路),从正(一只脚对着城市前进),会向某地进发之意……本义为有目的远行。”可见,“征”字本义非讨之征,乃征行之征;“略”字本义非攻略之略,乃指对土地划分疆界。后人构词,征字构成“征讨”,略字构成“攻略”,这是引申义,不是本义。近年出版的《二十四史全译·史记》将“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一句译为:“奉命出使西部征讨巴、蜀以南地区,向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回到朝廷复命。”使用了征、略二字的引申义来理解司马迁原话。查《汉书》《通鉴》记载西汉在司马迁出使西南期间,统兵讨伐西南夷的将领是中郎将郭昌、卫广,奉命“征讨”“攻略”的并不是司马迁本人,显然,司马迁原话里的征、略二字,用的不是引申义,而是本义。认为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为“征讨”“攻略”,这是不正确的。
其次,我们看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略”字来叙述西汉使节出使西南夷时,该字用来指称什么事情的。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与夜郎王多同“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司马迁将这样的事情称为“唐蒙已略通夜郎”,或“唐蒙使略通夜郎”。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去接受邛、笮、楪榆等西夷部族的归降,在当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司马迁将这样的事情表述为“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可见司马迁写西汉使节出使西南夷所用的“略”字,意思一指招降或受降,二指置郡,语境意指西汉派使者出使西南,通过和平方式将西南夷及其聚居地纳入汉朝管辖范围。近年出版的《史记》今人注释本也有对“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中的略字注释为“行视、视察”的。其实,司马迁对使者出使任务为视察的记述并不使用“略”字,例如汉朝沟通西南夷之后,唐蒙征调夷民凿山通路,导致西南夷数次反叛,元光五年汉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视察,司马迁写道:武帝“使公孙弘往视问焉”。他用的是“往视问”而不用“略”字。汉武帝还曾派司马相如行视西南,责诫唐蒙并安慰巴蜀之民,司马迁的表达是直接写:武帝“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亦不称此事为“略”。既然司马迁对汉朝使者赴西南受降置郡称为“略”,事情办妥后称为“略通”“略定”,那么,我们把司马迁述自己奉使“略邛、笮、昆明”理解为他到邛、笮、昆明等地去接受归降、划郡置县,这才符合他使用“略”字记载汉武帝派遣使者经略西南、开拓边疆的特定意思。
再次,《史记集解》的注语也说司马迁奉使西南目的是为了平夷置郡。裴马因在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一语之下注云:“徐广日: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司马迁原话讲的是个人经历,裴驷引徐广语作注,意在说明司马迁为何事出使西南。就是说,裴、徐都认为司马迁奉使西南是为了平定西南夷、设置五郡。对照元鼎六年汉朝平定西南夷是以军队征定为辅、和平受降为主的情况(下文述),我们就得出一个与裴驷徐广注语、西南平夷置郡事实都相符合的意思:司马迁奉使西南,任务是接受归降、设置五郡。
综合上述,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句话应当理解为: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邛、笮、昆明等西南夷地区接受归降、设置五郡。这才符合司马迁所表达的、他奉使西南任务为受降置郡的意思。
二
要证实司马迁自述出使西南任务为受降置郡,必须找出司马迁奉使西南的具体时间,并且奉使时间与汉朝在西南平夷置郡的时间一致。
司马迁奉使西南起、迄于何时,《史记》《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关于返回时间,司马迁在“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一语后面接着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今河南洛阳——引者注),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据此,学者公认司马迁返回复命的年份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复命的月份,查武帝在首次封禅泰山前后的行踪:“三月,遂东幸缑氏(今河南师偃——引者注)……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初七——引者注),上还,登封
泰山。”封禅后,武帝沿海边“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在武帝这条巡行路线上,司马迁讲述他曾经到达三个地点:一是云“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时间当在三月。二是云“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没有明确说他参加了首次泰山封禅。三是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武帝多次出巡北方,而视察长城边防仅元封元年四月这一次,就是说,司马迁扈从武帝视察了长城。上述说明:司马迁奉使返回是追赶着武帝的队伍复命的,复命时间大致在三月下旬四月问。
关于司马迁出发的时间,学者现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为元鼎五年秋,认为当时武帝命令五路大军讨伐南越,其中一路由驰义侯征调西南夷的夜郎兵顺牂牁江东下,司马迁此时就随驰义侯去了西南。此说值得怀疑,驰义侯赴西南任务是“因犍为发南夷兵”往东伐南越,司马迁则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怎么会跟随出发?元鼎五年武帝集中力量平南越,尚未着手解决西南夷,文献亦无这年秋天汉朝派使者出使西南夷的记载。第二种说法为元鼎六年秋,在平定西南夷、设置五郡之后出发的。王国维说:“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犁、文山郡,史公奉使,当在置郡之后。”此说多为今人引用,但是王国维仅据《汉书》一个置郡时间就推定司马迁在置郡之后才出使西南,下结论可谓武断。第三种说法为元鼎六年春,张大可先生说:《汉书》记载武帝这年“春,至汲新中乡(今河南汲县),得吕嘉首,上便下令征西南夷”,司马迁作为郎中正在侍从武帝,奉使出发就在这个时间地点。武帝元鼎六年春下令征讨西南夷,《汉书》《通鉴》都有明确记载,虽然未写明使者在下令时就出发,但是对照司马迁的自述、裴驷的注释都说奉使是为西南平夷事,元鼎六年春出发是可信的。出发的月份,张先生只说“春,即元鼎六年正月”,不见依据。查《史记》记载征越汉军擒获南越叛首吕嘉的时间为元鼎六年冬,这年西汉使用《颛顼历》,以秋为岁末,冬为岁首,十月为初冬。即使擒获时间最迟在冬十二月,将吕嘉首级由岭南送往河南汲县新中乡武帝的行在所,一个月左右应当到达。武帝得吕嘉首级与下令征讨西南夷同时,则司马迁出发时间就为春正月。
如上所述,司马迁赴西南的出发时间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正月,向汉武帝复命时间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四月间,奉使前后约为十五个月。这个时间正处在汉武帝积极向四周开疆拓土的时段,就在司马迁出使西南之前的十年间,武帝开通了西域(公元前122年),驱逐了匈奴(公元前119年),平定了南越(公元前111年),现在又下令征讨西南夷。这个时候司马迁从武帝身边奉命出使西南,其使命内容与武帝开拓西南边疆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事实上,就在司马迁逗留西南期间,《史记》《汉书》都记载西南的且兰夷、邛夷、笮夷被汉军打败,其他夷族震恐,纷纷请臣归降,于是汉朝在西南夷地区新置了牂牁、越嶲、沈犁、汶山、武都五郡。司马迁作为汉武帝这年唯一派赴西南的使节,应当就是这次受降置郡的主持者。而且,他返回复命的时间比元鼎六年西南夷平定的时间迟半年,受降置郡任务就更加明显了。
三
确认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为受降置郡,元鼎六年汉朝在西南平夷置郡的情况是关键。如上所述,这年汉武帝既派出了征讨部队,又派出了司马迁这位经略使者。我们考察平夷置郡的过程。发现西南夷的多数部族不是武力征定而是和平归降的,五郡不是中央直接指定而是通过司马迁实际调查、将西南夷分类之后设置的。
首先,我们来看平夷的过程。汉武帝只是“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这支部队原本元鼎五年秋准备从巴郡顺牂牁江东下参加平南越的,为且兰夷反叛所阻。它由巴、蜀两郡罪人编成,并不是汉朝的正规军。人数也不多,八校尉乃汉武帝军队的一种编制,“每校尉有兵士七百人”,人数大约五六千,由中郎将领郭昌、卫广率领。面对大小部族数以百计的西南夷,显然这支部队只是作为使节经略的后盾,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西南夷是以使者经略为主的。从平定情况看,真正动武征服的只有且兰(也称头兰)、邛、笮等几个部族。司马迁写道:“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夜郎侯始依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接着汉军诛“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包括最大的夜郎国,多数西南夷是请臣归降、和平解决的。从归降到纳入汉朝管辖中间有个重要环节,即受降置郡。汉武帝处理西南夷请臣归降的惯例是:由中央使者会见归降部族的“君长”,接受其土地和人口,对其聚居地划郡置吏。对“君长”则给予赏赐和安抚,大部族的“君长”还让其入朝觐见,赐予封号、王印等。查史书,元鼎六年汉朝并没有派赴西南的其他使者,唯独见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赫然大书自己“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据此足以相信,司马迁就是这次西南夷归降的受降人,他代表汉朝中央政府将西南归降部族纳入了汉朝多民族国家范围。其次,我们来看置郡的情况。虽然史书没有记述元鼎六年西南置郡的具体过程,但是《西南夷列传》是司马迁参加了这次平夷置郡后写成的一篇传记,传记一开头就以较长的篇幅,根据聚居范围、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将西南众夷归类、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范围,按区域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分布和习俗。将传记中的部族划分与西南五郡的设置一对照,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司马迁当年置郡的痕迹。从对照表中得到两点理解:其一,司马迁对部族的归类划分与五郡设置完全吻合,二者浑然一体,显然,五郡区划是以部族区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学者研究认为,汉朝对西南夷的管理政策是“因故俗治”。“故俗”即西南夷各部族的居住范围、经济方式、生活习俗,因故俗治就是汉朝对其设置郡县管理时,基本保持“故俗”不变。这一论述,正好说明司马迁对部族的归类划分是执行汉朝中央对西南夷的管理政策,是设郡工作的组成部分。其二,司马迁对西南夷大小部族的分布和习俗掌握得准确、具体,在奉使时间短暂、经略范围广阔的条件下仍作如此严格的调查掌握,其直接动机应当是为了完成使命,其目的应当是作为五郡设置的依据和基础。因为在他出使西南之前父亲尚未将撰史责任交付他,把他当时调查和划分西南夷的动机和目的仅仅归于他为日后撰史积累资料,这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元鼎六年汉朝在西南平夷置郡的情况的确让我们相信,司马迁主持了这年西南受降和置郡的工作。

元鼎六年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为受降置郡,我们从汉武帝开拓西南疆土的历史过程还得到有说服力的佐证。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首次经略西南夷,委派唐蒙为使节,唐蒙“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乃且听蒙约,
还报,乃以为犍为郡”。这次经略的任务是将夜郎及其旁小邑纳入汉朝,设郡管辖,实现途径是和平招降。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位于蜀郡西南的邛、笮、楪榆等西夷“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武帝“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相如接受西夷归降,“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郡县设置后,汉武帝在西南凿山通道,西南夷暑湿饿疲死者很多,纷纷造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不得不放弃西南多数属县。解决匈奴和南越之后,从元鼎六年开始武帝又重新经营西南夷。这一年还是以使者和平经略为主,派少量军队为后盾,结果设置牂牁、越嶲、沈犁、汶山、武都五郡,西南地区大部分纳入了汉朝疆土范围。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解决剩下的滇夷等部族,“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开始滇王“未肯听”,武帝“以兵临滇”,结果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从汉武帝开拓西南疆土的过程可以看到两点:其一,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目标,就是要置郡管辖,将其纳入西汉多民族国家范围。司马迁是武帝多次派遣的经略使者之一,其使命应当与武帝开疆拓土的目标一致,其任务应当同历次经略西南夷的使者一样。其二,武帝将西南夷纳入西汉范围的方法是以使者经略为主,只要西南夷不采取军事对抗,他总是通过和平招降受降的方式来实现归属和置郡。元鼎六年司马迁对西南夷受降置郡,正是汉武帝对待西南夷一贯策略的体现。
四
司马迁奉使任务为受降置郡,通过考察他在西南的行动线路也充分得到证实。西南夷的分布是这样的:从巴郡以南(今贵州和四川东南)往西至昆明地区(今云南大理),依次分布着且兰、夜郎、滇、昆明等夷族,统称为南夷;从昆明夷向北至蜀郡西面,依次分布着嶲、邛、笮、楪榆等夷族,以及成都以北的冉駹、白马夷,统称为西夷。这是《史记》《汉书》的习惯指称。元鼎六年汉朝平定西南夷的顺序是先解决南夷后解决西夷。其进军顺序是:汉军八校尉部队在巴郡以南打败反叛的且兰夷,继续西进,夜郎请臣入朝,遂平南夷。接着北上,诛“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从汉军的进军顺序得知司马迁在西南的经略线路:他由汉中入巴郡,与集结在且兰地区的汉军汇合,首先经略且兰,接着随军西进,经略夜郎,他到达汉军未到的昆明夷地区。然后北上经略汉军刚征定的邛、笮等地,抵达成都。经略冉駹、白马夷后,返回复命。
我们并不是仅仅根据汉军的征伐顺序就认定司马迁在西南的经略线路,司马迁说他曾经南略昆明、“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这是司马迁随着征夷部队一路经略的重要证据。因为昆明即今云南大理地区,司马迁经略到达昆明,则事前必然随汉军由且兰到达夜郎。由夜郎到昆明中间隔着的滇夷国,早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曾经派人寻求通身毒国的道路,使者“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司马迁也称赞滇夷“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根据滇汉关系相对友好来判断,司马迁“略昆明”应当是得到滇夷的帮助,过境滇夷进入昆明地区的。关于“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查司马迁二十岁漫游、跟随汉武帝巡游都没有到达成都,所以成都为司马迁西南之行一站无疑。而且应为后面一站,因为在元鼎六年春正月武帝下令征讨西南夷、司马迁启程之前,汉军在巴郡南面已与且兰夷交手,在君命在身、路途难行、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司马迁首先到达远离且兰的成都去观瞻岷山及离碓,这是说不通的。司马迁亲口说自己经略昆明、观瞻岷山离碓,恰恰说明他经略西南的行动线路是从且兰夷到昆明夷,由昆明夷或滇夷北上,经略嶲、邛、笮、棵榆等夷后到达成都的。司马迁在西南随征夷部队一路经略前进,我们从西南夷平定前的对汉态度还可以得到佐证。早在二十年前唐蒙、司马相如经略西南时,部分夷族如夜郎、邛、笮等曾经归顺汉朝,但是这种依靠汉朝给夷族首领“厚赐”、封侯建立的归属关系并不牢固,他们反复叛乱,且兰夷还居然“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元朔三年(前126年),为了“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放弃了绝大部分属县。在多数西南夷已经叛离或脱离归属关系的情况下,司马迁如果脱离征讨部队这个后盾而另走别的线路,他会举步难行,而且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对西南广阔地区的经略,这是难以做到的。
既然司马迁是随着征夷部队一路经略前进的。在西南夷纷纷请臣归降、地方管理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作为中央委派的经略使节,当务之事就是受理归降,设置郡县。在元鼎六年春至元封元年三月这个特定时间、汉朝在西南平夷置郡这个时候,司马迁奉使西南并且随着征夷部队一路经略,如果认为他的使命为巡行视察,这不符合西南受降置郡的客观形势。如果认为他的使命为监军,则这一年处理归降、设置五郡的事实就无法合理解释。至于将司马迁的使命说是搞战略调查,则更加离谱。
五
汉武帝的西南平夷置郡过程,是开拓西南边疆、将西南夷纳入汉朝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的历史作用有两点:一是接纳众多归降部族加入汉朝多民族国家。西南夷的部族数以百计,大部分在元鼎六年加入汉朝国家,除了且兰、头兰、邛、笮等少数部族为武力征服之外,其余都是和平归降的。司马迁作为主持受降的汉朝使节,他会见部族首领,妥善安抚归降部众,使这些多数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融入了先进文化的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司马迁留下了推动西南民族进步的历史功绩。二是他在西南设置了牂牁、越嶲、沈犁、汶山、武都五郡。自唐蒙首次经略以来,汉武帝多次派使节赴西南招降置郡,所置郡县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已被迫放弃。司马迁出使西南是置郡数量最多、经略地区最广的一次,包括今天贵州、重庆、云南东北部、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均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此后,尽管西南五郡行政区划有所变更,但是这片广阔地区归属汉朝一直不变。在祖国疆域形成的历史长河中,司马迁留下了开拓西南边疆的历史功绩。司马迁赴西南受降置郡的历史说明,我们评价司马迁不能仅仅关注他写作《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还应当将司马迁与汉武帝时期为中华民族融合、为祖国开疆拓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唐蒙、司马相如、张骞、路博德、卫青等名字排列在一起,在我们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丰碑上为他再刻下一笔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才是全面评价司马迁的应有视角。
既然司马迁奉使西南受降置郡是他的生平大事,对汉朝和西南民族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只写“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一句,而不具体记载自己经略西南的过程呢?我们认为这是司马迁有意简略。凡是读过《报任安书》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差点丧命,几乎使《史记》不能写成,其直接原因是他参议政事,为李陵辩护。司马迁以宫刑换回性命之后,向友人披露了自己唯一愿望是完成《史记》写作,不想参议政事的意愿。因而在《史记》中对自己奉使西南、编修《太阴历》等政绩不浓墨书写,这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司马迁本意不愿张扬。可是我们在回顾祖国西南历史、回顾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候,却不能够忘记司马迁代表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南夷和平受降、设置郡县的伟大功勋。
责任编辑:侯林莉
——兼答张大可先生《司马迁生年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