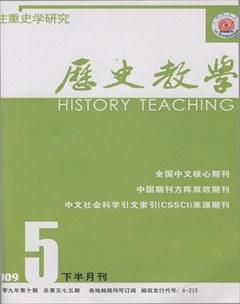蒋廷黻的选择:从外交史家到外交家
冀满红 吕 霞
[摘要]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国家形势,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与鼓励之下,外交史研究领域巨擘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然而,实任驻苏大使的经历对于蒋廷黻而言则是一段不愉快的外交体验。究其原因,既有自身外交经验的欠缺,亦有国内国际局势的掣肘。蒋廷黻从事外交是当时国民政府学人从政的一个缩影,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
[关键词]蒋廷黻,外交史研究,外交家,学人外交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0-0024-06
“学而优则仕”一直以来都是以“心忧天下,经世济民”为标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选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内战频繁、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一批隐身于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出而担当外交重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学人外交”热潮。蒋廷黻先生即是在这一时期被国民政府所聘用,成为“学人外交”的典型代表之一。然蒋廷黻的与众不同在于,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事业皆与“外交”相联系。本文的重点即在于通过考察蒋廷黻从外交史家转变为外交家的人生轨迹,一窥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
一、学界:外交史研究领域的巨擘
蒋廷黻与外交结缘源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八所“常春藤联合会”的会员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尤其是在近代政治学领域,20世纪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汇聚了诸如穆尔(John Bassett Moore)、沙费尔德(William R.Shepherd)与海斯(Carhon J.H.Hayes)等驰誉全球的教授,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学子。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中,曾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就有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与胡适。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受海斯与沙费尔德世界价值理论的影响,对外交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博士论文就与英国外交问题有关,同时他也“对中国外交极感兴趣”。
1923年春,蒋廷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便致力于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由于当时研究中国外交的“标准书籍是莫斯(H.B.Morse)的三卷《中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该书是依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丛书写成的”。而蒋廷黻认为:“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其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因此,“我想根据中国书面资料,来研究中国外交史”。在此理念指导下,蒋廷黻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时,尤其注重对中国外交档案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并率先在南开大学运用档案资料讲授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1929年,蒋廷黻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前往担任历史系主任,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由于“清华大学的设备完善,经费充裕,使他可以广泛的搜集资料。清官的档库固不用说,同时北平故都更予他许多便利收罗清季权臣的私人文件”。经过多年的努力,蒋廷黻终于以清官档案为基础,加上他个人广泛搜集的史料,用西方现代史学体例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上中卷。这两卷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收录了清朝道光二年(1822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政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为国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提供了“自己”的史料。另外,蒋廷黻还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出版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六年(1929~1934年)中,由于直接接触原始史料,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涉外问题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甚至是对前人研究的颠覆性看法。这些见地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论文中,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等。时与蒋廷黻有同事及朋友关系的陈之迈对此评价道:“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这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蒋廷黻作为开创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贡献。蒋廷黻对近代外交事件与外交人物独到的看法,使他成为“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除注重对外交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蒋廷黻对现时外交状况亦投以相当关心。“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社会舆论对中日和战问题的探讨占主流的情势之下,蒋廷黻“不仅讨论当时最为人所关切的对日外交,同时也讨论到当时并不为人注意的对苏外交”,其载于《独立评论》第六号的《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开启了这一先声。由于蒋廷黻晚年曾在联合国提出过影响极大的《控苏案》,故人们潜意识中似乎保留着的仅有蒋廷黻反苏的深刻印象,但在当时,蒋廷黻更注重的则是如何全面的认识苏联,并在此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可能的合作。
蒋廷黻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思想散见于他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时评中。在蒋廷黻看来:“苏联自有其困难。彼所须者为和平,盖准在和平环境之中始能继续其建设事业。彼之国际地位欠佳,夹在东西两强敌之间,而彼无一可靠之与国,彼之不愿在远东多负责任乃彼之自为谋也。”因此,虽然苏联在远东地区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但自德国法西斯兴起之后,苏俄的外交战略重心已逐步移向欧洲。这种态势决定了苏联不得不在远东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日本进攻中国,苏联虽能给中国一定的援助,但在较长时期内,则不可能出兵抗击日本,以致引火烧身。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是正常的,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从理智上来说,苏联当时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什么可厚非的,对苏联所实行的避免作战抓紧建设、蓄积国力对付德国的基本国策,我们要持体谅的态度,不要对苏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指望苏联会无私的出兵帮助中国抗日。但同时蒋廷黻又认为:“苏联面对自己的危险,一定急于争取友邦的援助倒是真的。因此,我对出使苏联一事,是将成功的希望建立在苏联自身的需要上,而非建立在苏联的慷慨上。”
国际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蒋廷黻对苏联的认识以及中日两国形势发展的预测:“中国实际上非常需要外援,甚至包括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我们认为日本在军人的统治之下,对中国必将继续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蒋廷黻对苏联的深入分析,引起了时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曾多次邀请蒋廷黻面谈,听取他对中苏两国关系的见解,“他想知道我的计划,他要我尽可
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一年前(1934年)蒋(廷黻)曾去莫斯科成功地完成了一桩特殊的使命”,即是指此时蒋介石授意蒋廷黻以非官方代表身份赴苏考察,试探中苏之间建立进一步友好关系的可能性。蒋廷黻根据与苏联高级官员会晤所写成的详细报告,成为此后蒋介石政府谋求与苏联关系转变的重要参考。
二、政界:出使苏联的外交体验
1917年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为改变受协约国武装干涉所造成的孤立无援的处境,苏俄政府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为此,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尽管事后苏俄政府并未完全兑现,但这无疑使刚遭受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丝希望。经过长时间秘密接触和谈判,中苏于1924年5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恢复中苏外交关系。但是因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受西方国家反苏政策的影响,中苏关系长期貌合神离。1927年中苏关系再添变数,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14日宣布对苏绝交。后随着中东路事件的升级,苏联也于1929年7月17日宣布对中国绝交。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及远东地区的侵略步步深入,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宣布复交并互派大使。继颜惠庆之后,国民政府于1936年8月26日任命“蒋廷黻为中华民国驻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1月赴苏上任。至此,蒋廷黻由外交史家开始走上外交家的道路。尽管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曾经警告他出使苏联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蒋廷黻则颇为自信,认为“中苏两国均地大物博,在国富财力方面之发展,均无求于人,同时两国目前正努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力求国际和平,故本人此次奉派出使苏联,图谋两国友好邦交方面,当不感任何困难”。况且“两年前本人曾赴苏考察政治制度及经济建设,对彼邦人士所得一切良好印象,至今不忘。至我驻苏大使馆方面,相识者甚多,余之职责当在敦睦邦交,想莫斯科中苏旧友亦必与予协助”。然而,实任驻苏大使的经历对于蒋廷黻而言则是对之前美好设想的一种讽刺,这主要是由于西安事变与七七事变而引起的对苏交涉的复杂性让蒋廷黻始料不及而大受打击。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旨在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突发性事件。以现在的观点视之,诚可为爱国行动。然在时人眼中,由于张杨部队、中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这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苏联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如“‘同盟通讯社传播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之暗示,而遂谓:张学良已成立一政府,受苏联之支持,并与苏联联结有攻守同盟之条约。”尽管“塔斯通讯社顷被授权,声明该项报告为毫无根据,而为一恶意之捏造品也”,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也均否认与中共有联系,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认同蒋介石在中国的统一领导地位。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方面对此仍存疑忌。事变次日,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与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联名给蒋廷黻发的电报中就提到:“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电报还要求蒋廷黻去“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但又未指示具体办法。于是,毫无外交实践经验的蒋廷黻在未与外交部接洽、对整个事件又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凭着书生意气贸然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面,且“第二次与李维诺夫谈时几至决裂”。苏联方面对此极为恼火,李维诺夫训令苏联驻华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表示:“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虽然蒋廷黻在事后致外交部的报告中承认自己的行为“事近越权,应请处分”,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蒋廷黻并未追究责任,而是责其继续与苏方交涉,争取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或共同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以应对因日本侵华步步深入而导致的民族危机。然而,蒋廷黻与苏联方面的交涉并不顺利。中方要求签订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则坚持“谈判的程序应该是:第一步,太平洋沿岸诸大国间先达成一项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第二步,与中国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步才是与中国谈判互助条约”。直到“七七事变”后,苏联才作出让步,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中苏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领土和主权,缔约国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向第三国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协助。虽然“此项条约之内容,极为简单,纯系消极性质,即不以侵略及不协助侵略国为维持和平之方法”,但由于战争初期苏联方面给予中国较大的物资与军火援助,同英法美等国只在道义上同情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使得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人尤其是曾参与蒋介石研究制定对苏政策的孙科、杨杰等人对苏联表现出超越实际的幻想:力图说服苏联与中国结盟,参加对日作战。对此,身为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却大不以为然。一年多的驻苏经历使他对苏联国内形势和外交立场有了更多了解:“(1)苏联的内部情况不宜与中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日。(2)国内的食物供应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紧张的。(3)国内的军队虽然吃得不错,待遇也好,可是最近对军队的清洗和处决了八位高级将领,在全军造成了混乱影响。(4)斯大林还担心,任何对外战争,会意味着他的垮台。”基于这些了解,蒋廷黻对于苏联出兵参战深表怀疑。相反,他却更多地表现出对英美的期望,认为:“吾人绝不可期望苏联之实力助我,目前外交活动应注重英美之合作。”这显然是与国民政府转而注重苏联的外交政策相悖,让其继续留任势必影响中苏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蒋廷黻于1938年2月被国民政府调回国内,结束了他作为驻苏大使的外交生涯。
三、从学界到政界:作为学人外交典范的分析
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2月,这短短一年多的实任驻苏大使的经历,对于蒋廷黻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体验。
从客观上来说,当时苏联正值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运动的扩大化使国内政治空气异常紧张,这也必然影响到外交领域。尤其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差不多所有非
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们都有同感。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不断监视,行动也受限制。在莫斯科的生活,完全与在西欧任何大都市或新世界(指美国)不一样”。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蒋廷黻的前任——颜惠庆的辞职,也使刚到任的蒋廷黻感到困惑与不便。蒋廷黻就曾回忆说:“有一天,我去拜访他(时任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时,我发现在我们谈话时,他不停地用铅笔击打桌子,很像中国和尚敲木鱼念经。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有些不解,后来他告诉我这是防止苏联特务‘格别乌(GPU)录音和窃听的最好方法。”其实,蒋廷黻也处于同样的环境之中,“他(蒋廷黻)的办公室和住所遍置秘密的麦克风,一天廿四小时不能随便说一句话。他的行动随时受秘密警察监视,完全没有行动自由。他和别国大使谈话要预先安排跳舞会,在响亮的音乐声中由双方的太太传达信息。”尽管蒋廷黻深知自己“不是苏联特务的对手”,因此“对于苏联是否在中国大使馆布置录音、窃听设备问题不想去侦破”,但这种“不是人过的生活”对蒋廷黻驻苏期间的工作无疑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从主观上来说,蒋廷黻从一介沉心于学术的历史系教授出任驻外大使,本身就暗含着潜在的诸多困难。虽然蒋廷黻的外交史治学为其从事的外交活动提供了相关知识背景,对他国的认识亦多洞见,但史学与外交毕竟殊途异归,不属于同等范畴。对外交史的熟稔并不意味着在外交实际操作上的规范——就西安事变与苏联交涉中的盲目与冲动就是显而易见的实例。对于外交经验的缺乏,初到苏联的蒋廷黻亦有自知之明,在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谈时他曾表示:自己“原无外交经验。此次来贵国负此重大责任,心中颇以为在友邦初试比在他国更为便也。我国先哲孔子曾言:处异邦,言必忠信,行必笃敬。果如此,则万事顺利矣。我拟谨守我国先哲之言,以补经验之不足”。然而外交关系之微妙、运作之复杂,远非忠信笃敬就能解决问题,更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进行,这使得书生气十足的蒋廷黻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应变不及,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如西安事变交涉时,蒋廷黻明明知道苏方所获消息不准确,“李(李维诺夫)氏提及中国亲日派,余未及时纠正,可惜之至”。懊悔之余,蒋廷黻只能表示:“此后有机当迎头痛击此类谬论。”
尽管作为外交史家出使苏联,蒋廷黻并无出色的表现,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糟糕。但蒋廷黻跨越学界与政界的鸿沟,接受国民政府这一任命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符合。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国民政府被迫作出开放的政治姿态,吸纳大批教授、专家等知识分子到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对政府而言,此举在借助社会名流效应来“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国内各派别、各民族的凝聚力”的同时,还可以“扩大国际影响”。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则是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就如蒋廷黻,他“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我们可以说他的态度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
正是基于同样的想法,一些术业有专的学者毅然放弃多年研究而服从于整个国家的需要,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出任驻土耳其公使等。但这些学者与蒋廷黻郁郁不得志的驻苏外交生涯都有着意料之中的一致性,即受国内外环境尤其是自身外交素质的局限,在极为讲求技艺而非仅仅有热情就足够的外交面前,充满了挫折感与失败感。虽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尽心尽力的理想得以暂时有所寄托,然从整体上而言,他们所起的作用都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得不偿失——因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或放弃了原先擅长的学问。翁文灏对此有深刻体会:“余原治学术,因对日抗战而勉参中枢,诚意盼于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但迫于环境,实际结果辄违初愿,因此屡求隐退,追计从政时期因政界积习相因,动辄得咎,备尝艰苦,且深愧悔。”
除了学问上的损失,学人出任外交职务对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独立性也是一种损害。北洋时期外交官相对较为自由,“彼时似乎很少军人与巧宦愿意出任外交官,同时他们尚有自知之明,对于外交界也另眼相看,认为那是对外交涉,有关国体,而且在私人方面也无权利可争”。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方针的加强,党化政治与党派色彩亦对外交产生了相应影响,使国家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党之事,对驻外人员的政治身份也作了硬性规定,故一批学者不得不背离原先崇尚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加入国民党。以蒋廷黻为例,他被任命为驻苏大使时仍是无党派人士,当时即有劝其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均被其婉言拒绝。然上任不久,蒋介石又亲自去函,晓以利害:“入党与外交似无甚关系,但驻俄使节则关系较重,故中正意谓兄加入本党,于公于私皆得便利,而努力功效亦必增大”,并且还在信中“特附上入党志愿书数份,如兄同意,请填写寄回,介绍主盟人则由中正任之”。在这种情况下,蒋廷黻只得无可奈何地表示接受。因为他也意识到作为为国民政府服务的驻外人员,必须与国民党保持至少在表面上的一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一定的牺牲,承受一定的束缚,这也是同时代心系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却又不能摆脱的桎梏。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