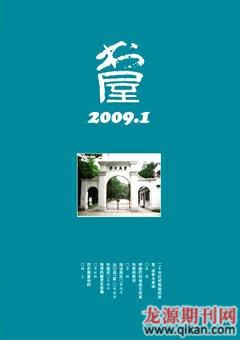可怜误记戴东原
田 吉
《清国史·儒林传》卷八中,我们找到了长沙人余廷灿的本传。交代余氏的生平行事之后,撰者重点介绍了他的学术成就:“其学兼综经史及诸子百家,象纬、勾股、律吕、音韵,皆能提要钩玄。尝与休宁戴震、河间纪昀相切劘。”对一名二流学者来说,这评价尚称公允。不过,文中特意拈出的余氏曾经和戴震、纪昀二人相与论学之事,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翻开他的《存吾文集》,确实可以看见和纪晓岚的书信往还,但同样是在集中的《戴东原先生事略》,余氏明明惋惜地追忆着戴震:“廷灿未识君面,而喜读君书,后君之死十有二年来京师,从士大夫之后,日闻君之学与君之人。恐久就坠逸,因叙次其事略,以待史馆采择焉。”看来,廷灿当日交接的只是纪晓岚,而对于自己崇拜的戴东原却一直无缘结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相切劘”了。
史官作传,总得有所依傍。这篇传记的来源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沅湘耆旧集》。集中第九十五卷有余氏小传,编辑者新化人邓显鹤是这样评论这位湖湘乡贤的:“先生学有本原,其论天文律历、勾股径围之学,与休宁戴氏东原往复辩难,具见《存吾文集》。”看起来邓显鹤似乎并未仔细阅读余氏文集,难怪杨树达先生后来给《存吾文集》撰写提要的时候,也批评显鹤此传“传闻误记,多与事实不合”。
“传闻误记”自然不假,可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位娴于学林掌故、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导师”的文献大家,偏偏“误记”了戴震呢?
乾嘉之际,朴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界的中心位置。一大批朴学大师以治经学发端,精研文字音韵、章句训诂,进而扩展到名物、典章、史地诸方面的考据,产生了不少可以传世的学术成果。流风所扇,后进翕然,学者们纷纷为故纸堆吸引,不惜焚膏继晷、皓首穷经。后人分别以惠栋、戴震为宗师,把当时众多的朴学家划作彬彬济美的吴、皖二派。不久,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也悄然兴起,足堪鼎峙于后。而作为一代朴学宗主,戴震无疑成为众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那个时代最耀眼的青年俊彦,大都选择了朴学,竞相以能踪迹戴氏为荣——连那位自视甚高的章学诚,也和桐城派大师姚鼐一般,年轻时都免不了要仰视东原。
然而,正当这股朴学潮流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时候,一向以“理学之乡”闻名的湖湘大地却如同被遗忘的角落,几乎未受影响。“湘士治学大都以宋儒义理之学为依归”,尽管刚才说到的余廷灿以及稍后的唐仲冕等人因为游宦京师而稍稍接闻戴氏学风,但直到道光年间,要在湖南找出那么一两位纯粹的朴学家竟是那么困难。这点已经为不少学者所注意,而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说法最具代表性:“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这不过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线性描述,章太炎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被他讽刺“不知小学”的“三王”,就有王夫之、王闿运两位湖湘学人。最直接的恐怕是那位狂放的李慈铭,当他读到郭嵩焘的《礼记质疑》时,竟然径直宣称:“湖南人总不知学问。”尽管《越缦堂日记》一直以好逞雌黄、睥睨当世而名,但如此“裸斥”,轻蔑之甚却也不多见。
当然,李慈铭是邓显鹤的晚辈,章、钱二位的评论,显鹤更没有机会看见。实际上在当时,朴学也处于上升阶段,内部的“学术谱系”尚来不及进行清晰地追溯,而偏居“山国荒僻之亚”的湖南,在类似于今天的“学术批评圈”中更没有占据什么耀眼角色。因此,我们不能贸然推断显鹤对余廷灿与戴震论学之事的“传闻误记”,就一定是因为受到外界讥刺“湘学不竞”而做出的有意借重。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认为:邓显鹤应该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在他看来,余廷灿能与当时的学界精英讨论辩难,应该算得上是余氏的机缘,也是湖南学人的光荣。
这种苦心孤诣,在当时的湖湘学界,也决非仅见邓显鹤一人。嘉庆末年,湖南布政使翁元圻开局重修省志,恰逢清廷国史馆也正在续纂《一统志》,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的陶澍急忙写信告诉在长沙志局的好友黄本骐:“此时馆中正在纂辑《儒林》、《文苑》列传,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入者寥寥。弟虽极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无凭据之故。是省志不可不早成送馆,以备采择也。”为了能在国家层面多见着一些湖南人的名字,陶不得不催促省志早日成书,其一心表彰湖湘先正之情可谓亟矣。
不过外界的批评确也不是空穴来风,乾嘉年间的湖南,毕竟真没有什么像样的朴学家——当然也不否认一些学人受湖外风气的影响。在《新化县志》中,就记载着一位学者的有趣事迹,他叫唐世倜,是邓显鹤的同乡好友,早岁“好学喜吟,为诗已裒然成集”,中年之后因向慕学术,又“为考据之学,不复措意声律”。而晚年作客桂林,“见同人社集,复理旧业”。一生徘徊辞章与考据之间,这样的尴尬状况,是否也透露出当年真实的湖南学风?
回响往往要在声音消失以后才出现。咸丰以后,作为一种学术潮流,朴学逐渐衰落。但作为一种评价标尺,是否精于小学、长于考据却几乎成了学与不学的惟一标准。这么看来,尽管培育过屈原、周敦颐二位巨子、有着悠久辞章与理学传统的湖湘大地在其他方面不乏济济楚材,但对不起,偏偏少了些朴学人士,他李慈铭就有足够的理由鄙夷整个湖南。邓显鹤以后的湖南学者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是那位让李慈铭大发感慨的郭嵩焘,便自觉承认湖南“衣冠之盛,文章学问之流传,不逮吴越远甚”(《罗研生七十寿序》)。在他看来,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罗研生墓志铭》)。王先谦在编纂《皇清经解续编》时,也认为“江皖耆彦,学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到后来,湖南人对乡先贤朴学不昌的尴尬似乎越发敏感,心理紧张感也日渐增强。《湘学略》的作者李肖聃就曾这样惋惜:“假令砚仙(龙璋)生承平时,与王、段诸公为友,讲明字例之条,湖南文字之学,不如是之未昌也。”(《星庐笔记》)
但是,比其他地方慢了半拍之后,湖南的朴学很快昌盛起来了。在道光年间邓显鹤、黄本骥等人的提倡下,中经邹汉勋、何绍基,直到清末的阎镇珩、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尽管他不是很愿意承认自己的湘人身份),一时间湖湘英才纷纭,俨然不让吴越。进入民国,新学竞爽,朴学失却了那最后的光芒,日渐式微,但就在此时,往日没有被人家看得上眼的洞庭之南,却诞生了杨树达、曾运乾、余嘉锡、马宗霍、骆鸿凯、张舜徽等一大批朴学精英。历史的循环,让冷眼旁观者难免唏嘘不已。
可就算如此,这些湖湘学人仍然在为乡先辈们感到遗憾。作为近代以来湘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杨树达和张舜徽的态度大概可以略窥消息。
杨氏不乏对湖南朴学历史的清醒认识。1934年10月27日,杨树达在日记里记载:“读唐仲冕《陶山文录》。陶山之学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前辈能了解汉学者仅陶山及余存吾廷灿两人耳。”在《存吾文集》的提要中,他也感叹:“乾嘉之际,其时汉学风靡一世,而湖湘学子大都犹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而因为章太炎“不通小学”的讽刺,早年的杨树达与曾运乾(星笠)甚至订立过“雪耻之盟”:“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日后杨、曾二位步入中年,学问文章,海内推服,所雪之耻自然不止“不通小学”了。晚年的杨树达,还因为《积微居小说述林》出版的时候有人指责自己沿用乾嘉诸儒“常用之方法”,而特意总结出自己超出乾嘉朴学家的五个方面。学术自信心逐渐建立以后,他对来自朴学之邦的评判就有了自己的看法。浙江人张孟劬曾经这样评价杨树达和余嘉锡:“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揄扬背后掩藏不住赤裸裸的地域偏见和文化歧视,杨树达难免未惬于心:你张孟劬的文化优越感也太强了,先别说我杨某的学问,像余嘉锡这样独步天下的目录版本学,江浙人士哪能做到?爱乡之情,自得之意,均不难想见。不过对于张氏批评魏源和王先谦的“芜杂”和“乡气”,杨树达好像并未否认。
无独有偶,张舜徽在评价乾嘉之际的湘学时,也表达了与“乡气”近似的判断。本来当他看见李慈铭那句轻妄之言,自尊心也是大受伤害,借着撰写《清人笔记条辨》的机会,把李氏狠狠训斥了一番:“湘湖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为重轻,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褊狭亦已甚矣。”酣畅淋漓,令人神为之旺。但当读到另一位乡贤黄本骥的著述之后,张舜徽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黄本骥“其诗与文,皆不免有村父子气”。同样使用“乡气”这个概念,这话从张舜徽的嘴里说出,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域外人士,颇有点切中湘学病根的味道。为此,他还不惜引用朱熹的话来作为印证:“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骋空言而远实课。”(《朱子文集·与曹晋叔书》)看起来,湘学之弊由来已久,李慈铭的轻侮,也不是全无依据。
和邓显鹤相比,杨树达和张舜徽当然更有资格评价湖南的朴学,也终于可以用更对等的态度与江浙学人往复辩难。不过正是透过杨、张二位,我们分明可以看见,邓显鹤曾经面临的心理压力,并没有随着湖南朴学的兴起而消弭。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至今高悬于岳麓书院的这副联语,道尽了湖南人的气魄。只不过,此联作者却是那位被李慈铭讥为“江湖唇吻之士”的王闿运,或许这正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