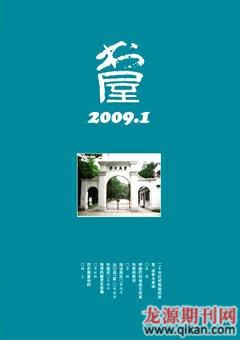闲话报应
雷池月
佛教传入中土两千年了,其中还经历了四到六世纪那样一段特殊兴盛的时期——南、北两朝都一度享有国教的尊荣,许多位君主虔诚向佛(最典型者如后秦的姚兴、梁朝的萧衍),到处摩崖造像,修庙开坛。总之,佛法西来时间不可谓不长,影响不可谓不大,然而历来大多数信众于深奥的教义却所知甚少,无论是闹市通衢,或者寻常巷陌,流播深远的大概只有报应轮回之说。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一个执著于现在的民族,向来不热衷于抽象思维,印度人在热带丛林的星光下冥思苦想出来的那一整套繁复而玄妙的道理,什么苦、集、灭、道四圣谛,什么五蕴皆空、诸法无我,什么十二因缘,善男信女们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大多是自己的现实诉求如何从神佛那里得到满足。于是,神圣的丛林成为各方利益交换的平台:政府靠出卖度牒牟利;僧众靠接受布施噉饭;信众则通过施舍和许愿(预期的施舍)来换取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需求。这种交易关系需要一种制约来规范,报应便成为贯穿这种规范的指导思想。
基督教义里也有报应一说,如托尔斯泰在《复活》的扉页上便引用了《马太福音》里那著名的句子:“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过轮回则完全是印度人的创造了。而由于报应和轮回被捆绑在一起,使它的含义在东西方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英文而言,报应主要有两个相对应的词:retribution和judgment。前者指一种应得的惩罚或赔偿,后者意为审判和裁决。“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是说上帝将为人们的诉求主持公道,而人们付出的报应则是向上帝赎罪。在这里,上帝只是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人们的言行作出裁断而分别给予奖惩,尽管《旧约》里的耶和华有时也很凶暴,但并没有用“六道轮回”等虚拟的恐怖来维系自己的权威。
佛教教义里的“六道轮回”本也不是为报应设定的,它的原意是说明不仅人生是苦,而且死后因为业因的不同,灵魂需要经过“六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牲道、阿修罗道、人间道、天上道)转生,除了登上极乐世界,总之是一片苦海。既然无论生死都是苦海茫茫横无涯际,那么,修行就是证涅槃、得解脱的唯一的自赎之路。修行的方法包括“戒、定、慧”三个层面,“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静缘曰定,破恶证真曰慧”,戒是第一步。所谓“戒”,目的是抵制人性各种本能的追求,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于是只能让戒律的条目不断增加,后来,竟达到和尚二百五十条、尼姑五百条之多。犯戒因情节不同分成若干类,接受波罗夷(即开除出教)、僧残(忏悔赎罪)、舍堕(没收财产兼入地狱)、单提(入地狱)等等惩罚。“六道轮回”在这里也就成了震慑教众的重要思想武器。报应也难免要纳入轮回这个理论框架里去,因为恐惧感总是推行任何教化必不可少的一件宝器。
但是,佛教的报应最初的用意并不是出于对恶的阻吓,而是指修行能获得的酬报。这种酬报不是指证涅磐、得解脱这类精神境界的到达,而是指近于世俗所理解的种种现实的好处,出家的叫神通,在家的叫福报。神通分五种,常人不可测,不去说它;福报则内容庞杂,概而言之,则无非来世和今生两类,两类所含则大体不外乎是富贵寿考、消灾灭祸的祈求及其印证。向寺庙施舍是得到福报的原由,所以施舍也叫种福田,因为可以收获福报。但是光有福报,凝聚力固然有了,却不够牢固,于是还必须有恶报,用以惩罚那些背离信条甚至肆意作恶的人。不过惩恶并不是印度佛教教义中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对违反戒律的惩罚,虽然有些严厉,也是因为人欲的力量过于强大,不如此不足以维护僧尼队伍的纯洁性,而且还留有宽容的余地——实在受不住了,可以放弃,只要宣布一声,你就可以脱离佛门,不必再受戒律的束缚。这说明佛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洞察和谅解。
只有在中国,在大乘佛教的宣传里,报应的惩戒功能才被发挥到了极致。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的应该有如下这几条:
一,历史上任何文化的传播,距离和影响力总是呈一种反相关,就是说,距离愈远,影响力愈弱。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因为本地和尚念的经文本是来自外面,在不同的语言和社会环境里,一再的转述难免会让经文走样,把经念歪了的情况不可避免。佛教自东汉时传入后,发展很快,到了北魏,天下僧尼竟达百万之众(“南朝四百八十寺”,也差不到哪里去),可是这时翻译过来的经书很少,而且多是印度人自己操刀(最著名的如四世纪初的鸠摩罗什),其于汉语难免有许多不甚了然之处,抓耳挠腮之余往往便用音译。这种译经不经译者亲自解释,别人只能是如读天书,不知所云。所以那百万之众究竟有几人理解佛法真谛确实是个问题,而灌输起来方便,接受也比较简易的,无过于报应轮回那套理论,僧徒们很快心领神会,还能“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并以此影响和凝聚广大的善男信女。全国各地许多反映这种内容的造型艺术(重庆大足最为典型),充分证明大乘佛教曾经在教义宣传上的这种片面性,而教义的引进滞后,是“念歪了经”的根本原因。
二,我们的民族缺乏思辨的传统,从来不习惯于对抽象命题(如彼岸、终极目的之类)作抽丝剥茧式的深思冥想,只执著于眼前的“有”,对于同一时间的另一个空间,主流意识是不承认的,即便对有些说不清的事物,如鬼、神之类,也是取“敬而远之”、“祭如在”这种含混的态度。从老庄到东汉的玄学直至后来的禅宗,表面看来都有若干追求思辨的成分,但实际上多数只反映了一些对生活方式或者生存态度的探索。特别是后来成为大乘佛教主流的禅宗,慧能因为不能忍受佛教修行需要面对的重复而繁琐的思考,提出了“顿悟”的主张。“心即是佛”,何其简单明了!而且这一命题完全不能证伪——谁能认识别人心中的佛?现在有些半吊子文人、艺人爱作高深状,侈谈什么“禅意”、“禅境”,究竟内容如何,谁能说得清楚?一部《五灯会元》,大师们的机锋越没有逻辑就越显示出意味无穷,然而细究起来,终归是一堆昏话。
上述这种背景正是报应轮回之说得以深入人心的前提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通了佛性的大师,不需要这么多大师,芸芸众生也不向往做大师,他们只是施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座用布施来交换福祉的平台。对他们,只要说清楚报应的道理就够了。然而证明这一理论的实例却实在是太少了,当然,首先可以多宣传来世报,这是无法验证因而不需要兑现的,但现世报终归是最有效的教材,可惜出现的机率太低。照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到头终须报,报应率太低一定会引起信仰的动摇,这无疑需要从理论上补漏:“有心为善,虽善不奖;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说法想必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下子就把相当数量的应有的报应化解了。当然,仅有消极地回避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典型事例,运用必要的包装手段,进行正面教育。
三,正面教育需要现世报的教材,但很少,怎么办?除了尽可能地敏锐地抓住一切可利用的线索,夸张渲染,进行加工外,只有依靠传法的导师们运用自己的“神通”,制造一些报应的奇迹。那些在新区从事开辟工作的传教者们,往往都善于用神秘主义的外衣包装自己,事实上,他们如果没有两手过硬的绝招,根本就不可能打开局面,更别说取得上至国王下至百姓崇奉如神明一般的地位。四世纪时后赵的佛图澄最具典型性,他能知过去未来,断吉凶祸福,无不灵验,暴戾成性的两代国君石勒、石虎叔侄都尊他为国师,无计不从。从有关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佛图澄“神通”之广大简直令人骇然(他不时可以在河边把自己的内脏掏出来清洗),其他还有一些大师也具有种种惊人的法力,后来历史上有那么多善恶报应的故事,不少应该就是他们亲手炮制或者由一言九鼎的他们所转述。
四,中国的俗文化在因果报应的宣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小说体裁的作品——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里,就已经有了结草衔环这类报应题材的记载。但中国俗文学的发展是宋代市民社会兴起以后的事。宋初成书的《太平广记》是此前各朝各类小说和传奇故事的总汇,而且也是此后数百年戏剧、曲艺和说部创作的题材库。《太平广记》原书约三百万字,明代以前只有传抄本,明嘉靖时刻印出版,但因卷帙浩繁,仍是流播不广,明末冯梦龙把它整理缩写成《太平广记钞》,从此影响越来越大。《太平广记钞》里专门记载报应故事的内容虽然只有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共一百多则,但另外散见于其他各卷的因果报应异闻,总数远过于此。这些故事不少就是佛教僧众创作和传播的。明朝中后期是俗文学迅猛发展的时段,冯梦龙和凌濛初编著的“三言二拍”,其中多数故事都贯穿了因果报应的指导思想,罗贯中和施耐庵的大部头长篇里也多处穿插着因果报应的情节。这证明此时报应轮回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于文盲所占比例太高,广大底层民众接受这种影响并非通过阅读,而主要是来自对戏剧、曲艺、传说以及民俗等形式的耳濡目染。中国戏曲的形态,长期以来虽然失之简陋,但在民间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几百年来它用因果报应来进行伦理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居功至伟。剧目名称直接标明一个“报”字,就有《奇冤报》、《天雷报》、《杀子报》等,不胜枚举。
不过,因果报应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并不能完全归诸佛教的作用。因为:
第一,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便有了因果报应的故事流传。举一个例——春秋时郑庄公手下的大将子都和颍考叔(就是那位化解了庄公母子矛盾的著名孝子)奉命出征,子都为了独享胜利的功劳,竟用暗箭射杀了颍考叔。回朝后在庄公举行的庆功宴上,子都突发狂症,谓颍考叔鬼魂前来索命,最终自残而死。幼时看过名伶李万春演的《伐子都》,报应这一段特别精彩,硬靠高靴,从三张台子上翻下来,白净的脸上(子都是著名的美男子)一眨眼就布满黑油烟,最后“硬僵尸”倒地而死,那功夫当真了得——这故事的流传早于佛教的传入至少五百年,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第二,国人自创的宗教——道教的出现虽然略晚于佛教的西来,但它有着更广泛更详尽的异度空间的设计——依据人间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安排了天堂和地狱世界的统治秩序,而为了完成儆世济人推行教义的目的,当然需要准备许多由报应来承载的正面和反面的教材。总体上说,道教的影响不如佛教大,除了宋、明两个朝代的某些时段——如宋真宗、宋徽宗、明世宗这几位笃信道教的皇帝在位时期外,道教只能扮演千年老二的角色,但是它有主场优势,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贴得更紧,鬼神世界的表述也更为精细和生动,于是,千百年来,它对于国人报应观念的形成,作用也是巨大的,甚至更为具体。
第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从理论上说,虽然从来不承认、不宣传异度空间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却不能不虚拟了一个一切是非标准的最高裁断者——天,天是具有惩罚意志的,于是便有了“畏天命”,便也有了“敬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正说明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既然妥协了,也就承认了鬼神是可以代表天意来施行惩罚的。报应之说自然也顺理成章了。不过儒家在这点上始终有些羞羞答答,为了掩盖这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常常找些其他的借口,就像清代的一位大儒,家里办丧事,请了僧道两众大做水陆道场,为了消解他人的质疑和自己内心的矛盾,特意写了如下一幅联语:读儒书不信佛教;奉母命权做道场。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软弱态度,报应的观念当然会更加深入人心了。
而且,儒家时常也有意识地宣传报应之说。不过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它的指向往往着眼于一些所谓“宏大叙事”,即时代风云和庙廊事业这类题目。举个例子: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李世民屠兄杀弟的行为时说道:
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以仪刑也,彼中(宗)、明(皇)、肃(宗)、代(宗)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意思是说,开国的君主干下了罪恶的勾当,难免会成为后世子孙仿效的榜样——英明神武的先人做得,我如何便做不得?于是有唐一代,皇室子孙互相杀戮的惨剧没完没了。从这里,人们自然会得出报应的结论:哪怕你是一代英主的李世民,欠下了骨肉相残的孽债,终归要由你的子孙也用骨肉相残来清偿。
再举一个例子。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赵光义继承哥哥赵匡胤帝位的合法性,不断提出过质疑,以当时的情况看,不是“弑”,也是“篡”,尤其不堪的是还要逼死并无野心的亲侄儿,实在太狠了点!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后来赵普弄出来的那个“金匮密约”(记载了赵匡胤向母亲杜太后作出的由弟弟接班的承诺)。明人笔记中就有人指出过赵光义是受到了报应的——他的儿子赵恒(真宗)、孙子赵祯(仁宗)、曾孙赵曙(英宗)都是精神病患者,都曾或一度“昏聩不能理事”,或“呼号奔走于朝堂之上”,完全没有盛世明君的气象。这还不算,仁宗是独子,而他本人竟连独子也未留下一个,子息之弱,可以想见。到了钦宗被俘以后,继位的弟弟高宗又断了后。他的昭慈皇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于是选养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即后来的孝宗),帝统又回到了太祖一系。昭慈皇后做的梦想必是鬼神索债之类,一做再做,情节一定比较恐怖,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能让高宗大悟。所谓大悟,无非是明白了这些年来国运不昌是因为自己的先人欠下的历史债务没有偿还,于是最后作出了这样一个清偿宿债的决定。
所以,报应观念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释、道、儒三家是各有其贡献的。当然贡献有大小,但宣传的方向基本一致,只是内容各有侧重。
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转型,伴随着革命的威权,进行了全民的意识形态大清洗。积数十年之功,多数传统观念可谓荡涤无余,但意识深处的报应观念,却有些难以撼动,而且竟有与时俱进之妙,使人们在行恶的诱惑面前有所自敛,从而起到了若干维护社会纲常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大概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生活中有太多因为政治斗争而带来的个人或群体命运的反复变化,地位、权力、财产的状况往往一夜之间判若云泥,虽然对此通常伴有许多说辞,但那些大块文章于一般人未必有用,对很多情况的认识,人们内心深处实际上只能以报应来概括其中的因果关系。“三大改造”时候的事就无须说了,自1957年反右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二十年间,运动持续不断,间距越来越短,手段越来越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使用肉刑以至于滥杀无辜,在在可见,直到1973年,通过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批示,才把这种情况控制下来。每次运动新上来的人一般都必然有整人的记录,当然也难免要被后面上来的人整,整人的,被整的,看整的,都会不时地从心底冒出两个字:报应!
报应的共识不独只存在于一般群众,大人物者也在所不免,当然须是在吃过斗争的苦头以后。林彪葬身大漠,举国骇然,当时便有老帅吟诵出那遐迩尽知的偈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齐都报。
有“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之慨的开国元戎,自然是久经考验的无神论者,此时此刻,也只能以“报应”论时事,足见这两个字的言简意赅和深入人心。
康生蛇蝎小人,狠愎有过于张汤,虽然结怨甚众,但却能得善终,而且丧事可谓备极哀荣(在他之前,共和国历史上还无人享受过如此盛大的葬礼),很多人当然不服,于是便有了他死前为怪病所缠的种种流言,拨乱反正以后,甚至还有人写了小说,描写他剧烈头痛反复发作时,总会见到众冤魂前来索命,惟妙惟肖,动人心魄。这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让康生受到些活报应,不能太便宜他了。小说的情节有无根据并不重要,它只是反映国人对报应的向往和祈求。
“虺蜴为心”、“窥窃神器”的江青,因为“地实寒微”的自卑竟导致肆意整人的恶毒,出招奇狠,血债无数。审判庭上,听到一声“判处死刑”,吓得失了方寸,像阿Q一样喊起口号来,再听到“缓期执行”,才恢复常态不吱声了——可见她怕死。然而几年以后,她却选择了自杀。一贯高唱“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最后竟寻死,想必是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何以会崩溃?不得其详。但不外乎是精神的重负超越了她的承受能力,因为他晚年的生活条件并不差,是绝望还是愧疚,并不重要,反正自杀是一种横死,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在她和她的走卒手下惨遭横死的冤魂。
二,一些自然现象的巧合被有意识地集中起来并加以放大,造成了人们迷信报应的效果。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地都能听到一些传闻,说某某人在批斗会上因为殴打了自己的父母亲长,事后或遭到雷击,或突发暴病,或意外毙命等等。此类传闻往往事出有因,所以虽然纯属巧合,当局也很难作为谣言来追查。即使在高压下,人们不敢任意传播,但内心却不免深受其影响。
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突发精神病者比较多见,我也曾亲见过两起。白天斗人火力极猛,到半夜里,突然就疯了,或狂呼乱叫,或作极力申辩状,语句则含糊不可辨。很明显,这是本身精神压力超过其负荷极限的表现,本不足怪,但很难不让人往报应方面联想。
人之寿夭,各有宿命,所谓“修短固天”,实在有很多偶然因素。而这些偶然有时却构成或被人归结为一种规律,进而与报应的观念挂起钩来。几年前在深圳,一位四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请我吃饭,彼此感慨岁月沧桑之余,她说起当年同班三十人中,已死去五人,而其中四人都是反右中涌现的左派打手,得的病也很怪,什么骨癌、脑瘤这一类的,死前颇为痛苦。她说:“我当时不懂政治,只是觉得都是同学,何必那么凶狠?某某(已故的打手之一)后来可威风啦,毕业分配时,他叉着腰在讲台上训话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简直把同学当作自己的奴仆一样。他死得最早,我看就是报应。”我对她的话只是报之一笑,因为我不相信报应,道理很简单:这类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和报应挂得起钩的实在太少,而生活中的丑恶和残忍又太多,两者间根本不成比例。
说来说去,报应只是一种迷信。人们对它念念不忘,并时时把祈求的目光投向它,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有许多是非善恶没有得到公平的清算。就说“文革”吧,非正常死亡的人那么多,每一个死者都是他家人心头永远的彻骨的痛,而造成这些悲剧的大小元凶们又查处了多少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清理三种人”,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乘运动之机想抢班夺权的大小野心家,他们得罪的是下台又上台的当权者,当然难逃惩罚,至于一般群众,特别是那些不断被各路豪强用来开刀祭旗的二十九种人及其家属,他们无辜被残害甚至虐杀,凶手有几人被追究治罪了呢?一句话:“历史宜粗不宜细,朝前看。”就算完事了。八十年代前期的“整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还曾代人向省里领导这项工作的办事机构递交过材料,揭发一个现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期间的包括逼死人命在内的种种罪行。经手者开始的态度很好,过了些日子便慢慢凉下来,最终不了了之。大概是那位副部长已经找到了得力的保护者。事实上,那次整党很大程度上是走了过场,后来还搞了个“回头看”,下面干部的评价是:“回头一看,一片皇冠(日本车品牌,当时正是纷纷以“皇冠”取代原来的“上海”、“伏尔加”的高峰期)!”由此也可想见其效果。
到了九十年代,又有人提出过“清算”的话题。北京作家毛志成教授发表文章《谁干的?》,他提出的问题是:在那段恐怖的岁月里,所有骇人听闻的暴行究竟是些什么人干的?这些凶手们是否应该追究罪责?他认为应至少作出明确的结论让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后人也能从中获得教益——至少多一份判断是非荣辱的参照。毛先生的文章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响,有点像巴金老人建纪念馆的呼吁一样,在市场经济的热风中蒸发了,消失了。前些日子,读到黄裳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至于“文革”的遗老遗少们,听了样板戏,想起失去的好日子,会黯然神伤,或手舞足蹈,都说不定。
这里视文革为“好日子”的“遗老遗少”,当然都是大小恶棍一流,他们真的已经“为失去的一切黯然神伤”了吗?未必!那只是黄裳先生的一厢情愿吧。事实上,其中不少人眼下的日子远比“文革”时滋润得多,如果你细心去了解一下,许多脑满肠肥、颐指气使的“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文革”期间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应该能回答毛先生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谁干的”这类问题没有什么兴趣,当然前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并不甚了然,因而也就谈不上对报应与否的关心。整整一代新人,不再把与报应有关的思考放在心上,这应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吧,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肯定也是大有裨益的。不过细想起来,似乎也还是有几点可虑之处。
第一,千百年来,我们是一个信仰资源稀缺的民族,而仅凭儒家的的道德说教,不足以防堵来自人性恶的诱惑和驱动,于是报应之说便一直在守护社会伦理底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某些人有干坏事的冲动,却不敢干,怕报应。在社会关系相对松散的时代,这往往比法制还管用。当市场经济向我们展示了它污秽的另一面时,在唯利是图带来的寡廉鲜耻甚至伤天害理现象面前,是否该想一想,为了实现理想的和谐,便放弃了对恶行的报应,任由时间河流去稀释和冲刷有关的记忆,那后果,是否合算?
第二,“朝前看”,这话当然很对,但同时也还必须朝后看,因为只有朝后看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得到前进与发展的。何况,许多是非利害要靠后人才能完全认识清楚。所以,对前人所受的委屈和苦难,后人有责任为他们伸张正义,同样,对于前人的恶行、暴行和罪行,后人也应该为他们定性定罪,让他们的耻辱永远成为后世的教训。过去为前朝修史的史家们都是很注意恪守这一原则的。
第三,大家都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错了,所以要着手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似乎就不要再翻历史老账了。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阶层(劳与资、贫与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是无法绝对回避的,而且,如果不汲取以往的教训,则矛盾和冲突不断累积必然又会导致极端化的结果。极端化的思想和行为,难道还没有让我们的民族吃够苦头吗?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民生第一,让群众分享改革成果,这些都是痛定思痛的心得,很好!只是还需要明确地总结恶有恶报的反面教材,才有利于在人们心中培植更多的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