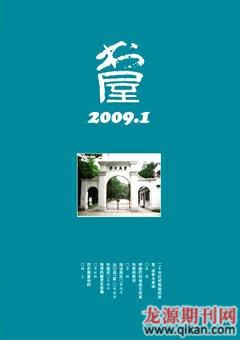出口成“脏”
陈漱渝
什么叫脏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大体而言,“脏话”是相对于“净语”的一个概念,多指羞辱、诅咒对方,以及涉及秽物、性行为或和人体器官的语汇。不过,对“脏”与“净”的看法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比如女性性器官常被当成脏字骂人,因为它除了具有隐蔽性之外,在男性视角中它还可能成为欺骗或背叛行为的发生地;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它既是生理发泄之处,同时又被视为秽物。但在十三世纪的英国,它却被视为寻常物。比如1223年英国伦敦有一条街道竟以它命名,甚至在这个名词之前还加一个动词“摸”(Gropecuntlane)。这件事见诸文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脏话文化史》,作者为露丝·韦津利。同一书还举例说,在《圣经》时代,拿国王的睾丸来宣誓忠诚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又说,胡须在伊拉克文化中占有神圣的位置,所以2003年在一次阿拉伯高层会议上伊拉克代表用“胡须”来诅咒科威特外交官。这些都说明对于“肮”与“不脏”,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关于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古老描绘见诸《易经》。今人多不识古文字,以及某些古文字意义的转化,并不将其划入脏话的范畴。比如“运转乾坤”,今天多用于表达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但在《易经》中,乾坤两卦明明是两性生殖器的符号。八卦的根底,即古代生殖崇拜的遗风。《周易》中的“云行雨施”,即古代性行为的术语。至于“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咸其訆”、“咸其辅颊舌”,更把性行为的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一般读者并不以为污染耳目,只有像潘光旦这样博学的人类学家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
在一定条件下,脏话的含义还可以淡化或转化。比如号称中国国骂的“他妈的”,原由五个字合成——前面有一个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名词,借破坏对方母亲的贞操侮辱、激怒对方,而使谩骂者一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它由五个字压缩为三个字和两个字的骂语之后,其攻击性逐渐淡化,有时化为了口头禅和感叹词。在特定场合,这个脏词骂语还能转化为一种爱称。中国现代对脏字有独到研究的鲁迅在他的著名杂文《论“他妈的”!》中举例说:“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不要吃。妈的你去吃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流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出口成章,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文化境界。即使有些妙笔生花的文人,口头表达能力也未必能跟他的书面表达能力相称。但“出口成脏”却是一件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尤其对于男权社会的男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动过粗口。蒋介石的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就是浙江的骂人话“娘希匹”,当代观众已经在有关电影和电视剧中聆听过了。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结句为“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也成为中华诗词史上的一种壮举。毛泽东说过,中国古代圣人是孔子,现代圣人是鲁迅。但这两位圣人也都动过粗口。孔老夫子删削的《诗经》,其中的不少篇什就是当时的猥亵歌谣,其中保存着赤裸裸的性语汇。孔夫子还把自己那位“利口辩辞“的弟子宰予骂作“朽木“和“粪土”。鲁迅是严词反对辱骂和恐吓的作家。但作为一个不但有七情六欲,而且爱憎之情特别强烈的人,鲁迅的私人信件中多次出现过骂人话,比如致钱玄同信中,骂刘师培计划创办的《国故》月刊是“坏种”办“屁志”,在致许寿裳等亲友信中还使用过“仰东石杀”或“娘东石杀”这类浙东流行的骂人秽语,其侮辱性远远超过了绍兴的常用骂语“小娘生”和“贱胎”。
外国名人也有爱骂人的。据说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就有骂脏话的习惯。他的太太不堪忍受,终于有一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一大串脏话掷向丈夫,借此让丈夫知道她平时是如何痛苦。不料马克·吐温彬彬有礼地聆听之后,淡淡地对妻子说:“亲爱的”,虽然你用词都正确,但语调有些走样。令妻子啼笑皆非。行文至此,又读到一则新华社专电,说1997年英国女王的丈夫因首相府插手戴安娜王妃的丧事,出“粗口”呵斥首相府的工作人员,此时女王在旁,对丈夫的做法露赞美之色。可见在讲绅士风度的英国,尊贵如女王丈夫者在情不可遏之时也用脏话伤人。
脏话既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自然也会成为文学作品——包括经典名著中的常客。不但中国的《诗经》、《易经》中有所谓脏话,《圣经》“雅歌”中并不雅驯的内容也颇不少。西方的文学名著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因有脏字被检方控为“有伤风化”。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有脏话一度被禁,作者也被送上了法庭。外文跟中文一样,也有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Congress”,普遍的字义是“国会”,但亦含性行为之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就有一些这样的双关语,被选作教材时,常常在课堂上引起学生的窃笑。近些年来,为了纠正神化英雄人物的倾向,中国的“红色经典”中常借助脏话表现人物的人性和个性。比如优秀电视剧《亮剑》、《狼毒花》中的主人公,都是名副其实的“出口成脏”。这是否会给中国的观众造成“听觉污染”,颇值得作家认真考虑。还是鲁迅说得好:“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
在文明社会,当然不会放纵不文明的脏话肆意泛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标榜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其中并不包括诽谤、中伤和随意骂脏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英文俚语与非传统用词辞典》因为收入了脏话,在图书馆一直被控制使用,只有事先办理特别申请手续才能借阅。2003年12月,美国摇滚明星波诺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出“粗口”,引起了舆论的谴责。加州议员道格·欧瑟特为此提出了一个名为《广播电视清洁法》的议案,要求禁掉八个脏字,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瞩目。
不过也有人对脏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男人骂脏话跟女人哭泣一样,能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人认为使用口语暴力,有时可以缓解乃至避免肢体暴力,压抑肢体的攻击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对脏话的正面效应不宜估计过高,它至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吐一时之快。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两军对垒,主将照例先对骂一番,然后开打,恰如斗蟋蟀,先要撩拨它的触须一样。在这种场合,语言暴力就不是肢体暴力的缓冲器,而是催化剂。用脏话以恶制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2008年秋天,在北京松榆里社区某一栋楼内,贴出了一张“脏话公告”,臭骂一周三次在楼道内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公告”下方注明:“谁撕就是谁干的!”因为不愿背黑锅,无人敢揭这张“公告”。结果由居委会出面,表示要调查处理行为不文明者,同时批评“公告”作者对居民造成“视觉污染”,表示一旦查明,也要追究作者的行为负责。
作为脏话的清洁剂是委婉语。如果说脏话把语言带进了阴沟,那么委婉语就可能将脏话带出阴沟。比如用“排泄物”代替屎尿,用“例假”“大姨妈”代替月经,用“胸”代替乳,用“下部”代替阴部。最有意思的是上厕所,一般场合称之为“去一号”,“去洗手间”,“去卫生间”,“去化妆间”。我在韩国餐厅如厕,看门前挂有卷帘,上书“解忧处”三字,顿时感到这个排泄秽物的场所诗意盎然。有人还告诉我,台湾有一个地方的男厕称为“听雨轩”,女厕称为“观瀑楼”,那就更显雅致。当然,还应配有其他图案作为标志,如在“听雨轩”画上烟斗或礼帽,在“观瀑楼”画上高跟鞋或红嘴唇,否则误入“白虎节堂”,势必会引起误会,产生尴尬。用委婉替代脏话固然可取,但也不能走向极端。1926年10月2日,周作人在《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发表《违碍字样》,批评出版界对“违碍字样”的删削和不必要的避讳。比如,由于神经过敏,连“子宫”都不敢写,避讳作“子X”,甚至创造出一个怪字(“子”旁加一“宫”字)作为替代。像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步入魔道了。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从古至今,既然脏话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文化现象,就有必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乃至进行跨文化研究,目的是了解脏话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个人原因以及遏制和消灭脏话的有效途径。1923年12月,周作人应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纪念增刊之约,撰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文中强调了该刊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脏话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鲁迅。他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指出,晋朝大重门第,子孙即使是酒囊饭袋,依靠祖先的余荫仍然可以得官,所以要攻击高门大族坚固的旧堡垒,就必然去瞄准他的血统。“他妈的”一类的脏话,便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产生的。当然,这只是鲁迅的一家之言,别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也还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脏话文化史》的作者也是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分析脏话产生的原因。该书认为,在战争中清一色男性环境,生理和心理压力极大,造成大量咒骂也就不足为奇。有一句世界广泛流行的骂人话,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传播开来的,因为对于处境险恶、离乡背井的美国大兵,有这个情绪字眼可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福气,尤其是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
窃以为,世界各国的脏话语多以母亲做标靶,是因为骂语必须有冒犯性,能犯禁忌,从而引起对方的震怒。在人世间母爱最为神圣,最为伟大。亵渎母亲就是亵渎神圣,因而最能侮辱对方的人格,伤害对方的感情。当然也有人把辱骂的对象上溯到祖母、外祖母甚至祖宗,或旁及到姨妈(如保加利亚语)、姐妹、小舅子。这类脏话肯定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在有些场合,脏话骂语也施之于物。比如不小心碰了头,恼怒之时脱口就是一句脏话,这时只是一种本能的宣泄,没有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内涵,就如同打嗝和生理排放一样。
在当代中国,脏话泛滥成灾是发生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国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文献。一时间,“他妈的”、“放他妈的屁”、“造他妈的反”一类豪言壮语充斥于大街小巷。我当时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曾奉工宣队之命撰写一篇批判“走资派”的稿子。送审之后,工宣队找我谈话,认为稿子毫无战斗性,辜负了组织期望。结果我被迫在一篇千字文中加入了五至十句“国骂”,才最终获得通过。我的这一亲身经历说明,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时代,骂脏话就等同于革命。人性的扭曲、语言的扭曲竟到如此地步,实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这也证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总的说来,骂脏话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用脏话骂人的方式并不可取。但骂可骂之人的可骂之处,跟骂不该骂之人的不该骂之处,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据已故贾植芳教授回忆,在1955年全国文联批判胡风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用五个字的“国骂”痛骂胡风。这件事散文家柳萌可以证实,相关文献也能证实(见王春瑜:《琐忆贾植芳》,《芳草地》2008年第4期,第65至66页)。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像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应该充分吸取的。
既然“出口成脏”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而发明脏话绝不可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发明者确是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鲁迅语)。有趣的是,竟还有人争夺脏话的发明权。这个人就是狂飙社的主将高长虹。为了拥有“他妈的”这三个字的知识产权,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锦袍的世界》里才初次使用。”查这篇作品,结尾确有“他妈的”三个字,不是具体骂某个人,而是骂爱国者反被人斥为卖国这种社会现象。《莽原》周刊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4月24日,而鲁迅的《论“他妈的!”》作于同年7月19日。高长虹的上述表白看来是要跟鲁迅争夺“他妈的”的发明权或首发权。但鲁迅讲得很清楚:“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关的口头禅。”可见“他妈的”这三个字早已有之,任何人想拥有这个词的专利都是办不到的。
消灭脏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人把骂人比喻为一种跟抽烟差不多的恶习。戒烟很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戒掉。一个人一辈子绝对不骂一句脏话也很难,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日趋和谐,文明用语的日趋普及,用脏话骂人的陋习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些年最壮观的骂人场面多出现在中国男足的赛场上。那万人齐骂“傻X”的声音,简直可以上遏行云,下断流水。但在今年北京的“两奥会”上,这种骂声已经绝迹,而代之以掌声、欢呼和加油声。外国运动员也报之以“谢谢北京”、“谢谢香港”、“谢谢青岛”、“谢谢中国”等热情友好的话语。可见经过提倡、引导,任何陋习都可以逐渐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