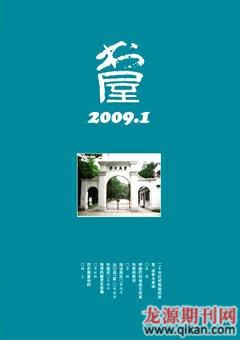职业、事业断想
樊百华
佛教说业不说职业。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宗教怎么肯定职业对人生的意义。其实,既然人首先必须吃喝,必须生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例如修行,那么,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也好,主持、方丈、教皇、牧师、喇嘛、班禅、活佛等等也罢,他们就都不仅是“先知”,也同时是一个社会角色,一个职业人。当然,各种职业对他人乃至人类的价值不同,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只是说,任何人都首先要设法活下来。传说释迦牟尼七天不吃不喝,终于修成了佛,但本可以继承王位的他成佛之后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很多底层人每天要做的:乞讨!不能说他的乞讨本身与乞丐的行为有何两样。
仅仅从“获得生存资源的活动”这一点谈论职业,那么,偷盗确实也是一种人类的职业。这样说很多人已经觉得大逆不道。我刚刚说过暂时不考虑职业的社会价值。国王与托钵僧的价值怎么比较,宁肯上十字架也不跟敌人角力(耶稣)与骁勇善战或者能征惯战(穆罕默德)如何评价,需要作另外的讨论。
我自己也常常脱口而出“事业如何如何”,彻底朴实地看,若是可持续谋生的就首先都是职业。为了与职业区分开来,我把事业定义为“一时或很长时间内难以换饭吃的活动”。这里面人们长期以来的一大流传看法是“窃国是事业,窃钩是罪业”。其实,皇帝、总统等等,其职业的最大特点,首先恐怕恰恰是“味道甚佳”。这样说来,窃国与窃钩本身都是“职业努力”。
近代以来,因为纳税人的“国家支持”或商人们的商业投资,求真的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谋利活动,事业的光环也愈益显露出职业的品格来。创造美的文学艺术活动越来越成为“自由职业”——职业是实话实说,自由则是说不需要遵守劳动纪律,没有组织规章的约束。
较为复杂的是“致善的活动”。教人向善在所有宗教团体那里曾经无不是神圣的事业。最突出的当然是中世纪。那时的教会,例如基督教的从教皇到牧师,是上帝与俗众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但是,他们的世俗生活或多或少都是由仆佣、助手伺候着的。俗众向教会纳税无不是神圣的义务,教会的各级教职无不为人们垂青。集权力、地位、荣耀、滋润于一身,真是不赖的职业呢!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政教合一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人生下来就入教了,但后来只有少数人甚至还是懵懂的孩子,就被选送到例如寺院,这对孩子所属的家庭(族)可是一大喜事。为什么?在我看来,这孩子一辈子都不需要种地放牧了,不用干最粗最脏最累的活儿了,尽管进入寺院还得尽义务,例如少林寺的小和尚还得干很多劳累的活儿,但总算跳出了农门,进了“事业机构”,靠了念经打坐、划拳劈腿,就能衣食无忧了。
所谓不劳者不得食,这里的“劳”当然指直接生产衣食的体力劳动,基本上落在经济学说的“第一产业”。真要是不劳者不得食,从古代的祭祀开始的事业,就都不可能出现了。可是,从来都是治人者尽享荣华富贵,而“治之要者,唯祀与戎”。所谓一张一弛的文武二术而已。于是,古往今来无不是嘴皮子、笔管子、刀把子、枪杆子,比起钉耙锄头来魅力四射、神采奕奕。
生存既然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人类的第一个秘密也就必定发生对于谋生活动的关联中。那就是:不是不劳者不得食,而是恰恰相反,不劳者得美食、先食。准确说,是不劳者如何通过种种手段赢得和分享到治权,而后把劳动者当成了自己的手足。
由此看人类的宗教,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一切宗教的操纵支配者们,无不是寄生的。真是很奇怪啊,寄生的靠着说教而赢得尊敬,而且人们不得不承认,说教者对人生万象的观与思、觉与悟,确实比芸芸众生要丰富深刻得太多。这好比中国传统的文人雅士,终身悠哉乐哉,吃香喝辣,但见识确实要比布衣农夫深广。去年我在研究安利“直销”与“传销”的异同时,看一本关于中国安利公司的书,那当中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地说道:“传教士传教时,无论对方相信与否,他总是不断地将福音传播出去,不会因有人不信而动摇他传播的意念。因此,做直销事业不要因为几位朋友不愿意加入就心灰意冷,应该学做传教士,执著坚持到底”〔1〕。这里我想顺便说到心理学:例如过去的中国,虽然长期没有心理学,但却有很丰富的勘察统驭人心的经验。人类的各类宗教操纵,尽管教义经籍中间没有任何心理学的探讨,但在宗教的操纵实践中,却有对人性人心的最精明的把握。
回到“治之要者,唯祀与戎”。既然这是统治社会的最高事实,那么,一旦社会摆脱了种种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羁绊,祭祀阶级(层)也就只能结束其实质的职业时代,而让信仰回到人们的业余生活。是的,是业余生活。我认为,所有的职业本身都没有信仰可言,因为——所有的职业都是谋生性的。宗教信仰有关于人生,但无关于谋生活动本身。正像原始巫术曾经是例如狩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实际上无用于狩猎,否则后来的狩猎就不会摒弃巫术了。
据说一些政教分离国家的现代基督教教会,已经从人们的“公共生活”剥离开去,就是说教会已经对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具有或软或硬的压力。信不信教、参不参加教会活动,纯属个人的“非职业偏好”。于是,教育、司法等公共领域,不再有教会的权威。不要说牧师不得进入学校的课堂传教,就是任何教师在课堂上力捧某一宗教,也有违法之嫌。教会还有,教职人员也还有,但都成为人们的无涉于权力结构的安排,而且越来越重叠于慈善事业。而慈善事业中的专职薪给人员当然是一种职业人,是非盈利慈善业基于效率与责任而必须做出的职业安排。
从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职业化。任何人都必须谋生而不可寄生,都必须有职业或者首先表现为一个职业人。在这里,人人都必须受制于凡胎肉身的纠缠,必须脱魅,而无法靠了神秘、魅力不受任何职业的羁绊。
尤其重要的是,例如教会的非职业性,只能出于公共安排;而其职业性历史遗留只能出于非公共性安排。这种安排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一团体或者某一政党作出的,而是民主宪政社会所有公民都负有参与责任的一种基本制度。
这使人们从一些新维度看到了“职业化社会”对“事业”的挤压——一切无效于实利的活动都必须“非职业化”,都不得成为获得谋生性回报的职业性手段。
有些社会不是这样的,大量的职业对人们的实利活动非但无效而且有害,但是却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公薪”人员。这样的社会在文明程度上,还处于宗教裁判所权力至上的中世纪。
职业化社会有高低阶段之分。高级的职业化社会,是人类的事业得到巩固持续的职业支撑的社会。例如科学研究当然是人类必须不断加强的事业,一个社会发达的标志首先就是科学研究有高度的自由、热情,人们对之有恰如其分的职业性支持;再如推动民主化转型当然是一些落后社会的极重大的事业,民主化运动之开展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职业支撑的程度。事业非职业,但有赖于职业社会真实真诚、自发自由、持续有力的支撑,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职业、事业相互涵养的好社会。
注释:
〔1〕时骅编著:《安利直销》,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