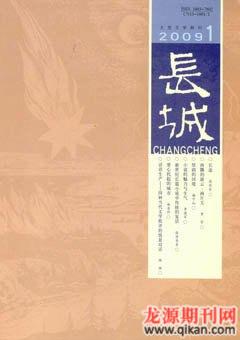致外祖母
顾 艳
一
时间在岁月的河流里快步如飞。我的外祖母1908年生于绍兴,1921年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28年10月,与同为绍兴人、刚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外祖父在上海结婚。我的母亲和姨妈、舅舅,还有我的两个哥哥全部出生在上海。我本来也该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因为父亲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落难,携着妻儿和岳母来到杭州定居。1962年冬天的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我在杭州浣纱路上的妇女保健院哇哇落地,成了我们家唯一出生在杭州的人。
我的十六岁仿佛就在眼前,可是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的我,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细嫩的皮肤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就像树枝上新鲜的红苹果。现在我闭上眼睛,让自己重新回到十六岁的时光里,我想起那一年秋天,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第一次面对死亡。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她的尸体挺在床上,脚后跟点燃着两支白蜡烛,这是照亮她归向漫漫黄土路上的长明灯。那些从上海赶来的舅舅、姨妈们轮流哭喊着,家里的哭声此起彼伏,然而我却没有流泪。因为没有流泪,舅舅、姨妈们认为我是一个不孝的外孙女。
她的墓地,在杭州半山区高高的山冈上。葬礼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深秋的落叶湿漉漉地散落在山坡上。我穿着新买的中统橡胶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紧跟着葬礼队伍。她落葬时,亲人们又一阵嚎陶大哭,而我却仍然没有眼泪。这真是大逆不道的事。我茫然地望着亲人们,相信他们的确比我对她更有感情。然而在她去世后的三十年间,我每年都会梦见她许多次,小时候的场景一幕一幕地在梦里闪现。在我们家逝去的四个祖辈中,只有她能走进我的梦。
前些天,我整理衣橱看见她的一件被洗得发白了的蓝色大襟衣衫,平平整整地压在衣橱最底层。这是她去世三十年后,唯一的遗物了。每次整理衣橱,我都舍不得把这件褂子扔掉。仿佛扔掉她的褂子,就是扔掉我整个童年的记忆。我的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她居住的东街路上的一个墙门里度过的。她和我们三兄妹,居住在这个墙门内一间十八平米的板壁屋子里。屋子的后门有一个大院子,种着元宝树、桑树、桂花树,还有一口井,是整个墙门十三户人家日常用水的来源。与这院子一墙之隔的,是一个电影院。只要竖起耳朵,电影中的对话和独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从小就是在听电影中长大的。十二三岁时,我能爬上一棵元宝树翻墙去蹭电影了。
在我记事那一天起,就知道她不喜欢我。家里吃饭,必须让两个哥哥先上桌,等他们吃饱吃好了,我才能吃。这是她定下的规矩,对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总是站在桌边馋涎欲滴地望着我的大哥和二哥狼吞虎咽,心里的自卑感慢慢滋长起来。那次大哥一边吃一边对我做着怪相说:“我们把肉吃光了,你没得吃,谁让你是女孩子?”这一刻我知道了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不能和两个哥哥一起上桌吃饭。我本能地对两个哥哥,有一种妒嫉和抵触心理。
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实在太饿了,见到桌上香喷喷的油煎黄鱼,我忍不住拿起筷子夹鱼,她看见后大叫:“不准动,你哥哥他们还没吃呢!”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先吃,我不能吃?我肚子饿。”她说:“这是规矩。”她说着就来夺我手中的筷子,我“哇哇”大哭,她还是没让我吃,只塞给我一只刀切馒头。
“我不要馒头。”我随手把馒头扔了。
“你还犟。”她火冒三丈地从灶房里拿来一根烧火柴,噼噼啪啪地打在我身上。自这一次挨打后,我虽然没敢再抢先上桌吃饭,但心里对她很记仇。
那时外祖父去台湾后,杳无音讯。她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很少有笑脸,也很少有开心的时光。自我出生后,她已经过着底层妇女的贫穷日子了。她靠我母亲每月给她的微薄生活费生活,舅舅和姨妈却从没有尽抚养他们母亲的责任和义务。每个月舅舅都会从上海坐火车来杭州,但从来就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她每月省吃俭用,就是为了把积蓄下的钱等舅舅来的那天烧一大锅红烧肉,买上几只罐头食品,让他吃了再打包带走。
每个月只要闻到红烧肉的香气,我就知道舅舅要来了。舅舅来了总是在我的小床上睡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走。那一夜我就和她睡一张五尺宽的雕花大床,那是她从前和外祖父的婚床。我洗完脚,早早地睡到雕花大床上,拘束地蜷缩到床的里头。她睡前有坐在床头抽烟的习惯,有时抽一支,有时抽二三支。由于经济条件差,她抽的全是最便宜的劣质烟。
我看她吞云吐雾,若有所思的样子,知道这是她劳累一天后最轻松的时光,也是我感到最温暖的时光。这时候她不会凶我,有时还会坐在床头一边腾云吐雾,一边给我讲一些她过去的好时光。
“像你这般大,我在绍兴是念私塾的。那时念私塾都是男孩子,我阿爸思想开通,把我也送去私塾念书。他见我读书好,又花钱把我送到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那可是有钱人读的学校,学的是英文呢!”
“你会英文?”
“怎么不会。英文和钢琴是我们的主要功课。”
“哦,太外公思想开通,可是你怎么不?”
“我什么不?”她脸一沉。
我没敢吭声,她说:“你倒说说,我什么不?”
“你重男轻女,不让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吃饭。”
“啪”地,她顺手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子道:“你说什么?你无法无天了,你。”我“呜呜”哭起来,觉得很委屈。舅舅过来劝架,她才消了气。我没敢哭得太响,钻进被窝抽泣着。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躺下睡着的,等我哭够了钻出头来,窗外一弯月芽儿正明晃晃地照在雕花大床上。我望着她熟睡时皱巴巴的脸,实在想象不出她少女时的模样。
这晚我是听着她的呼噜声,闻着她熟睡时呼吸的味道委屈地睡去的。
舅舅来杭州的那天下午,时常会领着我的大哥和二哥去儿童公园玩,买奶糖和巧克力给他们吃。大哥等舅舅一走,会告诉我:“我们昨天在儿童公园坐旋转滑梯,舅舅还买巧克力给我们吃,还有牛奶糖。”我听得既妒忌又向往。所以,每一次舅舅来我都眼巴巴地期待着,可总是失望。自然他是讨好她,她不喜欢女孩子他就不带。我对舅舅的记仇,就是在一次一次失望中积累起来的。
那个星期天下午,舅舅又要带着大哥二哥出门去玩了。大哥和二哥,穿着西式短裤和短袖,配着牛皮背带;大哥肩上还扛着舅舅的高级照相机。我又一次失望后,不顾一切地双脚双手护着大门,不让他们出去。然而,我的耍赖并没有达到目的。她冲我大喝一声,拉开了我。这时舅舅就像抛弃一条病狗一样,把我抛弃了。大哥朝我做怪相,二哥同情我说:“别难过,我们爬山,你爬不动的。”
等舅舅带着大哥二哥出门后,我趁她不注意溜回母亲家告状去了。这一年我九岁,知道朝着东街路笔直到底,过三个十字路,然后再左拐弯进一条弄堂,就可回到母亲家里。母亲家仿佛是我心中的灯塔和希望。我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走得满头大汗,可是母亲不在家。我失望地坐在家门口的地上等。天一点点黑了下来,我又累又饿,竟然坐在地上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外祖母家的小床上。
我没有见到母亲,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外祖母家。一起床,我生怕外祖母给我耳掴子,背起书包就往外跑。她在后边喊:“你个小讨债鬼,别跑。”她一边喊,一边追,很快把我拉回来,道:“洗脸,吃饭。”
这顿早餐是我有记忆来,吃到的最好一顿早餐:一杯牛奶,一块奶油蛋糕,还有一块巧克力。
二
外祖母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架美国旧钢琴,那是保持她原来身份的体面物品。家里再穷,她也必须让孩子们学钢琴。她先是让大哥二哥学,可他们三天新鲜过后,死活不肯学,她就找上了我。尽管我也不想学,但面对她随时能打到我身上的柴棒,只得乖乖地跟她学钢琴。她要求我每天练习两小时,不到时间不能溜。我就老老实实地守时,认认真真地练琴。一次我叮叮咚咚地弹出了好听的曲子,她很自豪地对邻居姨婆说:“我年轻时候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是洋人老师教我们学的钢琴呢!”姨婆说:“是吗?”她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笑容道:“洋人老师可严格了。”
姨婆是小脚,没有读过书,只因儿子被“改造”,媳妇远嫁别人,她就和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似乎与外祖母有些同病相怜的地方。姨婆和外祖母的床只一板之隔,有时两个老太婆在熄灯之后,会隔着板壁聊一会儿天。
“我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但我们乡下不作兴女孩读书,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嫁给一位教书先生。娘家知道婆家经济条件不怎么样,怕我嫁过去受苦,嫁妆就格外丰厚。有六床缎子被面的棉被,两只大樟木箱,八只红木雕花衣架,还有带镜子的梳妆台,红漆木盆,金属首饰盒……”
“你娘家条件真不错。”
“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跟着斯文的读书男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穷得连饭也吃不上,饿死了两个孩子,娘家也不管了。苦命哇!”
我竖着耳朵听,但没听完她们的对话,就哈欠连连地睡着了。
每天一放学,我必须和外祖母用一根扁担抬一只马桶,我在前,她在后,走十分钟路,去固定地点倒粪便。我们抬着马桶走街穿巷时,我特别喜欢东张西望看风景。有时走着走着,就走弯路了。她在后边喊:“别看斜眼,看什么看?你走到哪里去了?”我被她一吆喝,慌了神,扛在肩上的扁担就觉得格外重。那天路过一家小酒馆时,一个酒鬼跌跌撞撞地出来,撞翻了我们,粪便溅了满地,还溅到了我们身上。
路上的行人掩鼻而逃,外祖母没有骂酒鬼,却骂我道:“你怎么走路的,你好好走路,会被他撞翻吗?”我说:“是酒鬼不好,快让酒鬼赔我们马桶。”她说:“你错了,还赖别人?”我顶嘴道:“我没有错。”她就气急败坏地给了我一个耳掴子。我“哇哇”大哭着,管自己跑回家。半个多小时后,她拿着一根扁担和摔碎了的马桶回来了。
墙门里有个木匠,她用一只老母鸡的代价让木匠修马桶。木匠却不干,硬要再添上一包利群牌香烟,才能立等可取。她慷慨地说:“好吧!”然后转身让我去买烟,自己“喔喔喔”地捉老母鸡。她捉老母鸡时躬着腰,最醒目的就是膝盖上两个大补丁。她总是宁愿自己穿补丁裤子,吃青菜萝卜,也不会亏待邻居。
木匠也是个酒鬼,常常喝得烂醉倒在灶房门口的泥地里。每次见到他踉踉跄跄地倒下去,我就吓坏了。我不敢从他身边经过,而是回转身绕一个大圈子走后院回家。这次路过他门口,我突然觉得撞翻我们的,不就是这个酒鬼木匠吗?他刚才裹着件棉大袍,戴着顶棉帽子才没有让我认出他。我发现了这个秘密,转身跑回家告诉外祖母道:“你别给他老母鸡和烟,应该让他赔咱们一只新马桶,是他撞翻我们的。”
“你胡说什么?买烟去。”
“我没有胡说。”
“你还没胡说?你再敢胡说,小心你的脑袋。”
她恫吓我,我这才去买烟。我路过酒鬼木匠的家门口时,他正得意洋洋地做着木工活,见我道:“烟买来了吗?”
“买个屁。是你撞翻我们的,还向我们要老母鸡和烟?”
“嗨,你个小丫头,倒是比你外婆厉害。”
回到家,我很不情愿地将买回来的利群牌烟,递给外祖母。那是她自己舍不得抽的烟,但为了邻里关系,她是不会争取自己的利益的。
晚上七点多,酒鬼木匠将修好的马桶送来时,我正在弹钢琴。他冲我说:“到底是有钱人家,这年月大家饭都吃不饱,你还有钢琴弹,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呵!”我朝他白了一眼,外祖母客气地向他道谢了又道谢,直听得我厌烦透顶。我心里想,哪有这样胳膊往外拐的?
我很想要一只铅笔盒,买一把新算盘,一只新书包,可是我从不敢开口向她要。阿大新,阿二旧,阿三破,用到我身上算盘也是缺胳膊少腿的。我穿的衣服,也是两个哥哥的旧衣服,没有女孩花朵般的味道。同学们见我常穿着男孩子的衣服,给我取绰号:野小子。
她不在乎同学们这么叫我。那天几个女同学来家里,她看她们穿得花蝴蝶一样,和我说:“给你也做一件花衣裳吧!”可是到了过年,花衣裳连个影子也没有。她说:“我把布票换年糕和糯米粉了。明年再给你做不迟,你还在长个子呢!”
大年三十前,她会把家里养的一群鸡,大概有七八只,一只只斩杀。她杀鸡,从来不让大哥二哥帮忙,却总是叫上我,让我抓住鸡的脚爪。我不敢看她用菜刀锋利的刀刃划向鸡的脖颈,但鸡在我手中一颤一颤地挣扎时,我的心就悬了起来。
她把鸡杀白洗干净,给自家留一只,就开始送人了。张家一只,李家一只,姨婆一只,送的全是隔壁邻居。有些人家,只向她道声谢谢,并不礼尚往来,她也从不计较,真是有大户人家小姐的派头。这年的小年夜,舅舅从上海来,她就把自家留的那只杀白鸡给他带走了。养了一年的鸡,她和我们三兄妹连鸡汤也没喝到,但她很快乐。每当邻居告诉她这鸡好吃时,她就很有成就感。
大哥二哥因为没有吃到鸡,大年三十和她吵起了嘴。大哥说:“你把我们当什么?谁养着你的?”二哥说:“我姆妈的工资都给你了,你给我们吃什么?”兄弟俩声讨着,一句句就像利剑一样刺伤她的心。我看到她坐在床边,猛抽烟,一言不发。开始我有点幸灾乐祸,但见两个哥哥无情叛逆,又同情起她来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却不敢走过去安慰她。
三
就在那年春节后,我的两个哥哥回父母家住了,这让外祖母很伤心。她对大哥二哥说:“你们真的要走吗?你们回去谁给你们做饭吃?你们的姆妈医院里工作忙着呢!”大哥说:“不要你管,我们吃食堂。”大哥二哥头也不回地走了。她绝望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喊着他们的名字道:“大泉、小泉,你们要常回来看外婆啊!”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悲凄,仿佛生离死别似的。
那几年我和她两个人生活。虽然没有了从前的忙碌,但也不寂寞。她可以对我颐指气使,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她就让我隔三天给她洗个头,过两个月给她剪一次发。她省下去理发店剪头发的钱,积蓄起来等着大哥和二哥回来给他们买好吃的。
一天二哥给她送月规钱,也就是她和我两个人的生活费。她把老早就准备好的一包花生,一包水果糖从一只纸板箱里拿出来,上下打量着二哥说:“瘦了,瘦多了。”二哥说:“没瘦,你老看我干什么?”她说:“看你瘦多了。”
我惊讶她竟然为了防我偷吃,把食品藏到放衣裳的箱子里。我一边生气,一边馋涎欲滴地注视着二哥咀嚼花生的样子。突然二哥对她说:“你想吃死我啊?”她说:“什么话?这是最贵的小洋生呢!”二哥说:“你自己吃吃看,那是什么味道。”二哥把花生一推,气呼呼地走了。她一边剥一粒花生放进嘴里,一边喊:“你别走。”
二哥一走,那一堆花生和水果糖就是我的零嘴了。她转身问我:“真有味道吗?我怎么吃不出?”我说:“有樟脑丸味道,不过我不在乎。”她说:“你那馋样子,好像我一直把你饿着似的。”我朝她看看,没敢顶嘴。
舅舅依然每个月回来,大哥二哥不在,他也不带我去玩,也不给我买巧克力。当然,我早已没那份期盼了。外祖母仍旧会在他来之前做好吃的,买上一些营养品让他带回上海去。有时给多了,我们一个月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以致一日三餐全吃素。家里母鸡下的蛋,她也舍不得吃,一只只编号,存够五十只送给媳妇坐月子。
为了省钱,她不再找人挑自来水。缸里的自来水快吃光时,她就找上我去抬。抬两次,就把本来给别人的一担两毛钱省下了。她一空下来就纳鞋底,织毛衣,缝缝补补。我脚上穿的,全是她做的方口布鞋。她不但自己做,还一针针地教我纳鞋底,织毛衣。她说女孩子要学会这些,将来好做人家。
那天舅舅看见我会编织毛衣了,就让我给他的新生婴儿编织小毛衣毛裤。由于是刚学会编织,我完全忘了他对我的不公平,欣然答应了。第二天他买回来橘黄毛线时,关照我下个月来取。于是每天晚饭后,我编织小毛衣毛裤,外祖母纳鞋底。在一派静谧中,她有时会和我聊家常,聊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时光。
“那时光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没放学外边小轿车就停在那里了。女孩子穿皮鞋,长统袜,跳舞裙。我的皮鞋是红色丁字形的,长统袜是白色的,跳舞裙是格子背带裙。我喜欢把两根粗粗的长辫垂到胸前,做不出作业时就把辫梢含在嘴里。”
“你没小轿车来接你吗?”
“没有。我们家在绍兴,是我一个人在上海读书。”
“你在上海这么多年,怎么还是一口绍兴话,你们同学把你当乡人吧?”
“瞎说啥哩,我和同学说的是英语。哪像你到现在都不会说英语,你们学校都在学点啥英语?”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不就是口号么,这也是学英语?”
“那当然。”
她“嗨”地叹了一口气,不吭声了。
有时我问她问得萝卜不生根。高兴时,她会一五一十地把从前她父母家里的事告诉我。那些三姑六婆,叔伯婶娘以及她的兄弟姐妹、堂兄堂妹等。我喜欢听她讲从前的故事,那是一幅幅晚清民间图景。我知道她与从前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她不抱怨。她说:“那是命。”
我初中毕业考入高中后,要走上半个来小时的路,中午就不回家吃饭了。我不回家吃饭,她的中午饭就更加马虎了。她要把钱一分分地省下来,给小孙子买个漂亮的绸缎斗篷,免得小孙子在寒冬腊月里受凉感冒。我说:“你自己做一个给舅舅带走不就行了吗?”她说:“你那上海舅妈能看上?”我说:“看不上拉倒。难道就我配穿你做的?”她说:“还真的就你配穿我做的。”我说:“你这是欺负我。”她说:“我欺负你啥哩,我一针一线做给你穿,还欺负你?”我说:“我不要穿你做的,我要买新的。”
这年我十六岁,已经开始喜欢打扮自己了。没有店里买的新衣服,我就穿自己编织的毛衣,弹力针型,穿在身上很有曲线。我的头发也不再梳成两根羊角辫,而是披在肩上;刘海儿用一把铁钳在火里烤热,卷成弯弯的。我还用自己存了多年的零花钱,买了一双方口皮鞋。她说:“呦,像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放学我再不按时回家,常常三五个男女同学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完全打破了初中时男女生不说话的局面。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我很快被一个男同学喜欢上了。他是数学课代表,发给我数学簿时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喜欢你!”我看到纸条满脸羞红,仿佛那纸条是我写似的感到难为情;而他已逃远,远远地注视着我。
这天放学,数学课代表一直悄悄地跟着我。见没人时,他塞给我一只漂亮的金发洋娃娃。我第一次收到男同学的礼物,有点慌张,但还是在慌张中接收了下来。回到家,外祖母一眼就看见了我手上的金发洋娃娃。她警惕地问:“谁给你的?”
“同学。”
“男同学吗?”
“你问那么多干啥?”
“你明天给我退还给他。”
“为什么,我喜欢洋娃娃。”
“你给我退回去,我会给你买个和这一模一样的。”
我半信半疑,但我知道她反对我接受男同学的礼物。第二天一早我趁着没人,就把金发洋娃娃退还给数学课代表了。没想到他恼火地随手从教室的窗口扔了出去,让我惊讶、心疼和
尴尬。
四
那天放学回来,我对外祖母气呼呼地说:“都是你,你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我说着伤心地“呜呜”哭起来。她说:“我怎么你了?”我说:“你让我出丑,他当即就把洋娃娃从窗口扔出去了。”她说:“这样的男孩子,你不值得为他伤心。”我仍旧“呜呜”地哭,她说:“女孩子找对象要长眼睛,不然一辈子痛苦。况且你还没到找对象的年龄,急什么?”她这么一说,我满面绯红。我说:“你胡说什么?我哪里找对象了?”她说:“你别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可多了。你给我好好读书考大学吧!将来好男人多的是。”
“啥叫好男人?”
她一时语塞。接着说:“反正你不准在学校谈恋爱,你若出了事,我怎么向你姆妈交代?”我说:“我没谈,你别乱说。”她说:“我向你敲警钟。”
我十六岁初恋的萌芽,就这样被她扼杀了。我开始不理她,她也不理我。我们陷入了冷战。她狐疑地望着我,仿佛我还在偷偷摸摸交男朋友似的。一天,我在学校参加校庆活动,天黑了才忙完一大堆杂事。她不放心地赶来学校,见我和几个男生在教室里嘻嘻哈哈,劈头冲我骂:“你个小混蛋,我就知道你不听话,你给我回去。”
男生们一下安静下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冲她说:“你来干啥?”
“喊你回去。”
“我不回去。”
“你翅膀硬了,不要我管了?你再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情。”
“出事情也不要你管。”
她扬起手来,一个男生赶紧插嘴道:“我们忙完校庆聚一起聊聊天,您老放心,不会出事情的。”说完,他示意我跟她回去。然后,几个男生一个个溜了出去。她气呼呼地把脸拉得很长,一股阴森森的样子。我有点胆怯了,跟在她身后,一声不吭。
深秋院子里的树叶,一天一种颜色。由浅黄,而黄中透红。通红的叶子出现时,没多久它们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了。这时候那些光秃秃的树干,与枝桠笼罩之下的深红和金黄重叠的叶子让我陶醉。我在对大自然的陶醉中,忘了自己的烦恼,心情渐渐好起来。我不再和外祖母冷战,但仍然很少说话。星期天下午,我在饭桌上做作业,她和我说:“我去买点东西。”我头也没抬,回了一声:“哦。”
黄昏时分她还没回家,我就在煤炉上煮了饭。我们的厨房与姨婆家的厨房对面对。姨婆冲我说:“怎么你做饭?你外婆呢?”我说:“出去买东西了。”她说:“给小孙子买斗篷去了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你外婆也真是的,自己省死省活,给他们买个啥哩?”我说:“嗯,外婆就是那脾气,说不好的。”
姨婆的红烧肉香味,一阵阵飘过来。我已经很久没吃到肉了,一想到外祖母每月给舅舅又吃又拿,气就冒了上来。我冲着照壁一边诅咒,一边砸泥团,把一堵照壁砸成了大花脸。正在这时,墙门里的两个男人抬着外祖母在狭窄的板壁弄堂里喊:“小心、小心。”
我一惊,大喊道:“外婆。”
这时她神智还清醒着,挥挥手示意我走开。我一阵惭愧,仿佛刚才的诅咒全被她听到了似的。我紧张地说:“外婆,你怎么了?”
“你外婆摔倒后不会动了,也许是中风吧!”
“那该送医院,我找姆妈去。”
我一路飞跑着,在医院找到了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母亲。母亲说:“等我忙完就来。”大概晚上七八点母亲来了,但外祖母的神智已经模糊不清,认不出自己的女儿了。
外祖母入院后,再没清醒过来。那天放学后,我去医院看外祖母,正巧陪床的女佣走开了。我走到她床头,轻轻喊:“外婆,你醒醒,我是小英。”她望着我说:“你看你看,一只老鼠从我脚背跑过了。”她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让我沮丧和害怕。我没等女佣回来,转身就从她的床边逃出了医院。
我愧疚自己没良心,但后来我仍然没再去医院看望她。
一天帮忙抬外祖母的那个邻居,交给我一个绸缎斗篷,说:“那天你外婆跌倒,这斗篷正巧掉进一汪水坑,我女儿把它洗干净了。”我“哦”地一声,接过绸缎斗篷,待邻居一走,想着它就是导致外祖母病倒的罪魁祸首,我就恼火地拿着一把大剪子,“嚓嚓”地把它剪碎了。
外祖母去世后,这房子被舅舅拿走了。房产归了舅舅,我就回到母亲身边。这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经考上北京和上海的大学。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已经被平反。他告老还乡,回上海去了。我和母亲住的那几年,心里却满满的全是外祖母的影子。一个晴朗的春日午后,母亲难得有空坐下来和我闲聊。我们聊到了舅舅和外祖母。母亲说:“其实,你舅舅不是你的亲舅舅,是你外婆领养的;但你外婆待他比待自己亲生儿子都好,欠他的呗。”
“领养的?那谁是她的亲生儿子?”
“你的小舅是她亲生的。小舅在你出生那年离家出走了。”
“为什么出走?现在哪里?”
“一直没有音讯,不知是死是活。”
母亲说到这里,摇了摇头道:“不说了。”
我没再追问,但外祖母、舅舅和失踪的小舅盘绕在我脑海里就像谜团一样,久久不能散去。
五
如今在杭州这座城市,只住着我和外祖母。我住阳间,她住阴间。每到清明也只我一人,去她的墓地除草献花。母亲退休后,也回上海去了。我的亲人们都远在北京、上海和国外。前些天,我去东街路上看被舅舅老早卖掉的那间外祖母的板壁屋子。它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木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拆”字。三十年后,我呆呆地望着,一切都已沉静。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