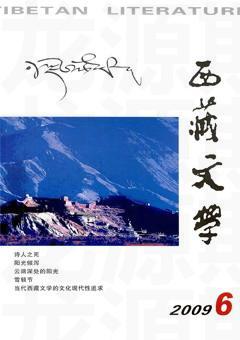当代西藏文学的文化现代性追求
胡沛萍 于 宏
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西藏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历史起点。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人民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他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开始以新的思维来思索周围的事物和内心的信念。社会的转型、变革带来的人们精神上的变化必将反映在文化和文学的转变之中,而文化和文学上的转变则会影射社会的变革。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西藏社会变革最明显的特征是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与规划,是对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向往与憧憬。在50年代初期,这种进步性的追求的具体表征主要是对旧的生活环境的拒斥、逃离,对新的生活家园的渴望和憧憬,反映在普通大众那里就是对个人作为“平等的人”的生存权利的确认和追求,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认同和实现。之后,随着新的社会制度在西藏的确立,随着新的社会建设的展开,思想观念和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西藏人民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社会思想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西藏社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西藏社会的各种转变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但都可以被规划到同一个轨道中去,那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换句话说,西藏社会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历程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这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古老而年轻的西藏人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坚定目标。而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中留下了形象的面影。可以说,那些精彩纷呈、体式各异,或客观写实或真切抒情或浪漫神秘的当代西藏文学艺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记录并参与了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性追求这一复杂、艰难而又伟大的历史进程。它们既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下了这个伟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助推器,在西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为西藏人民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寻找历史合理性,并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这种合理性。
一
对旧的社会生存环境的拒斥与逃离,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的渴望与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个人的生存意义和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从而成为一个有着自由生命的主体,是生活在旧西藏的广大民众在变动着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现实追求。具体地说,抛弃黑暗、专制、残暴的旧制度,从被奴役的枷锁中脱离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主人,过上有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是20世纪50年代西藏人民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的最迫切的渴望和追求。当然这种渴望和追求的实现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为前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西藏人民需要做出历史性的选择,并需要为这个选择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也正是当代西藏文学最初的基本叙述目标。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当代西藏文学走上了它的现代性历程。很明显,它的现代性追求和特征,首先体现在它的叙事内容上,即对社会进步的肯定和展望,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寻找与追求。也就是说,在叙事内容上,它的主题与社会主题是一致的。比如《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等。这些小说从主题上来说,有着相同的指向,那就是记录西藏人民对自由、民主、幸福的社会现实的渴望和追求。从这些小说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人民对社会现代性的执著与向往。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当代西藏文学都在为西藏社会现代化进程释放着自己的能量,它们见证了民族新生的历史过程。记录了民族奋进的精神面貌。
二
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西藏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征途上依然一如既往。只是跟以往的精神取向不同的是,从这时起,作家们的眼光除了继续叙述西藏民众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渴求之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开始用现代意识思索民族传统文化,并在对传统文化思索中发现不适合社会进步的因素,提出自己的质疑,以此寻求新的文化发展出路,试图让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获得生命力并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提供精神支持。在这方面,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扎西达娃在1970年代未走上西藏文坛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现实。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敏感和单纯,用他那并不老练的笔调捕捉下了那个时代发生在高原的一些微妙变化。当然,这一切与整个时代的精神风向的变换有着密切的联系。
19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转向的时刻,社会主题和全民诉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动向,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题的赫然凸现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力推行。与推翻旧制度,翻身解放作主人所具有的历史动力一样,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再次激起了西藏大地的巨大变化。人们逐渐从过去阶级斗争的漩涡里走了出来,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尤其是年轻人,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开始寻找着未来。扎西达娃早期的作品就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西藏年轻人不同与以往的生活状态。扎西达娃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西藏青年所具有的鲜明特征,那就是: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渴望,以及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途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引发的迷茫和困惑的情绪。在对扎西达娃早期小说的评价上,一般认为此时的扎西达娃显示了年轻作家共有的稚嫩和缺陷,其作品是简单地反映社会现实,没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厚度,“这些早期作品虽然说也充满了灵气,表现了藏族青年一代在新旧生活的冲突与矛盾中的选择和追求,但总的说大都停留在社会学层面上,既缺乏民族特色亦少有个性特征。”对于此种评价,笔者在过去也颇为认同,但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历程,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扎西达娃早期的作品具有社会学色彩,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确有些道理。但若说他早期小说“缺乏民族特色亦少有个性特征”和思想深度则是不确之论。其实,在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初期,西藏群众所表现出的那种独特的现代性特征在扎西达娃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他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既用真实的笔触又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题材和主题反映了走上新的历史征途的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变化的藏族作家。可以说,扎西达娃的早期小说比较及时且恰当地表现了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风貌。这个时代特征恰恰就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由于新旧事物和观念的蜕变而引发且鲜明流露出来的民族整体性的困惑和迷茫。只不过在扎西达娃的小说中,这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困惑与迷茫是通过处在不同阶层的西藏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境遇表现出来的而已。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扎西达娃早期小说了解当代西藏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在扎西达娃的早期小说中,对处在时代转变关口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作了三个侧面的描绘和揭示。一是新旧观念碰撞引起的冲突和心灵震撼;二是西藏青年面对现实的困惑与迷茫;三是西藏青年对
美好未来的渴望与追求。其中因新旧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带来的冲突和引发的困惑是最为典型的一种精神状态。扎西达娃在谈到自己的一篇小说时曾说:“也许,我当初写《归途小夜曲》的创作动机很简单,或者只是想告诉读者,今天拉萨青年不都是清一色的穿长袖袍,唱民歌,跳踢踏舞,而仅仅是这种生活习俗的改变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其中包含千百年的民族传统习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与渗透。”正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简单关注,却深刻地昭示了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艰难转变这一“痛苦”过程,因为这种转变是来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裂变。这种由来自古老传统的观念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观念所产生的尖锐冲突,极为典型地表现了西藏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所面对的艰难抉择。扎西达娃的小说《没有星光的夜》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历史内容的文本。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很简单,但它的选材却具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而其主题指向则更能展示民族传统心理和陈旧观念向现代意识的转换和裂变。
这篇短小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过去,“复仇”在西藏的康巴地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在那里素有“父仇子报,永世不忘”的风俗习惯。《没有星光的夜》的题材大概就源自于这样一个人们熟悉和古老的题材。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题材,但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却是中国各族人民对现代化社会热切渴望的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因此故事的主题指向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民族生命力蓬勃发展的陈旧陋习,在小说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留给人们的是一种面对未来的积极态度。小说一方面肯定了阿格布勇敢地抛弃旧有的观念,愿意向“仇人”下跪并结为朋友的行为的进步意义;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毫不讳饰地揭示这种观念的不合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小说的深刻和真实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以阿格布的下跪来结束故事,而是以拉吉的死和阿格布受到妻子和乡亲们的唾弃留给了人们深思的空间。小说写道,就在阿格布跪下的一瞬间,村民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人群像被一个霹雷惊炸开的羊群,姑娘们难过得几乎晕过去,小伙子们愤怒得狂跳起来,老年人痛心疾首。”“康珠猛地闭上眼,难过地扬起了头,颤颤地吸了几口气,两眼滚出了一颗颗泪珠。她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人群。”这样的细节描写意在警示人们,这种不符合现代社会法理规范的陈旧观念必须改变,然而改变又是极其艰难的,它需要有阿格布那样觉悟和认识较高的青年起带头作用。可以说,小说中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历史进步的内容是主人公阿格布的转变。阿格布的思想和行为之所以能够转变,从小的方面说,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具有先进的思想觉悟;从大的方面说,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觉醒了的追求进步的民族大多数人的集体要求。对于那些具有历史眼光的人来说,那些阻碍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遗留物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民族的进步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即使付出了代价,社会仍然会难以向前发展。扎西达娃安排了一个让主人公完成艰难的精神或观念改变的痛苦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一种根深蒂固且“合情合理”的风俗习惯的逐渐蜕变,也意味着一个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展示出的历史智慧和果敢勇气。扎西达娃的深刻之处一方面体现在他的选材的典型性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对故事发展及其结局的合理安排上。他既意识到了时代要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历史的进步必须以抛弃一些具有负面影响的思想观念和陋习为前提;同时他也深刻地意识到了那些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观念和行为是具有顽强根性的,它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们会长久地盘旋在民族意识的深处,所以他没有简单地让转变轻而易举地完成,而是让它经历了巨大的阵痛,在阵痛中完成了思想意识的转变。从《没有星光的夜》这篇并不完美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开始后,西藏人民现代意识的再次觉醒和对现代性生存环境的进一步追求,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追求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
现代性追求不但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以及群体意识、观念的巨大转变,更意味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即对个人自我存在价值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对个人自身活动空间的追求与扩展,对个人感性体验的积极张扬等。当然,对个人价值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对自身活动空间的追求和扩展,对个人感性体验的张扬并不是抽象的话语概念,它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个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中。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就体现在作家在创作中以语言文字的各种排列组合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充分认知和展示中。这种充分认知和展示既表现在作家在创作主题上倾向于对个人化的情绪、感悟的表达,也反映在作家在创作技巧上偏离传统,锐意创新的探索意识上。新时期以后,西藏文坛的作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创新、进取意识。1985年前后,就在中国当代文坛出现先锋文学的时候,西藏文坛以《西藏文学》为主要阵地,率先开始了文学新局面的开辟。在《西藏文学》的倡导下,提出了“西藏新小说”的概念。不管这种提法是否能够全面概括当时整个西藏文坛出现的新的文学创作倾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新出现的小说创作倾向的确表现出了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文学创新迹象。无庸置疑,这种创新意识源于对文学现代性的强烈呼唤,它们毫无疑问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冲动,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意识,它们似乎有预谋地要冲破传统的羁绊和镣铐。它们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自律性,即特别重视文学的艺术追求,而淡化文学的社会色彩,而这些恰恰是艺术审美现代性最主要的内在特征。专门研究审美现代性的学者周宪指出:“在我看来,自律性是审美现代性的关键,正是因为艺术具有了自主的特质,它才构成了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殊的张力关系,才塑造了现代艺术的面貌,才形成了审美现代性的诸多层面。”“西藏新小说”所呈现出的首要特征就是对过去创作手法的有意识的偏离和文学自律性的自觉追求。那些锐意创新的作家们不再迷恋和运用他们曾经熟悉的创作手法,而是选择了从西方舶来的各种现代主义手法和技巧。在他们的创作中,讲述什么故事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述故事;主题不再是小说最重要的要素,手法和技巧成了至高无上的因素。于是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不断出现,遂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潮流。在这些小说中,寻求主题已经变得不那么轻松,有些文本很难寻到一个稳定的主题,而作家们也不在乎主题的有无或明确与否,他们更乐于用飘忽不定的情绪和意识把玩所谓的文字游戏,制造叙事“玄机”。它们与内地的先锋小说遥相呼应,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文坛一道很独特的艺术风景。尽管这个潮流持续的时间并不
是很长,但它所展示出的风采却完全可以映照当代藏族文学在1980年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并因此而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在这个潮流中,除了扎西达娃和他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风马之耀》、《世纪之耀》、《丧钟为谁而鸣》、《野猫走过漫漫岁月》等之外,其他一些作家如色波、索琼、通嘎等人也创作出了许多很有特色的作品,如《圆形日子》、《九道班一夜》、《你在呓语,那不是歌谣》等,这些作家和作品共同为那个时期的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艺术自律性的确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代性侧面也逐渐凸现出来,那就是:面对不断进步的社会现实,天然具有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结的作家们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深沉思索和担忧,当然这种思索和担忧是与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觉醒密不可分的,同时它具有一定的反思性,一种独特的审美反思性,它来自于作家与现实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时期之后更为年轻的西藏作家,由于受到西方非理性哲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广泛而深刻影响,加上自身生活经历的历练,他们在为由于社会进步而带来的民族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和个人自由空间的不断扩大而深感喜悦的同时,也产生出了掩饰不住的忧虑和感伤。这种忧虑和感伤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无法根除的“精神病”,它在那些敏感而天生多愁善感的艺术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精神病”作为一种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它体现的是个人对生命的“超越现实”的体验和感悟,有的时候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观照中透露出对变化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迷恋或眷恋。具有这种精神特征的文学创作在两个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审美维度。
第一是对自身生命存在极具个性化的体验和描述。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西藏作家来说。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既是个人现代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文化趋势导引的结果。尊崇个人价值的时代,促使文学创作步入了“个体写作”的轨道,作家开始专注于描绘、展示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这样的书写在当代西藏诗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除此之外的第二个审美维度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新确认和皈依。当然,此时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确认和皈依,不是简单地肯定和认可,而是体现在文本叙事内容上的民族化,目的在于追求深厚的文化内涵,其最终的艺术耳的仍然是追求创作的“个性特征”,以区别于受全球化文化影响而造成的创作上的大一统趋势。当然,文学创作中文化内涵的增加也表现出了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担忧和焦虑。如果说扎西达娃等人的小说创作关注民族文化和与之相对应的思想观念,是为了揭示民族文化之中那些有可能阻碍社会发展,羁绊民族精神提升的陈旧因素,以求寻找民族进步,社会繁荣,从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现代性眼光;那么此时的年轻作家则采用的是另外一种眼光。他们更关注民族文化中那些具有积极性质的因素,并给予它们无限的向往和最高的赞美,他们最基本的心理诉求是,渴望能从那里找到民族存在的文化依托,让那些具有精神性特征的文化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在得到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拥有充实的精神世界,更为直接的目的是为自己漂泊的灵魂寻找到一个赖以安放的精神处所,因为他们在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现实中感觉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他们也感到了被“文明”压抑的生存困惑。现实的困惑使得诗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天空、云端和遥远的过去,那些充满着文化意味的意象成了他们难以舍弃的旗帜。在那里,他们寻找着属于自己心灵的宁静世界。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社会疏离的姿态。
年轻一代作家们的这种文化心理诉求,其实就是典型的审美现代性反思。他们通过文学的方式质疑现代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文化和精神的变异是否一定合理,其最终的目的当然不是否定现实,而是思索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继承和建设民族文化、培育符合人性的人文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文化关注和精神诉求尽管与前一辈作家的“文化关注”具有不同的方向,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指向,那就是促进民族进步、繁荣民族文化,提升民族精神,让整个民族的全面发展适应新的历史环境。
当代西藏文学的这两种不同侧面的追求,恰好表现出了现代性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实用性和反思性。实用性的现代性主要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它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这种现代性要求用理性为社会规划未来蓝图,并看重当下的有目的的社会实践,它意味着人们对物质丰富、科技发展等这些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渴望与享用。当代藏族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现代性的追求上,始终与社会实用现代性是步调一致的。也就是说,当代西藏文学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定位在为社会进步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位置之上。这样一种现代性追求自然是社会历史对文学的要求,也是作家们自觉的追求。随着新时期文学新潮的到来,当代西藏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所转变,不再是一味追逐社会实用现代性。在新的文学观念的刺激下,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审美现代性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文学在淡化政治、历史意识色彩的行进中,更多地呈现出了个性化色彩。当然,当代西藏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凸现并不意味着作家们不再关心社会现实,现实依然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只是他们变换了关注现实的方式。
当代西藏文学从一产生起就与现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可以说,当代西藏文学就是在西藏人民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渴望与追求中起步的,因此它的现代性是与生俱来的。从注重社会物质文明的“实用现代性”到侧重于精神世界的“审美现代性”,当代西藏文学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性追求中形象地展示了西藏人民风雨沧桑的社会实践和微妙细密的精神变迁过程,它以自己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西藏人民探索、追求的背影。
注释:
①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②扎西达娃:《和内地朋友谈创作》,《萌芽》,1983年,第2期。
③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3页。
责任编辑:克珠群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