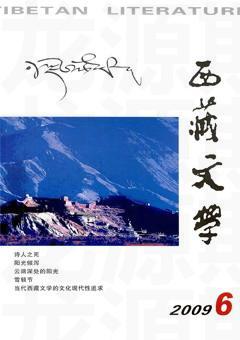玛吉阿米没有我的留言(另四篇)
周天燕
一个夏日中午,我带着远方的三位记者朋友从大昭寺出来后直奔玛吉阿米而去。
那天我们坐在楼顶平台上,闲适地品着酥油茶吃着藏式炒面。客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找来留言本,想一饱眼福。很有意思,我们在厚厚的一大摞留言本中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写字的整页纸张。土皮大哥和阿华老师好容易在一个夹缝处找到了一块勉强可以写字的空白处,快乐得如孩子。姚大师更绝,竟然洋洋洒洒地在一本留言簿的封面上写下了一大段文字。朋友说:“你也来几句?”我笑着谢绝了。那倒不是客气,是我不知道该留下些什么。无数次到过玛吉阿米,但是却从来没写过什么。不是没想过,也曾提笔想写过什么,但是提起笔却不知从何下手,一次、两次过后,反觉得什么都不留才是最好的感觉。
第一次到玛吉阿米是2∞5年与拉萨市文联的作家一道参加一个聚会。我们随着八廓街的人流转过一个街口,再转过一个街口,一幢黄色外墙的二层小楼呈现在眼前,玛吉阿米静静伫立在夏日的阳光下。走进小小的门洞,踏上窄窄的楼梯来到二楼,不大的空间里,沿着墙根安置着一圈古色古香木质桌椅,中间很随意地摆放着一张矮几和几张沙发,屋内显得很拥挤,却很随意、舒适。在有些发黑的墙上,是玛吉阿米的画像和一些美丽的壁挂。窗外,就是大昭寺的后门和八廓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八月的阳光洒落满地,照得人暖暖的,空气中飘散开朱哲琴天籁般的吟唱……那一刻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涌上心头。仓央嘉措,一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僧人,一个被推上圣坛的凡人,一个宫墙内吟诵的诗人,一个不幸的幸运者。玛吉阿米,一个善良美丽、温柔多情的少女,一个被活佛爱上的民间女子,一个渴望爱情的藏家少女。多少年过去了,这里依然留着两个青春男女永恒的记忆……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不记得那天聚会的情景,只记得玛吉阿米的下午充满无限的想象。
后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一个人在午后来到玛吉阿米,坐在二楼临窗位置,要一小壶浓浓的酥油茶,静静地看着八廓街上缓慢的转经人流,看得眼都涩了,再慢慢翻看着一本本留言簿,读着别人的故事,感动着,大部分时候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头脑一片空白,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耳畔回响……
那些用藏纸制成的本子,样子很随意,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精美,有的因为翻看的人多了而显得皱皱巴巴。本子放得很随意,只要你坐下,桌上就会有几本,随手就可打开、合上。先不说留言本里写着的内容,只用手抚摸着那柔柔的纸张,心里就有一种神圣而又充满渴望的感动,仿佛触动了心底那根最柔软的神经。其实那些留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
玛吉阿米没有我的留言,不是我没有话想说,因为活佛的情意缠绵的诗行已深深植人心底。
已过了开花的时光,蜜蜂儿不必忧伤。
既然是缘分已尽,我何必枉自断肠。
压根儿没见最好的,也省得情思萦绕。
原来不熟也好,就不会这般颠倒。
有活佛的情诗在心底,玛吉阿米却没有留下我的心路历程,不是因为我缺乏表达的勇气,因为活佛早在百年前已将我的情怀写给了格桑花般圣洁的玛吉阿米。
玛吉阿米,流浪诗人诗行中永恒的主题。年复一年,那座孤独的老房子依然伫立在桑烟缭绕的八廓街角,静静地聆听大昭寺的海螺声,冷静地旁观着世事变迁,接纳怀着各种心情到来的人们,用最平静的心态守望玛吉阿米的爱情。
没有我留言的玛吉阿米,处处飘洒着我少女般的情怀和宗教般虔诚的青春。
追赶夏的尾巴
西藏的秋天总是夏雨的淅沥中,在蔚蓝色的阳光下悄然来临,夏季静静远逝。
在一个十月的某个午后,我在急驰的汽车上看到车窗外蓝色的天空如海水般温柔地抚摸着大山粗糙的脊背。阳光下,世界在一片片金光中摇曳,在片片金黄中却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绿。秋正尽情地舒展着它厚重的色彩,把世界渲染得无比华贵,而夏如窗外飞逝的风景在视线里急速远去。
仰望天空,在湛蓝的天空里打盹的云朵和直白的阳光还泛着些夏的硝烟。一片干皱的杨树叶却轻飘飘地打在了我的脸上,季节在我身体定格——秋已深。因为在空气中,我分明嗅出了冬的气息,干燥中透着寒冷。
忽而来一阵凉风,下起雨来,一阵秋雨一阵凉了。秋雨打湿了秋厚重浓烈的金黄,打湿了夏的尾巴,却未能抚平树上树下那些干皱枯黄的面容。飘摇的树叶在雨中摇曳着枯黄的身体,落在冰冷的水泥路面上,而后被疾驰而过的汽车碾得粉碎。心也在这个季节碎了,湿了。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地下着,似乎想把夏彻彻底底地清洗,却将那蓝色的天空擦拭得更加洁净透明,把秋的色彩渲染得更加直白。
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在了十月底一个午后的两点钟,那天我坐在北京路上“川茶吧”二楼临窗的位置见证了今冬j不,应该是今秋的第一场雪。天阴沉沉的,一片黑云压在了布达拉宫上方,仿佛到了四川冬日的傍晚,以为又要下雨了,先是几粒青稞大的雪花和在雨中羞羞答答地洒落在干巴巴的马路上没了踪影,在风的鼓舞下,雪花儿逐渐成群结队地从天空扑向大地,飘落在街道两旁那些在秋风中还固执留守的黄的绿的树叶上,飘落在干渴的街道上,飘落在路人的衣服、脸上,迅速融化,不多会儿街道湿了,整个世界都湿了。这时我看到街对面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欢快地从一个门洞里奔了出来,在人行道上伸出双手接飘落的雪花,她虔诚地昂首望着天空,笑魇如花,跳动的身体像一朵跳舞的红雪花儿。
十月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阳光就从云层中露出了它灿烂的笑容,在川茶吧外的大街上,我的眼睛搜寻着街对面,想再看看那个想捉住雪花的红衣女孩儿,她一定是想接住好多好多的雪花儿,然后堆个雪人,与她游戏吧!这时,一个朋友对着雪后晃眼的阳光和满树落叶的忧伤,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没有话题的季节!”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望着雪后湿淋淋的大街,望着满眼的萧瑟,发了一会呆。无言以答!是呀!岂止是这个季节让人没有了话题,如今在这个充满欲望和贪婪的世界里,大家为名利,为生存而奔波战斗,朋友相聚,话题除了升职、加薪之类就是怎么赚钱买车购房,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话题可以引起大家的兴趣呢?我想问问在我头顶飞过的几只叽喳的麻雀,可它们没时间回答,因为它们要趁着北风没来前寻找充足的食物,以度过寒冷的冬天……
看着踏着春风一路歌唱着走来的夏,在秋风中越走越远,留下的尾巴让我追赶不上。在这个秋天,我的生命与淹没在这满目金黄中的绿一道淡出季节。我真想追上夏的尾巴去问一问,即将经历漫长的冬天,到下一个夏天来临之时,我的生命在季节的抚慰下还会复苏吗?你会为我带来云朵和阳光吗?
今秋的这场雪,打湿了秋的傲慢,打痛了夏的尾巴,拉开了冬圣洁的序幕。
追赶着夏的尾巴,我想留住季节的承诺。经历了这个秋天,北风即将把色彩拾起,我将窗台上仅存的绿收藏于心的深处,等待
下一个秋天到来时去追赶夏的尾巴!
藏地之春
伴着雪花,踏着冬的步伐,桃花悄无声息地开放了,西藏的春天就在一个下雪的早晨来了。
西藏的春天没有姹紫嫣红,连阳光都在每日午后的狂风中隐入了厚厚的云层。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高原农民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
西藏的春耕准备其实是在藏历年过后,三月中旬到四月初之间,天气欲暖还寒的时候就开始了的。这时农人们也刚从藏历年喜庆的氛围中走出来,周身似乎仍散发着青稞酒的香气。他们动用马、手扶拖拉机之类的运输工具,将自家积蓄了一年的农家肥运到田地里密密地撒,手扶拖拉机的“得得”声及马的脖颈上系着的颇显笨拙的硕大的铜铃慵懒沉闷的声音便把整个村庄淹没了,也唤醒了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广袤田野。
翻看藏历,择取了良辰吉日,春播便真正开始了。西藏各地的春耕仪式,因地理位置,气候差异,在时间上都各不相同,地区之间,县城之间,会相差几天到半个月不等。甚至是一河之隔的邻村之间也会有差别。旧西藏,高原的寒冷、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力,使藏地农民无法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因此,藏族人对土地充满敬畏和崇拜,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春耕有着一套近似宗教般庄严的仪式。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业飞速发展,彻底打破了靠天吃饭的落后农业生产格局。如今,高效率的机耕机播代替了“二牛抬杠”,高产优质的新品种的普及推广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以及农业科技的普及,使西藏农业生产迈向现代化。但对于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藏民族来说,土地胜过了一切,土地是他们存活的甘泉,是割舍不下的亲人。年复一年的春播是他们精心播种希望和幸福的日子。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对土地的期望和爱都浓缩在这年复一年的春耕中。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了一回林周县春堆乡巴则村的开耕仪式(春堆:藏语意为湖上面的平地),感受西藏农村庄严、神圣的春耕仪式。一大早,当金色的晨光洒向大地,薄薄的雾霭还笼罩着远山时,村外那块准备举行开耕仪式的地头40台拖拉机已一字排开,场面甚是壮观。还有两头被村民们进行了刻意装扮的耕牛。虽然早就不用它们来耕地了,却是每年春耕仪式上最重要的角色。用牦牛尾毛做成的硕大鲜红的穗子系在两只牛耳上,牛角挂上哈达结上五彩布条,脖子也用有着悦耳声音的铃铛点缀。牛每迈出坚实有力的一步,身上所有的饰物便有节奏地响起来,飘起来。俨然一匹出征的战马,一副威风凛凛、雄赳赳的样子。全村老幼都身着节日的盛装,手捧切玛(预示丰收的吉祥彩斗)、哈达、青稞酒和糌粑,那样子似乎不是去劳作,而是要到田野里会见什么要紧的人物或者参加盛大的派对似的。村民们先互献哈达、切玛和青稞酒,相互祝愿丰收、吉祥。人们寻来一块较大些的白石,将其视作一尊慈悲的神,恭敬地立在田埂。然后由年长者在地中央燃起了“桑”(松柏枝),在袅袅桑烟中大家纷纷虔诚地往“桑”堆上和天空中抛撒些糌粑、茶、青稞酒之类农家特有的东西,还不断地默念祈祷。所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之类的祈盼便一五一十地道给在渺远的神界正注视着自己的众神。然后齐喊“亚索!亚索!”(意为春耕开耕吉祥的祝词)。扶犁的男人将一条洁白的哈达系在牛角上,自己仰脖将碗里琼浆般的青稞酒喝个精光后,随着一声夸张的吆喝,犁尖便深深地插进初春松软湿润的土地。村民们也来到拖拉机前给每一辆拖拉机戴上哈达,并给犁手敬献哈达、切玛和青稞酒。随即,40台拖拉机齐发动,马达的轰鸣划破了高原的宁静,平整的土地很快被翻整出来,春耕仪式结束。
此刻仍然沉浸在开耕的喜悦中的村民们,在地头席地围坐,喝着青稞酒、酥油茶,品尝着风干牛肉、“卡赛”(一种用酥油炸制的点心,皮薄而酥脆)等食品畅谈着属于自己的农事话题。孩子们在田地间自由嬉戏。随着几杯青稞酒下肚,男人、女人们响亮悠长的歌声也在田野中飘荡起来。有歌者,就有舞者。大家一边唱着,一边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仿佛这才是春耕的高潮。这种狂欢会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到西山。这天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加嫫”(汉族女子)的加入,村民显得格外兴奋,歌唱得更响亮,舞步跳得更欢快了。孩子们开心地跟在我身后看我拍照,村民们热情地给我捧来青稞酒、酥油茶,惬意地与村民们坐在地头品尝着醇厚的头道青稞酒和浓郁的酥油茶,吃着美味的牛肉和“卡赛”,我感受着高原春天的热烈,高原人的豪爽。歌声划破高原的宁静,响彻九宵,藏地之春并不冷清。
当如火的夕阳铺满大地,村民们带着幸福而满足的微笑,踩着微醉的步子兰三两两地回到村庄之时,我在夕阳里久久回望这片土地,放眼天地间,思绪已然飞到秋天,金色的麦浪仿佛已在眼前翻涌起来了。夕阳下那群快乐、勤劳的藏地农民一定看到了同样的画面吧。
时间天堂里的一粒沙
那座如珍珠般镶嵌在江南水乡的城市,于我像梦之旅,充满浪漫温馨的想象。诗意的触感充盈我的情怀,但陌生。
那是个冬日午后,阳光慵懒地透过锦绣天堂巨大的落地窗,洒落在身上。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张餐桌的距离,真实得如梦。
站在这座城市热闹喧嚣的街头,因为有你在这里,我不怕。与你呼吸着同一座城市的空气,行走在你每天穿行的大街,幸福暖暖地包裹着我。冬日的阳光无比温柔。小雨无比清澈。这座城市有了你,便不再陌生。
此刻,你我如此接近,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呼吸,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眼角细细的鱼尾纹。抬头望着你傻傻地笑,那一刻你一定觉得我很低,是的,我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可我却在心底暗自欢喜。
进入这座城市的那一刻,我像一只迷路的蛾子,惊惶而迷离。而你却如城里的街灯,在无数个夜晚静静闪耀着温暖的光芒。那个空气中弥漫着湿腻腻泥土味道的夜晚,我飞临你的上空,在三万米高空望见你,如你给我的第十九次回眸般永恒。那一刻,我义无返顾地扑向你的怀抱,瞬间从此灰飞烟灭,时间永恒定格的是你慌乱的眼神。
在这座城市,纵横的街道,耸立的高楼,将天空分割得支离破碎,如我的思绪。关于这座城市,表象的熟悉之下,隐藏着说不清的陌生,走过那些残旧的石牌坊,穿过一座座古城门,仿佛穿越着时空,而我却从此失忆,在时间回眸间茫然、落寞。
你牵着我的手。凉凉的。一阵凉意迅速从指间涌向心头,在全身蔓延开来。你的手轻轻地不经意地从我脸上掠过,如你牵着我的手。那是你给我的温柔。只有我才能在冰冷中品味出的温柔。
阳光下锦绣天堂门前那座残破的石牌坊,仿佛升腾的烟雾凝固于此,在冬日阳光下散发着远久年代的味道。想到曾读过的一句话“当时间流沙般地从指间消逝,将我的面容刻划得斑驳沧桑之时,我的指间一定紧握着一粒沙,那是关于时间之外的回忆,里
面装着整个世界,只有你与我,”当然还有关于那只蛾子和街灯的回忆。那里是天堂。我们是时间天堂里的一粒沙。
在你的一个个转身,我的一次次回眸中,这粒回忆的沙遗失于这座城市。语言在这里失声,文字无法描摹我的心。
在这座城市,有你却没有我的诗歌。
在这座城市,有你的天堂我的回忆。
在这座城市,有你的熟悉我的陌生。
我的城池在三万里之外,八千米高空之上。
那里阳光灿烂!白云朵朵!那是我的天堂!
我可以在白云上打盹儿,我可以在雪莲上写诗,还可以在群山之间徜徉我的梦想!
那时的你,一定在天堂歌唱,那是一曲从相见那一刻便唱响的分离之歌。那时的我,一定在时间天堂里寻找那粒沙,那里有关于你和我的一切。
梦中的“乌金贝隆”——热振游记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可以经常到唐古乡熟振寺,每回去都能听到当地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与热振寺有关的传说、典故,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有这么一个传说就令我久久难以忘怀,那就是关于“乌金贝隆”的传说。
据说在热振寺外面的广场上有一个神奇的所在,你只要每天在那儿虔诚地转经,可能不知不觉地就在转经路上消失了。去哪儿了呢?这个转经路就在魔筒上,你不知不觉进入了“乌金贝隆”。“乌金贝隆”是传说中的一处圣地,类似于乌托邦、桃花源这样的人间仙境。有“一个隐藏的山谷”的意思,翻成汉语,可译作莲师秘境。那是有缘的凡人可以进入的理想国度。如果在纯洁无垢之人的带领下,人们只要充满善良的期望,保持一种纯净的内心,就有可能进入这样的神秘山谷,而一旦进入之后,你身后的山谷就会自动地合拢,也就是说进去的人,就会非常幸福,外面的无缘人,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无须传说,从第一次来到热振我就深信,美丽的热振风光和热振寺本身灿烂的历史文化就是我梦中的“乌金贝隆”。“热振”是“根除一切烦恼,持续到超脱轮回三界为止”之意。
一次次来到热振,我的心就像被什么牵动般,有种莫名的感觉,其中有点感动,有点渴望,还有点不知所措。从林周县出发,一路向北,翻越卡拉山口,山谷渐深,山中的植被也逐渐繁茂起来,隔着车窗向外看,远处,翠绿的群山被如哈达般洁白的云雾缭绕着,身边绿绒绒的草地上有五彩的“邦锦梅朵”静静地开放着,牦牛悠闲地散布在草地上,像颗颗黑珍珠,整个世界被渲染得如一幅幅流动的风景画。
过旁多,溯热振藏布而上,美景就不断在眼前变换表现方式。时宽时狭的河谷,是春绿秋黄的常年草场。清澈的水流,澄碧见底,柔曼恬静,又不时在湍急处白浪翻滚,使之凭添一股朝气。河北岸遍山长满四季郁郁葱葱的柏树,南岸一丛丛茂盛的灌木遍布整个山坡,春天小叶杜鹃默默吐芳,夏季山花烂漫,秋天色彩斑斓,间或有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高山调皮地探出了头……这里的一切与距它仅25公里的旁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没到热振寺先看到连绵成片的柏树林,蔚为壮观。热振寺就静谧地安卧在几十万株古柏的怀抱里,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比拉萨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早350年以上,是藏传佛教著名古刹。土石结构的围墙朴实无华,和多数名寺的气派华丽截然不同。百余平米的大殿里的殿中殿,供奉着阿底峡从印度带来的佛像。后殿是阿底峡、仲敦巴、俄师徒的塑像。一般寺庙里显赫的宗喀巴像在这处于一隅,而且塑像也比上述三尊小得多,主殿西侧偏殿供着阿底峡和一至五世热振活佛的塑像以及六世热振活佛的灵塔和塑像。寺周围号称有108泉和108塔,现在仍可看到许多佛塔散布在古柏间。僧人们住在家人修建的一个个院落里,俨然形成了一个修行村。
林间许多古柏高20余米,最高可达30米,粗细要几人合抱。面对这满目青翠,放眼天地四方,上边是宝石蓝的天空浮动着灿烂的白云,下边是翡翠色的江水夹杂着银色的石滩,相互映衬构成一幅难得的图画。山顶白雪皑皑,山坡上柏树青青,灌丛间姹紫嫣红,喜鹊树间穿行,牦牛低头吃草。在午后的阳光下置身于经堂、佛殿、僧舍、佛邸散布的古柏林间,四周静谧而安祥,斑驳的阳光洒落林间小路,佛殿中传出诵经声、林间有杜鹃婉转低吟,不远处热振藏布江在欢唱……一切声响在此时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的天籁之音,让人心旌摇动,恍然如入仙境。
其实这不正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乌金贝隆”吗?!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