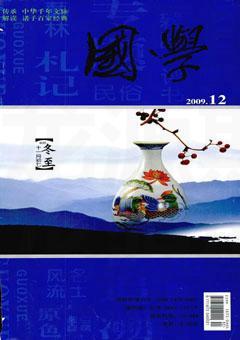民族智慧的守望者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掌握、擅长某些技能的能工巧匠的口传身授,民族的记忆、文明的脉络,才得以保留和延续——这些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工巧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怀念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然而,以人为载体、口传身授的特点是艺随人走,人类的许多珍贵的技艺,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绝种,而消亡。
传承人锐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告急的根本原因,直面这一现状的同时,或许更应欣喜地看到,较之以物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而言,传承人的可培育性和可大量“复制”性,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潜力和明显优势所在。
如何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寻访日渐稀少的传承人,培育文化传承新生力量,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留住人,才能留住艺,留住文化之脉。
一位词作家,舍弃名利,十二年来坚守在深山老林,为的就是保护、培育村寨文化的传承人
陈哲:让乡土文化活起来
12年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村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戴着眼镜的黝黑汉子在村寨间行走,有时坐在篝火旁,有时立在老树下,与熟悉当地民间文化的老者彻夜长谈,倾听唱经人的悠长吟咏,录下他们的歌声,摄下他们的舞姿,记下他们的风俗。
“我叫陈哲”,他的眼神非常亲切,衣着与当地人没多大区别,话语朴实自然,村民们很快就和他熟悉起来。当人们知道他就是《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这些响亮作品的词作者时,又都惊住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人会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的民间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致?
陈哲说,12年前他在云南、广西、贵州采风时发现许多古老优美的民族村寨文化不是变味就是消失,如果不赶紧抢救,以村寨为依托的那些民族就会丧失自己的身份标志。他认为,保存最具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就是维护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传承之路,并且越走越动情,越走越迷恋。他首先深入到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一个鲜花盛开、江河清澈、地貌保存非常完好的地方,在许多民族村寨建立了文化档案,用声像和实物记录了原始的文化形态。为了让乡土文化活生生地延续下去,他制订了“土风计划”,到每个村寨探访那些身怀文化技艺的长者,然后组成传承志愿小组,发动吸引村寨的年轻人加入传承的行列。年轻人多数都在外面打工,陈哲就一个一个启发他们,告诉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宝贵之处。劳作之余,他请老一辈人授课,课程是歌舞、语言、习俗,再请年轻一代边学习边研讨,定期考核、比赛,逐渐激发起年轻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欲望。
自2005年至今,兰坪大山里的普米族、傈僳族、白族、彝族的男女老少多次走到昆明、上海、北京,展示他们的传承结果。国内外观众和学者惊奇地看到,最具本民族标志的文化形态已经被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完整地传承下来,而最熟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那些老人也在尽情传承自己的所有文化记忆,陈哲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文化传承的艺术家、学者、学生。据统计,陈哲与其他文化传承志愿者已经发现了上百位村寨文化的老一代传承者,培育了30多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传承小组,成员有200多人。
文化传承的丰硕成果使陈哲信心十足,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下一步主要致力于云南白族拉玛支系、傈僳和佤族,湖北土家族,四川古羌后裔,广西与贵州的苗族的音乐文化传承工作。12年的艰辛耕耘,文化志愿者陈哲的传承理想正在化为现实!
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独特的演唱方式处于濒危状态
芒莱老人的长调梦
“我热爱蒙古长调,愿意倾其所有将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年过花甲的芒莱,是长调故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纳尔长调协会副会长。打小起,芒莱就天天跟着舅舅——草原歌王哈扎布学习长调。
每当挥着鞭子赶着羊群穿行在原野上,歌声尽情地飘荡在绿野,芒莱就觉得自己的歌声与草原已完全融入到了一起。与人交谈时兴之所至,老人还不时地唱上一两句长调,真的很难想象他这么单薄的身体,发出的声音竟是如此浑厚!
提起哈扎布老人,芒莱黯然神伤。他说,长调民歌具有“口传身授”的特性,而哈扎布老人的离开,对长调的传承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找一个像样的长调师傅太难了”。如今,歌王已去,还有一部分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旦师承关系得不到延续,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不及时传承,必然危及长调的保护与发展。
令芒莱更为痛心的是,哈扎布老人精心编写的上百首长调曲谱早已被毁掉了,在歌王退休后,很少有人请他出来办班,或者从他身上对长调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做一些资料整理、录制等工作,哈扎布没有出一张专辑,而他所擅长的潮尔、呼麦正濒临灭绝。
芒莱说,为了将长调传承下去,在草原歌王哈扎布的故乡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们组建了阿巴嘎纳尔长调协会,42名长调协会的成员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芒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协会上。
长调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想搜集、整理哈扎布生前演唱作品、声像制品,开展阿巴嘎纳尔长调的调查、研究,整理出版阿巴嘎纳尔长调歌曲的书籍资料等工作。并且将通过每年定期为长调爱好者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一批新一代长调歌手,使蒙古族长调这一传统民间瑰宝后继有人。长调协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60多人,整理出31首长调民歌,但没有经费,他们想搜集一些基本资料,却连车辆、汽油都要靠会员们自己垫付,处境十分艰难。
哈扎布的一个弟子,也是协会的成员,去年在协会忙了一年,不但没挣钱,还耽误了家里的生产。今年,为了生计,他去旅游点唱歌去了。“现在,蒙古族长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饭店、旅游点演唱”,芒莱说,这也没办法,现在协会搞活动很难,牧民们家里都有活,总不能让民间艺人饿着肚子保护长调吧。
近些年,政府投入专门力量保护长调,文化部门举办了多次长调比赛和长调研讨会,蒙古长调也从草原走向了学校,效果非常好。他建议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利用一些现代化的声像手段,加紧抢救和保护长调艺术。
当年黄道婆传下来的技艺,如今只剩最后一位“织布娘”
康阿婆独自踩着织布机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上海有两人榜上有名,分别是顾绣的传承人戴明教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传承人康新琴。
乌泥泾最后一代“织布娘”——今年75岁的康新琴老人,现场表演了脚踩踏板、翻飞梭子的技艺,这门技艺,是由康阿婆的同乡,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改进形成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棉纺技艺。
康阿婆摩挲着她56年前织的布,“整整56年没织了,没想到现在还会。年纪轻时,家家都有织布机的。”这些年来,只有两人断断续续向康阿婆学过这门技艺,“学会纺纱了,织布还早呢,梭子都摆不会的。现在没人愿意学了。只要有人学,我都愿意不要钱免费教的。”
上海徐汇区文化局文化研究室主任黄树林,仍旧觉得可惜,“以前乌泥泾还有一种挑织技艺,团花织出来是有立体感的,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已经失传了。”在上海,像康阿婆这样的老人已是个位数,黄道婆的技艺,濒临彻底消失。而顾绣传人、80多岁的戴明教老人已没法再拈起绣针了……
即使是发轫于上海近代工商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面对传承的烦恼。入选上海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龙凤旗袍制作技艺,其第三代传人徐永良,今年42岁,至今没收到徒弟,“学这个很苦,我17岁开始学,到现在还觉得没掌握成熟,现在根本找不到年轻人来学。”著名的海派旗袍,现在只有20来人掌握原有的手工缝制技术,都已40多岁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口传心授,传承人就是历史的‘活化石。有些民间老艺人不愿意传,那就是人走艺绝。”上海市文广局社会文化处处长刘晓南说,上海正在把对传承人的保护落在实处,如筹划着为传承人生存、生活提供保障;由项目保护单位和传承人共同协商收徒或尽可能以资料形式予以保存,提供技艺复原的可能等。
而上海面对的困难,更大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正在迅速消失。如黄道婆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如今即使走遍整个上海,棉花田恐怕也无处寻觅,“大都市现代化进展太快,这个问题比其它地区更加明显。” 刘晓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