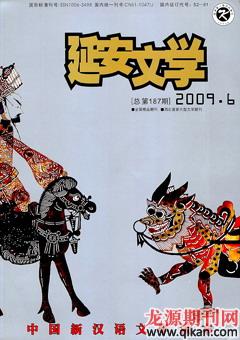户县女入
赵 丰
一
见惯了户县街头的女人,要想写点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走在街上的时候,听见女人的声音,如同炒豆子。我喜欢吃炒豆,放一粒在嘴里,“咯蹦”一声,脆响。那样的感觉真爽。喜欢吃,也就喜欢看人炒豆。一口铁锅架在街头,锅下是火焰,倒进白生生的黄豆,用一个铁铲子来回搅动。有时,我看着看着就走了神,忘记了脚步的移动。
女人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是从母亲开始的。而我,是从祖母开始的。童年,县城的西门下,就是涝河。祖母牵着我的手,出西门,到了河岸上。最深刻的记忆是在秋天的黄昏。清冷的风吹过,轻轻地一声声叹息,岸边的树便成了一种空旷静态的意象。黄叶拼尽生命全部的赤诚从空中坠落,点染了萧瑟的寒秋,昭示了生命成熟的厚重和沧桑。很快,天就黑了,星星点点滴滴地挂在天上。祖母让我数星星,我总是数不清。祖母一声叹息,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星。她的眼花了,看不见天上的星。后来,我长大了,才感觉到,天上的星星,是盛在祖母的心里了。
追述户县的历史,似乎比秦腔久远得多。汉唐时期,户县是皇室的后花园,称上林苑。一首《上林赋》,既成就了司马相如,也为户县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想象。“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皇家的公子哥们在此赋诗,狩猎,该是何等的风度啊。当然,这其中,是离不开女人点缀的。女人的气息,笑影,以及她们的鬓发、长袖,会让公子哥们滋生出温柔的情感。
我六岁那年,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家迁往沣河边的秦渡镇。1979年的秋天,我再次走进这座县城。那时,我已经粗略地知道了它辉煌的历史,但是它已经远离了昔日旖旎的风采。是的,一颗星,瞬间也会从夜空消失,别说一座宫殿,一处园林,那更渺小得不值一提。因此,面对着它的趋于平凡,我就有了儒生般的伤感。命运,就这样暗示我与它将结下不解之缘。这是缘分,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怀揣着一所中等师范的毕业证,我去位于东大街的户县一中报到。记得,是午饭后,学校门口有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吵架,你一句我一句地对骂,像爆炒豆子的声音。我始终也没有弄清她们吵架的缘由。因为,我想尽快走进那扇铁门,感受一个陌生的环境。
此后,我就蜗居在了县城。说户县是个小西安,是因为它的城中心有一个仿照西安钟楼建的建筑物。不过,它的名字换成了中楼。音没变,可是,“中”和“钟”,就成了不同的概念。八年后,我成了县政府的秘书。县府大院,就在中楼的东边。走进办公室,一开窗,我就和它遥相对视。距它不到百米的地方,有棵古槐。树的身围很粗,陪伴这座县城应该有些年头了。树木的品种里,我尤其喜欢槐。秋风扫荡的日子里,老槐细碎的叶子在树根拱起的土地上堆积了一层深沉的黄色,与稳健的青色树干融合得自然和谐。蹲下身子,掬一捧槐叶,伸手一握,枯黄的叶应声而碎。碎叶流沙般地从指尖流淌,宛若品味生命的漫溯,抚触时间的脉络。我甚至不忍心踩踏那些铺展在地上的落叶,因为,从吱吱呀呀的声音里,我总能感受到叶子的心碎。夏天,没有雨的日子,树冠下的阴影里就围着一些老女人。手里摇着一把蒲扇,不知疲倦地摇着。有时我想,她们是在无意识地守护着老槐的余生。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会靠在树身上,眯着眼睛,歪着脖子,用手掌支起下巴,仰头看着枝上的叶子。用这样的姿势来观察自然界的景物,对我来说,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二
南方人到了西安,会感受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的景象。户县距离西安也就几十公里,南面是秦岭,北边隔着渭河就是咸阳。咸阳市区往北是一道塬,黄土下埋着许多皇上。每处埋皇上的地方都堆起一架小山。一刮西北风,尘土首先光顾的,就是户县。因此,县城的空气里弥漫着尘土的味道。每日有无数的农民工和车辆从乡下驶进县城,也把乡下的泥土裹挟了进来。如果穿黑皮鞋,鞋面上半天就是一层尘土。男人们有应酬,不穿皮鞋不行,女人们就随意了。她们穿布鞋或那种平跟的休闲鞋,走起路来匆匆忙忙,看她们的神情,仿佛焦急去赶火车,或者到某个地方去救火。
县城的女人大多来自乡下,真正的居民是极少数。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区也就两万多人。改革开放以后,城区的人口剧增到七八万。那些女人有的是享受了“农转非”政策的,有的是跟着丈夫进县城做生意的。还有,从乡下嫁给县城的干部职工或郊区的农民,从乡下的学校、商店、卫生院调回县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城工作。这是上个世纪进城的渠道,现在呢,渠道就更多了。比如在商场、农贸市场租间门面房做生意,在美容美发店、茶秀、宾馆饭店做服务员,在建筑工地打工,做保姆,跑出租……在小城的历史上,她们只是一个个过客,或者说一粒粒沙尘。但她们活得有滋有味。
在乡下,女人通常比男人起得早。这是因为,她们要在太阳出来前做好全家的早餐。要是谁家屋顶的炊烟在清晨的霞光中升起,是要遭人耻笑的。进了县城后,她们依然维持着这种习惯。
很快,我就发现,县城的女人们喜欢吃辣子。那馋劲,绝对让男人汗颜。顺口溜中的“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是针对女人编的。女人们吃辣子,不是细细地放一点提味儿,而是当菜来食用,吃面条放辣椒,吃搅团放辣椒。饭碗里没菜、没油、没肉能行,但要是没了油泼辣子绝对不行。无论吃什么,都是红红的一碗。手里拿半个热蒸馍,也要用辣子抹得红彤彤的。我有时想,户县的女人性子急,说话像炒豆,是不是跟辣子吃多了有关?
不长时间,我的耳朵就习惯了女人们那种炒豆的声音。我有熬夜的习惯。常常,还在梦中,就被女人的叫卖声吵醒。楼下,是一条马路。天还未亮,马路上就响起了女人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卖菜咧——割豆腐咧——谁要蜂窝煤——谁买鸡蛋!”那“蛋”字,拖得尖细,悠长,像一把无形的锥子,刺破我梦境里某个温柔的情节。楼里住的女人们这时会俯身在阳台上,高声吼道:“等一下!”只那么一两分钟的功天,她们就端着盘子,穿着拖鞋,踢踢沓沓地下楼。你仔细看去,说不定衣服上的某个纽扣还没系上呢。
在县政府办公室上班的间隙,我常去的地方是中楼西南角。西南角原来是红旗商店。这是一个时代味很浓的名字。后来经过扩建,改名中楼商场,沿街开了许多门面房,经营者大多是女人。我常去那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邮电所,可以寄发稿件。老远,无数双女人的目光就伸长过来,揣测着我脚步的方向。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就低着头,仿佛在想着心事。就这,她们还不肯放过我,这边扬着嗓门喊:“买啥衣裳进来看——”那边的嗓门更高:“吃啥?米饭、饺子、扯面——”
户县的面条有数十种。斜角面、担担面、尖尖面、油泼面、臊子面、摆汤面、凉拌面、浆水面、糁(户县人发zhen音)子面、炸酱面、麻什、扯面……都是女人们的拿手活。那种叫扯面的,她们做的又厚又宽,类似裤带。做法是,将面和硬揉软,擀厚、切宽。双手扯住两头,在案板上使
劲地拌,发出“biang——biang”的响声。下到锅里煮熟。捞一条在碗里,无论是浇肉臊子,还是泼油辣子,或是番茄鸡蛋做卤,吃着光滑、柔软、热火、有筋性。既可口,又耐饥。
“面条像裤带”。是关中八怪之首。关中地方大了,真正地道的,还是户县女人做出来的。西安的、咸阳的、宝鸡的人来户县,都寻找“biang——biang面”吃。
有时,我中午不回家,就走进中楼西北角那家“大槐树面馆”,坐下,研究一些人的吃相。常常碰到一个中年妇女,人不胖,但总是要的大腕面。她噙住面条的一头,腮帮子不停地蠕动,牙齿噘面时发出“biang—biang”的响声。我观察到了,她在东北角的地方开着水果店。进了面馆,我不会那样干坐着,否则不仅面馆的女主人不高兴,顾客也会视我为精神不正常者。那时,我也是个顾客,面前也会摆一碗慢慢地吃。不过,总也吃不出曾经拥有过的感觉。上世纪七十年代学大寨时,我和村上的人去修太平河,每个生产队都有灶。我吃过我们队上寿娃他妈做的裤带面。那才是正宗的。宽度二三寸,长度一米上下,一根面条可以捞一碗。那时修河,全凭人力。尽管干着拉车、搬石的重活,一个下午不知道肚子饥。我的胃就是那时吃坏了的。吃饭不要钱,我就不要命地吃。还记得,那个中午,我吃了两大碗,下午受了凉,饭在肚子没有消化,晚上胃疼得在炕上翻滚,被送进了镇上的医院。
我的毛病是,喜欢保留一些特别的印象。因此,看到那个笔画异常复杂的“biang”字,总有一种亲切感。
三
户县女人的温柔细腻都融入了一些细节之中,或者说表现在一些被封闭的角落。我所看到的,不过都是一些表象。
一条铁路从县城的心脏穿过。十多年前,那儿还只能算是县城的边缘处,可是现在,它就成了县城的要害部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铁路和秦户路交叉的电线杆下,有一个三十岁左右卖草莓的女人。当然是春天,她瓜子型的脸上沐浴着沉静和温暖。我喜欢吃草莓,甜甜的,口感带着柔润。那天,我从那儿经过时,就称了一斤。谁知当我付钱时,却发现自己的兜里没装一分钱。她看出我的尴尬,笑道:“拿走吧。你不是每天中午都从这儿路过么?”
买草莓的钱,第二天我是如数付给她了。渐渐的,天就热了起来,她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她是乡下的女人呢,还是县城里做二手生意的女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跨过铁路的时候,总是无意识地朝那个电线杆下瞥一眼。那儿空荡荡的,我感到缺少了什么似的。我始终记得她那张如草莓一般红红艳艳的笑脸,以及柔润的语调。但是,如果某一天在其它地方碰到她,我不敢确定,我还能认出她来。有些事,有些人,远离了特定的环境,你真的不能相信你的记忆和判断。除非,你有什么特异功能。
与众不同的女人,藏匿在这个县城的角角落落。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去县医院探视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人——她曾是我值得尊敬的上级。坚毅、沉静、孤寂。这是她驻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她是从县人大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的。每年的中秋和春节,我都会去登门看望她。在病房里找不到她,我就来到住院部大楼前的花园里。果然,她坐在一条石凳上,安静地注视着地上的树叶、花叶、草叶。夕阳下,四处飘落的黄叶泛着金黄色的光。我轻声地呼唤着她,她回过头慈祥地对我一笑,脸上竟没有丝毫我所担心的悲伤。我陪她坐下,只是坐着,因为任何安慰都失去了意义。她捡起脚下的一片树叶注视着。那是一片极规则的枫叶,伸出七只工整的角,在夕阳的红晕下泛出一片金黄色。她在微笑,是那种让人欣慰的笑容。我被她的笑容深深地触动了,情不自禁地也捡起一片枫叶注视着,仿佛注视着自己的生命一般。
离开老人,我突然想起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落叶》。那是一个由一片藤叶演绎出的经典故事:病床上的乔安娜看到窗外的爬山虎叶子不断被秋风吹落,不无伤感地说,最后一片叶子代表她自己的死亡。老画家贝尔曼用画笔画出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春藤叶,挂在乔安娜病房的窗前。乔安娜绽放出了往日的笑容,精神日渐好转,终于活了下来。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谁能否认生命中的奇迹呢?我的老上级,那位患了绝症的老妇人,在灿烂的晚霞下,那样专注地注视着一片落地的枫叶,无疑是在感慨岁月的短暂,留恋往昔的时光。
四
户县这个地方,汉唐时期的富人也许很多。但是现在,有钱的男人就很稀罕,于是县城的女人们非常在乎小钱。在菜市场她们会为几分钱和卖菜的人争执,买衣服一般是先看价格,上百元的衣服不管怎么喜欢也舍不得掏钱。看电视时尽量把音量调到最小——她们以为音量越小耗电越少。淘了菜的水、洗了衣服的水一盆盆地攒着用来冲马桶。即使住在六楼(七层的居民楼基本没有),也不愿雇人把刚买的蜂窝煤、煤气罐搬上去,宁愿累得腰酸腿疼也要自己搬。户县远远不到享受天然气的地步,虽然家家有了煤气灶,也还是舍不得蜂窝煤炉。县城的人们几乎家家都盘炕,砖砌的,很漂亮。蜂窝煤炉白天做饭烧水,晚上烧炕。冬天,女人们离不开炕,坐在炕上纳鞋底、织毛衣、打麻将。盘了炕冬天就可以不用电褥子,也不用安暖气和空调。节俭归节俭,但她们毫不吝啬。谁家吃好的,忘不了叫来邻居、朋友共同享受。别人来借东西,她们认为是瞧得起自己,满面笑容地拱手相送。
我想,作为古时的京畿之地,这里的女人们应该不会陌生粉饰玉簪。当然,我指的是古时的女人们。现在呢,女人们总是抱怨跟不上时代。电视上闪出的化妆品广告对她们而言只能是精神的享受。走进超市、商场也只是瞧着那些化妆品满足一下眼馋。也有慷慨解囊的,但往往是“降价”了才“潇洒”一回——这时,新的化妆品又上市了。她们羡慕电视广告中的美女,但要是丈夫也在旁边勾着眼睛看,她会当着丈夫的面朝地上吐口唾沫:“妖精货!”解恨,精炼,连个感叹词都不用。
有一次,我在东关十字北边的人人家超市门前上了辆出租车。屁股没坐稳,车门还没关,一个女人的嗓音就响起来。“啥地方?”语速紧凑,简洁。是个女司机,年龄也不大。我关了车门,开了句玩笑:“你比我还着急呀?”她说:“今天背霉得很,在县城里空转了七八个来回”。一路上,她的话就不断线。不是嫌前面的车走得太慢,就是抱怨十字路口红灯的时间太长,再有,责怪某个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那天,好像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几次想打断她的话,讨论些天气之类的话题,但总是找不到她说话的缝隙。无奈,我就看着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努力让心灵变得滋润一些。
想到一个比喻:城市是一个蛛网。男人们守着网的疆域,女人们则像蜘蛛一样,来来回回地穿梭。谁能知道,她们在忙碌些什么?近些年,务花养草,成了县城女人们的嗜好。谁家的阳台上,没有几盆花草?男人们事多,再加上粗心,施肥,剪叶,浇水,都成了女人的活儿。渐渐的,东大街的府兴巷,就成了花市。
猪耳朵,是一个粗俗的名字。想不到,它会以盆花的形式出现。而且,现在依然被妻子养在院子。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家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盖了栋带院子的小楼。妻子在院子务着蔬菜,从没有动过养盆花的念头。去年冬天,她不知在哪儿弄回来一盆猪耳朵。它的形状普通极了,宛若猪的耳朵,肥厚,圆胖,肉肉的。一种极其普通的草,妻子却不愿委屈它,用花盆装着。为了让它的叶片有一副洁净的面容,她在街上买了一个带嘴儿的洒水壶,天天给它喷水。看着妻子洒水的样子,我有点想笑,又不想扫妻子的兴致,就由她摆弄。
那盆猪耳朵,既然起了一个卑微的名字,也就如同小城的女人,普普通通的生长着。刮风,下雨,大红的日头,都不用操心。它生长的速度极快,不知不觉的,就长了满盆。今年开春的时候,妻子嫌那个盆小,又换了一个更大的盆。有了生长的空间,它也就不负人心,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到今年夏天,它竟然覆盖了整个盆子,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我想,它没有尘世的欲望,也不会开花结果,但是无法遮盖它的高尚。它无法赢得人们羡慕的目光,就只有忍耐着寂寞和冷落,坚守着自己的朴实和清贫,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欢乐。是的,一种植物,和人类一样,即使普普通通,它也不言放弃生命的价值。